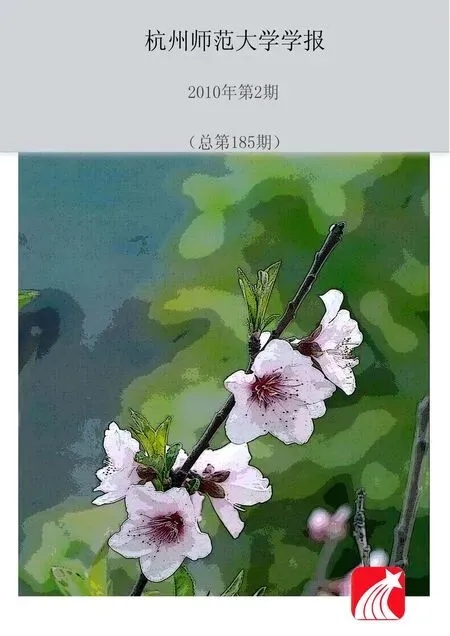別于董事義務的公司經理義務研究
吳偉央
(華東政法大學 經濟法學院,上海 200042)
法學研究
別于董事義務的公司經理義務研究
吳偉央
(華東政法大學 經濟法學院,上海 200042)
英美衡平法下的Fiduciary概念包括了董事和經理,造成了公司中董事和經理在義務和責任方面的混同。董事并不是公司的代理人,而經理是公司的代理人,應以代理法規則為基礎來確認經理的義務體系。與董事義務相比,經理應具有更高的忠實義務,經理違反注意義務的標準是一般過失。經理契約豁免經理義務的底限是不能因為免除經理義務而使董事會失去監控職能。
信義義務;義務標準;豁免底限
在現代公司中,董事會的職能逐漸地從經營(manage)職能中退出,正如艾森伯格教授所言:“事實上,董事沒有也不能指示公司經營和運行。實際上,在小型的封閉型公司中,公司的業務直接被股東經營,而大型公眾公司的業務則被高階層的經理經營”。[1](P.376)。故而,在公司的治理結構中,董事和經理的職能是有明顯區分的:董事的職能主要是代表公司監控(Monitor)和評估(Evaluate)經理的行為,而經理的職能主要是作為公司的代理人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而經營公司,兩者在現代公司中行使不同的職能,履行不同的義務,同時承擔不同的治理責任。在公司治理的法律研究中,應該對兩者進行區分,并有意識地對兩者的義務和責任體系進行區別性構建。
但是,在目前的公司法研究中,公司的董事和經理往往都被認為是公司的“fiduciary”,他們對公司負有“fiduciary duty”*本文將“fiduciary”譯為“受信人”,將“fiduciary duty”譯為“信義義務”。。長期以來,董事義務和經理義務往往被認為是同一件事情,再加上在英美的公司立法中,成文法規制的重點基本都是針對公司董事,公司經理的義務和責任一般都參照適用公司董事的有關規定。針對這樣一種現象,本文從fiduciary的界定著手,以比較董事與經理之間區別的視角來對公司經理的義務進行系統研究。
一 Fiduciary的概念界定
英文中的“fiduciary”一詞來源于拉丁文中的“fides”,其含義是“誠信”(faith)或“信任”(confidence),強調的是接受信任的一方要為另一方的最大利益而行事。與“fiduciary”(受信人)相對應的是“beneficiary”(受益人),兩者之間的關系稱之為信義關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
嚴格意義上講,受信人(fiduciary)、信義關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和信義義務(fiduciary duty)并不是源自于立法上的術語,相反,這是一組來自于英國衡平法院判例的用語,內涵和外延相對比較模糊。從它的發展來看,信義義務是18世紀晚期英國衡平法院在裁決關于“信任”事務中,為了保護受信人的利益而發展起來的,當時提出這個概念是基于一個非常概括性的原則——“當一個信任被設置了,如果這個信任被濫用了,衡平法院應給予濟助。”[2](P.70)后來,信義關系被適用于很多場合,具有了多重含義。“只要一個人得到了一個不管什么樣類型的權力,權力接受者使用那個權力來為另一個人的最大利益行事”[3](P.75),這種關系均為信義關系。受信人、信義關系等是一組開放式的概念,沒有固定的含義,很多社會關系都可解釋為信義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信義關系與“信托關系及代理關系”之間存在區別:第一,在邏輯上,作為一種社會關系,信托關系和代理關系均可稱為信義關系,這些法律關系可以理解為信義關系的屬概念;第二,在性質內容上,信托關系和代理關系等屬于有確定內容的法律關系,而信義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學理式描述*雖然學者們在解釋和研究信義關系的過程中對其內容和類型(忠實和注意義務等)等逐漸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是因為其本身開放性的外延和可探究性的內涵,使其在內容上總是存在著可解釋的彈性余地。;第三,在適用上,可以將信托法和代理法等具體的法律規則視作“特殊法”,將信義關系的規則視作為“一般法”,在具體明確為信托關系或者代理關系的場合,當事人的權責利應該適用信托法和代理法的規則,只有那些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關系,在屬于信義義務范疇的情況下,則可以適用信義義務的相關規則。
二 “董事——公司”關系與“經理——公司”關系及相應的法律適用
(一)“董事——公司”關系及法律適用
1.“董事——公司”關系一般被總括性地描述為信義關系。但是,具體到“董事——公司”關系到底應該定位成哪種具體的“法律關系”,適用哪個部門法的規則?由于公司立法沒有確切的論述和指引,學界也一直爭論不休。*如有學者總結認為:“董事、董事會與公司之間的關系,大體經歷了信托關系說、代理關系說到特殊關系說的一個發展過程” (見張開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7頁);另有學者總結了“代理與信托兼有說”“委任說”“代理與準信托說”和“法定關系說”等四種學說(見曹順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損害賠償責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博士論文,第21-24頁。)在此需要明確的是:第一,“董事——公司”關系不是代理法律關系。主要因為,董事的權力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法定性,并非完全由委托人(公司)授予和撤銷。另外,董事執行業務時的人格隱而不彰,展現在第三人面前的主要是公司的人格。第二,“董事——公司”關系不是信托法律關系。主要因為,董事并沒有像受托人一樣取得公司財產的所有權,而是以公司的名義與第三人發生法律關系。另外,董事為實現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要從事冒險的投資活動,而受托人是以保持該財產的價值為其第一要務,早期的信托法還嚴禁受托人從事有風險的投資事務。故而,“董事——公司”關系是一種特殊的法律關系。
2.在法律適用中,不能完全適用《代理法》和《信托法》的相關規則。信義關系是一個比較含糊的概念,其自身規則具有不確定性,也沒有具體的“信義法”支撐。故對于“公司——董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第一,適用《公司法》《證券法》中既有的確定規則,如關于董事的任免、公司董事之間的權力控制、董事的忠實義務規則及相應的法律責任等;第二,適用公司的章程和內部規約等類似于合同性質的規則,這些約定性的規范有助于厘清特殊情形下具體場景的法律適用;第三,適用信義關系的相關規則,學理性信義關系規則作為一種補充性的規范用以調整公司與董事之間權利義務和責任等關系。
(二)“公司——經理”關系及法律適用
1.關于“公司——經理”關系,學界中存在著代理人說、機關說、代表人說、三元角色說和管家說等多種學說,筆者認為,代理人說相對較為合理,并認為商事代理人角色更符合現實經理的地位。*關于“公司——經理”關系,在筆者的相關論文中設有專章討論。見吳偉央《公司經理法律制度研究——以經理法律地位為中心的權利、義務、責任體系分析》,中國政法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第27-51頁。故而,“公司——經理”關系是委托代理關系,更確切地講,“公司——經理”關系屬于商事代理關系。
事實上,英美法對于經理作為公司代理人的觀點基本沒有什么爭議。在美國《代理法第三次重述》立法過程中,曾明確指出:“公司立法注意到,公司的董事和在一些情況下的公司股東有權任命經理作為公司的代理人。”[4](P.1597) “在特定的場合中,公司非董事經理是相對于公司信義關系的信義方,所有的公司經理,就像雇員一樣,是公司的代理人,是作為公司和經理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一個參與方。”[5](P.491)大陸法系中,據學者考察后認為,“經理是典型的直接代理人,他以被代理人的名義為法律行為”[6](P.176)。可見,將經理在法律關系上看作是公司的代理人,將“公司——經理”關系定位成代理法律關系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2.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上,作為代理法律關系的“公司——經理”關系適用代理法的相關規定則是邏輯的自然延伸。英美法中,代理法較為發達,故將經理和雇員等定位成代理人后,直接適用代理法的相關規定。大陸法系在商法和民法中規定的經理權實質上也是一種代理權,或者說是一種商事代理權,具體適用法律的過程中也是以代理規則為基礎,主要適用代理的有關規定來確定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從上述關于“董事——公司”關系與“經理——公司”關系定位及法律適用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董事和經理都被視為公司的受信人,但是兩者之間是基于不同的基礎關系,董事與公司的關系是一個特殊的法律關系,而經理是公司的代理人,應該適用代理法的相關規則來確定其具體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籠統地將董事和經理義務置在信義關系的概念下來研究,難免會忽略兩者的個性,更看不到經理義務的特殊性。
三 經理義務的內容及標準
經理作為公司的代理人,其義務基于代理關系而產生,有必要從成熟的代理法中去研究經理義務的內容及標準。
(一)經理義務的內容體系——以美國《代理法第三次重述》為基礎
關于代理人義務的內容,學界有很多研究,但普遍存在著交叉和不系統的問題。2006年的美國《代理法第三次重述》(下簡稱《重述三》)對于代理人義務進行了清晰的體系性界定,為經理義務的內容體系提供借鑒*《重述三》將代理人義務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代理人“總的信義義務”;第二層次是忠實義務和執行義務;第三層次是忠實義務的4項和執行義務的6項具體義務內容。。
對應于公司經理義務的內容體系,筆者認為具體應包括以下內容:
1 忠實義務 具體包括:(1)“不得利用職位獲得物質利益的義務”,指經理不得利用與第三人交易時從該第三人處獲得物質利益,或者其他為了其自己利益的行為或者以經理的名義從事代理事務時從第三方獲得物質利益;(2)“不得為相對方利益行事的義務”,指經理應該為公司的利益行事,而不能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行事;(3)“不得競業的義務”,指經理有義務克制住自己與委托人的競爭,克制住為了自己或是協助委托人競爭對手的利益而進行的行為;(4)“不擅用委托人財產和秘密信息義務”,指經理有義務不得為了自己或是第三方的目的而去使用委托人的財產或者使用或傳達委托人的秘密信息。
2 執行義務 具體包括:(1)“遵守委托合同指示的義務”,指經理有義務按照經理契約中明示和隱含的條款意思行事;(2)“注意、技能和勤勉義務”,指經理處理公司事務時應當像通常處理在同樣情形下的自己事務一般盡適當的注意、技能和勤勉。經理特殊的技術和知識有條件地被考慮,取決于經理(代理人)是否適當地注意和勤勉;(3)“在授權范圍內執行事務的義務”,指經理有義務只在實際授權范圍內行事,有義務遵守來自委托人和委托人指派之人的所有關于經理為了委托人利益而行為的合法指示;(4)“善行義務”,指經理有義務進行適當的行為,并且克制住有可能損害委托人事業的行為;(5)“提供信息的義務”,指經理有義務盡適當努力來提供給公司及其董事會“經理知道的、有理由知道的或是應該知道的”有關事實的信息;(6)“財產隔離和保管商業賬簿的義務”,指經理不要在處理公司的財產時對外顯示出是經理自己的財產,做到經理財產與公司財產的有效隔離,保持和呈遞記載公司金錢和財產的收支情況的商業會計賬簿。
(二)經理義務的具體標準——與董事義務的比較
如果把公司經理和董事們放在一起作為同類的受信人,不在他們之間作出任何區別,也就意味著他們在公司中的機構職能和法律角色是一樣的,“會模糊兩者之間明顯區分的治理責任作用”[4](P.1597)。把經理看作是代理人,把董事會看作是委托人(公司)監管經理的重要載體,有利于我們區分這些組織在公司治理中的方案安排,故而有必要就董事義務與經理義務的標準進行比較分析。
1 忠實義務——應更加強調經理的奉獻因素
忠實義務要求代理人完全是為了公司(本人)的利益而行事,應該屬于道德義務的法律化。[7](P.172)但是,現實立法對于董事、經理忠實義務的落實是以一種要求其避免“利益沖突”的道德底限的情形式描述方法來進行規定,通過設置一些“消極義務”的高壓線,只要董事、經理不觸犯這些高壓線即為履行了忠實義務。可見,現實立法對于董事、經理等忠實義務的要求實際上是低標準的。
實際上,忠實義務可分為兩個層次——最小化情形(minimal condition)和最大化情形(maximum condition)。“最小化情形”要求忠實行為者“拒絕誘惑”,具體包括“不要背叛忠心的目標”,如不得私通、不得為敵人戰斗、不得崇拜外國貨等,這樣的忠實義務即是要求“不要背叛”;忠實義務的“最大化情形”包括了“奉獻的因素”(an eleme nt of devotion)和“肯定的奉獻”(affirmative duties of devotion),這是忠實義務更加積極的一個方面。Fletcher教授采用的忠實觀點是:“一個人樂意地、付諸于實踐地、徹底地奉獻于一個事業”。[8](P.26)這樣的觀點與James Hunter教授描繪的另外一個因素相吻合——“道德上的依附”,并且強調,這種道德上的依附行為不應該是抽象和概括的,而應該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8](P.26)如此一來,忠實義務“不僅僅是被否定性地定義,也有肯定性的因素”。
具體到經理的忠實義務,在20世紀末的一系列大型公司丑聞后,人們對公司內部的董事和經理(尤其是CEO等)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逐漸發現:現代公司中真正掌握公司實際大權的是公司經理,而非法律所安排的董事,而公司丑聞的制造主角卻恰恰是這些公司經理。故而進一步反思認為經理的忠實比董事的忠實更為重要和迫切,同時認為有必要提高對經理忠實程度的要求。“在后安然時代,公司治理丑聞呼吁改革,作為一個政策事項,信義義務法律可能呈現為州立法的方式來達到更大的經理責任。為了對付背叛和不忠誠現象,公司法和公司文化的標準應該在一個更加廣泛社會標準的范疇內予以重新考慮,將忠實作為一個公司法上的義務,同時也作為一個廣泛共享的社會標準。”故而“經理的忠實義務不僅僅是一個不背叛的程度,還要包括一個更加確定的奉獻(devotion)精神”。[8](P.27)需要經理促進公司的健康發展,不再是簡單地做到抑制住對公司的傷害,對經理來說還需要的是一個呵護義務或一個特定情況義務來最大化公司(或股東)的財產。
而就董事而言,其作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表意機關,并不具體參與公司的經營,而主要是代表公司行使委托人(公司)對代理人(經理)的監控職能。經理實際運行公司,作為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受信人,公司的經理應該承載著比董事要求更高的忠實義務,在公司經理的忠實義務中強調“奉獻因素”的積極要求不僅僅是一種道德呼吁,更是對其區別于公司其他主體(如董事)的忠實義務的一種體現。
2 注意義務——提高經理的注意義務標準
適用注意義務*雖然《重述三》將注意義務列為執行義務中的一個子義務,屬于代理人執行義務的一個方面;但是,在關于受信人的一般學理研究中,信義義務通常被分為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注意義務是作為與忠實義務相對應的一個重要方面。為方便學術對話及與一般理論體系相對應,在此特殊強調經理注意義務的研究。主要考量的是義務人達到怎樣程度的注意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義務人怎樣程度的疏忽構成對注意義務的違反。
(1)董事注意義務的標準——“重大過失”
英國高等法院大法官羅默有一個經典的表述[7](PP.182-183):a.一個董事在履行其職務時,他的技能水平應合理地從他的知識和經驗來判斷,他不必展示出比此更高的水平;b.一個董事不必對公司事務給予持續的注意。他的職責是定期地參加董事會議以及在偶爾有安排時參加董事會下屬委員會的會議,其職責具有間歇性質。然而他不必參加所有這些會議,盡管他應斟酌情況盡可能參加會議;c.董事的所有職責,考慮到業務需要以及章程細則之規定,可以適當地下放給其他高級職員。不存在可疑的根據時,一個董事有權利信任該高級職員會誠實地履行其職責,而不必對高級職員的過失承擔責任。英美法對董事的注意義務持較為寬松的態度,認為董事的行為只有構成重大過失始承擔責任,董事對一般過失不承擔法律責任。“他們承擔的注意義務的標準很難界定和說明,但是十分明顯的是,他們并不對他們所有的失誤都承擔法律責任,雖然,如果他們已承擔了更大程度的注意的話,他們可能已避免了此種失誤……他們的過失不必是沒有采取了所有的可能的注意程度所要求的疏忽行為;它必須是就商事眼光來看是嚴重的過失或重大的過失。”*Lagunas Nitrate Co. v. Lagunas Syndicate,[1899]2 Ch. 392,435.另外,在公司立法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降低董事的責任風險,使其在公司中盡量施展經營才能,美國許多州紛紛修改公司法以降低董事責任風險,如“允許章程條款取消或降低董事違反注意義務須承擔的金錢賠償”,“確定董事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董事違反注意義務而導致的個人責任的補償”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改變董事承擔個人責任的過錯標準”。[7](PP.232-233)
董事對公司事務的注意義務是一種低標準的要求,他們僅對嚴重的、重大的過失行為負責,對一般過失不負法律責任,對僅僅是判斷失誤的行為不負法律責任,對于自己不具備有關公司事務管理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而導致的公司損害不負法律責任。
(2)經理注意義務的標準——“一般過失”
在英美代理法中,早期的代理人注意義務的傳統標準是將代理人分為有償代理人與無償代理人,其中有償代理人負一般過失責任,無償代理人負重大過失責任。[9](P.193)但是,近期學界也開始鼓勵兩者并軌,不要因為無償代理人沒有從被代理人那里獲得報酬而減輕無償代理人的注意義務,建議對兩者統一適用一般過失責任原則。《美國代理法重述二》及評論中關于代理人注意義務規定:“代理人在與第三方的談判過程中的過失(negligence)對于其負委托人的義務而言構成了不當行為(misconduct)”*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 AGENCY (1958),第379條Comment-b.。
公司經理基本上是屬于有償代理人,按照傳統代理法的注意義務標準應該適用一般過失責任,按照現在代理法的觀點和立法,即使是無償的代理人也應適用過失責任原則,則公司經理更應該是負一般過失責任。“代理法上的代理人注意義務的通常標準是普通注意或者是一般過失,與董事相比較,這是一個更加嚴格的信義義務要求。因此,經理不僅僅要比董事盡更高的注意義務,同時,不像其他董事,經理們更有可能因違反義務而承擔個人責任。”[4](P.1640)“一般過失”即意味著經理違反了注意義務,在安然案的審判過程中,法官對于公司經理的注意義務的標準也是適用了一般過失標準。
綜上所述,董事的可責性標準為“重大過失”,而公司經理的可責性標準為“一般過失”,公司經理在履行代理事務時應該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
3 其他的執行義務
經理的執行義務,除了上述注意義務外,還包括遵守合同指示義務、在授權和合法指示范圍內執行事務的義務、善行義務、提供信息的義務、委托人財產隔離和保管商業賬簿的義務等。另外,其他的法規中也針對各種不同的情形規定了具體的經理義務。在此,筆者想重點提示其中的“提供信息的義務”以及《美國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規定的相應的新義務。
(1)提供信息的義務
現代公司之所以產生經理控制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對稱”,經理掌握公司的第一手信息,對于該信息的處理,經理可以瞞報、也可以進行對自己有利的加工之后再報。“安然事件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投資者——公司——高級管理者——其他管理者之間都不坦白,每個環節中都存在信息阻塞的問題。”[10](PP.1188-1189)故經理向公司及相關主體及時、準確地提供有效信息變得十分重要。
提供信息的義務要求公司經理應該準確地將公司經營過程中的各種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信息)及時提供給公司,因為公司是擬制的法律主體,故經理提供信息的一個重要對象就是董事會。同時,在提供信息的過程中,經理還有一個協助董事理解重要的公司報告信息的義務,包括有效地與公司董事公開商討一攬子的報告信息的義務。[4](PP.1631-1632)因為董事會成員由于時間和專業水平有限,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在第一時間準確地理解經理所提供的如財務報告等信息的真實性,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問題。更有甚者,為了蒙蔽董事,經理在提供信息的過程中,故意使用專業伎倆或者信息轟炸的方式,迫使董事很難準確理解所提報告的真實意思。如安然事件中,審辦人員發現,安然公司的經理并沒有將全部的信息提供給董事會,同時,經理以一種令人很難準確理解的方式提供信息。故要求經理協助董事理解重要的公司報告信息的義務,實為必要。
(2)《美國索克斯法案》的新義務
《美國索克斯法案》給經理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新義務,其中有兩個責任對于經理執行義務的理解尤其重要:第一,法案第302條關于“公司對財務報告的責任”,公司CEO和CFO必須在公司的季報和年報上簽字,保證報告中不存在對重要事項的任何錯誤、漏報以免產生誤導,簽字的負責人對建立和保持內控機制負責,向公司的審計師及董事會下屬的審計委員會披露關于內部控制的有關事項,評估內部控制并就內部控制是否發生變化進行解釋說明;第二,法案第404條關于“管理層對內部控制的評價”的規定,要求CEO等在每一份年報中必須包括內部控制情況的報告,申明公司管理層建立和保持充分的內部控制結構及相應的程序責任并包括對上一會計年度末內部控制結構及財務報告控制程序有效性的評價。這兩條在實施效果上,要求CEO等建立一個與公司之間的更加廣泛的信息報告鏈條,因為CEO等不可能檢查公司的每一項交易,這樣的要求迫使CEO們發展出一個可靠的信息系統,并且確信該系統的政策和程序得到下屬們的有效運行,議會和SEC的意圖明顯對準了公司的內部事務。
四 經理義務與經理契約——兼談義務豁免的底限
公司經理的信義義務是基于代理法,那么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公司經理的信義義務是一個純粹的授權性概念,還是帶有強制性因素?正如《重述三》中所規定的,代理人的一個重要義務就是按照委托合同的指示行事的義務。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委托合同是代理人得到授權的法定依據,委托合同的內容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代理人的權利內容。這個委托合同的內容是完全任意的嗎?可以對經理的信義義務進行無限制的免除和開脫嗎?
(一)信義義務已死——通過經理契約豁免經理義務的現狀
實際上,在公司相關的章程、決議和協議中對董事和經理的信義義務進行減免已經成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成文法和判例法也逐漸接受了這些豁免條款。有學者對西方公司的信義義務進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信義義務已死(Fiduciary duty is dead)”[11](P.993),因為“毫不夸張地說,現在絕大多數的公司章程都有排除經理對一些壞行為負個人責任的規定。雖然名義上,經理們要負忠實和注意義務,實際上在大多數案例中經理們沒有必要太過擔心,公司合同條款已經有效地排除了有意義的信義要求”。
依賴于信義義務原則控制經理行為是現代公司法律架構的一個前提,但是這個前提現在不再也不能如愿發揮作用。按照現在的法律規定,公司經理幾乎沒有理由去害怕法庭會認為他們違反信義義務而讓他們負責任。他們能夠獲得實質上的免責,法庭不會經常地挑戰經理的忠實,也不會二次考慮(second-guess)他們的管理決策。“純粹地用宣稱的忠實義務去禁止,用注意義務去執行非常有遠見的要求,這些公司的信義義務已經消失很久了。”[11](P.993)如果真是這樣的一種嚴重后果,那就不得不考慮這些合同中的免責條款的正當性。因為一旦信義義務因豁免安排不再對經理發生實質性的約束,那就意味著經理必然會產生腐敗現象,而這種腐敗是股東和社會大眾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有違法律精神的。“信義義務(尤其是注意義務)之所以能夠如此繁榮,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涵蓋有最小化政府干預的思想,但如果大量地減少這些義務的責任,遲早會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12](P.972)雖然,現在還沒有明顯地看出政府在這一方面強制干預的加強趨勢,但學者和法官們確實注意到了通過免責條款等大量減少經理責任的現象,他們也試圖通過法律解釋和理論探討的方式來更加正義地對該項制度進行剖析。
(二)義務豁免的底限在哪里——經理契約的強制性因素
委托協議的合同性質是否意味著董事會與經理的免責條款可以實行完全的意思自治?按照合同法的原理,一種可行的思路是該約定本身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但是公司法上很少有關于經理義務的強制性要求,而代理法上的代理人義務也逐漸被現實的判例所松動*如自我交易、與公司競業等情形,經公司章程或股東會同意后,逐漸地被認可。至于注意義務,則更多地被章程和合同等所排除,另外還包括商業判斷規則、責任保險和懲罰補償等制度的適用,致使現實中的案例少之又少。,另外,現實中條款本身的違法性也是經理聘任合同所事先考慮并被適當安排的,所以因條款本身的違法性而使得經理失去合同保護的現實性并不強。但是,筆者注意到了另外一條思路*Aaron D. Jones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提到過這樣的觀點。,即考察合同一方的董事會及董事身上的信義義務,如果董事會在合同中太過遷就經理,致使董事會完全失去對公司的控制而不能行使自身的監控職能時,則簽訂這樣的一種豁免約定是違反政策和法律的。
如在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v. QVC Network案中*637 A.2d 34 (Del. 1994).,1993年夏天,Viacom.Inc就收購Paramount的事宜進行談判,9月12日雙方簽訂了鎖定性的一系列合并協議,為避免觸發Paramount章程中反收購的“毒丸”條款,協議規定該項條款將作相應修改。但另一家公司QVC Network.Inc幾乎同時發出了對Paramount的收購要約,幾番爭奪,Viacom把總出價提高到93億美元,但仍比QVC的出價少13億美元。這時,Paramount宣布接受Viacom的要約,并修改“毒丸”條款以防止QVC的要約得到接受。在本案中,法庭認為,Paramount公司董事會與Viacom達成的挑選合并對象、防御措施的一系列協議應該是無效的,因為那些協議阻止了Paramount公司董事會履行其當公司的控制權交易正在處于預期狀態時的信義義務。“協議達到了不符合信義義務的程度,那這些協議是無效的,不具有執行力。”*637 A.2d 47 (Del. 1994).最后,以合同形式簽訂的防御措施被否決,法庭以給原告簽發禁止令的方式進行救濟,阻止了這起合并。本案中,當QVC Network出價更高時,Paramount董事會的信義義務要求其應該考慮QVC的報價,但Paramount董事會與Viacom的協議則排除了董事會的這一考慮,故而協議本身違反了董事會的信義義務。按照這一原理,一個董事會聘任了一個經理,雙方簽訂了聘用協議,“如果協議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不合理的或者是因為這個協議對經理(CEO)太過尊敬、賦予了太多的保護,導致事實上經理掌握了所有的權力,董事會卻不再能夠履行其法定的信義義務來監控經理和執行公司的相關事務時,這樣的一個協議可以認為是違反了董事的信義義務的”。沿著這樣一條思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如果經理聘任協議中給經理豁免責任的約定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即因為該協議使得公司董事會不再擁有足夠的監督和控制機制,則該協議違反了董事會的信義義務,這樣的協議應該是無效的。
在經理契約中對經理義務的豁免應該是有強制性因素的,這就是義務豁免的底限——不能因為給經理太多的豁免而使董事會違反信義義務,不能因為太過遷就經理而使董事會失去監控職能。這既是對經理義務豁免的一個底限,也是公司法保證維持整體治理機制架構的一個底限,應該得到支持。
在公司治理架構中,公司經理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法律研究也應該越來越關注公司經理獨特的義務和責任體系。“義務責任規則確實不是唯一的,但可能是最重要的規范(shaping)經理行為的因素。”[13](PP.175-176)隨著公司中經理與董事之間關系的逐漸厘清,重視公司經理獨特的法律地位,構建獨立的、區別于董事義務的經理義務體系將成為公司立法和公司法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不僅是為了一個知識點的重新整理和歸納,更是為了整個公司治理體系的切實合理運行。
[1]Melvin Aron Eisenberg. Legal Model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fficers, Directors, and Accountants[J]. California law review,1975,63.
[2]L S Sealy. Fiduciary Relationships[J]. Cambridge Law Journal,1962,70.
[3]J C Shepherd. Towards a Unified Concept of Fiduciary Relationships[J]. Law Quarterly Review,1981,97.
[4]Lyman P Q Johnson, David Millon. Recalling why corporate officers are fiduciaries[J].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2005,46.
[5]Andrew D Shaffer. Corporate Fiduciary-Insolvent: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Your Corporate Law Professor (Should Have) Warned You About[J]. 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e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e Law Review,2000,(8).
[6]范健. 德國商法[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7]張開平. 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Lyman Johnson. After Enron: Remembering Loyalty Discourse in Corporate Law[J].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2003,28.
[9]徐海燕. 英美代理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10]Donald C Langevoort. Agency Law Inside the Corporation: Problems of Candor and Knowledge [J].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2003,71.
[11]Celia R Taylor. The Inadequacy of Fiduciary Duty Doctrine: Why Corporate Managers Have Little to Fear and What Might Be Done About It,[J]. Oregon Law Review,2006,85.
[12]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Duty of Car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J].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1990,51.
[13]Daniel R Fischel, Michael Bradley. The Role of Liability Rules and the Derivative Suit in Corporate Law: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 Cornell Law. Review,1986,71.
(責任編輯:沈松華)
AStudyontheDutiesoftheCorporationManagerComparedWithThoseoftheBoardMember
WU Wei-yang
(School of Economic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The concept of “fiduciary” under the common law system includes director and board member, which therefore causes the mix of duty and liability of board members and managers. A board member is not an agent of a corporation. Instead, a manager shall be the agent of a company. The duty system of manager shall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Agency Law. Compared with board member’s duty of loyalty, managers have higher loyalty duty and the standard of duty of care is ordinary negligence. The bottom line of a manager agreement is not to cause the board member to lose his supervisory function as a result of exempting the fiduciary duty of managers.
fiduciary duty; standard of duty; bottom line of exempt
2009-09-11
吳偉央(1980-),男,浙江臺州人,上海證券交易所與華東政法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后。
D912.291.91
A
1674-2338(2010)02-00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