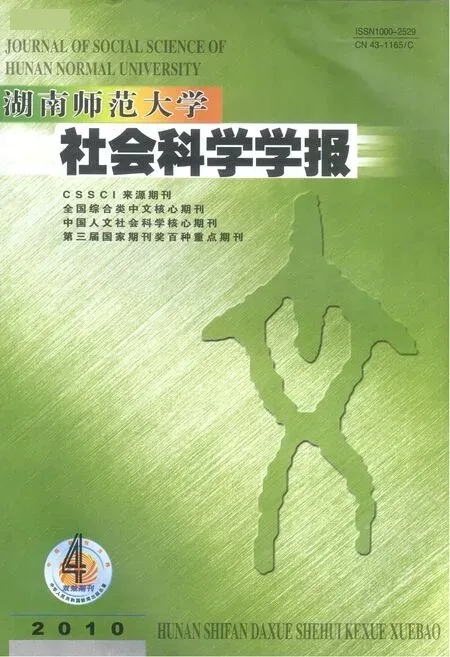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關于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報道的分析
吳果中,鄧雙喜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
——關于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報道的分析
吳果中,鄧雙喜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西藏“3·14事件”是大眾傳播媒介與意識形態相互構建的事件。從西方傳媒的生產流程,可以探尋西方國家的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之間象征形式的建構謀略,從而探究其謀略背后的話語權力關系、權力形式以及媒介與國家的互動等,為揭露西方國家對該事件的報道提供獨特的分析視角。
西藏;3·14事件;大眾媒介;意識形態
按照英國社會學家約翰·湯普森的看法,現代文化的傳媒化——現代社會的象征形式已越來越經過大眾傳播的機制和機構所媒介——是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個中心特征。“在現實生活中,它們(指大眾媒介,引者)無時無刻不在為人們編織著信仰、價值和集體認同……簡而言之,大眾媒介已成為支配意識形態的核心體系。”[1](P9)也就是說,大眾媒介每天都在用語言圖像娛樂、新聞以及廣告來建構概念,以此來表現并宣傳其意識形態。[1](P9)可以說,大眾媒介已成為現代社會中一種社會控制的新機制,統治集團的思想可以通過這種機制得到宣傳和擴散,并用來控制從屬集團的認識。因此,大眾媒介與主流經濟和政治力量的聯合為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傳通制造了一個新的手段。
所謂意識形態,具體來說,并不是盛行于當代研究中的“社會膠合劑”,也不是某種象征形式或象征體系本身(保守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的特點或特征,而是借用了湯普森的理解——意識形態就是服務于權力的意義。他認為:“在研究意識形態時……我們所關注的是象征形式是否、以何種程度以及如何在它們制作、傳輸和接收的社會背景下被用于建立并支持統治關系。”[2](P3,7)而象征形式指的是由主體所產生的并由主體和別人所承認是有意義的建構物的一大批行動、言詞、形象與文本。湯普森對于意識形態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慮問題的新思路,“使我們注意意義被調動起來服務于統治集團和人們的方式”。
于是,當西方媒體對西藏拉薩“3·14事件”進行不實、歪曲報道的,意味著以“客觀”、“真實”、“公正”為詮釋框架的新聞理論再次遭到質疑而引起中國輿論的強烈譴責,并由此而斷言:新聞客觀性在國際壟斷媒體資本時代呈現出“式微與掙扎”、令人失望[3]的時候,試圖找尋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之間象征形式的建構謀略,并深度解釋這些報道背后連結的各種話語權力關系和現代國家中體制化了的權力形式以及媒介與國家的互動等等,這或許是一種比較獨特的研究視角。
意識形態表達模式與象征建構典型謀略
要描述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的具體互動,我們不得不思考:媒介信息的意義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大眾媒介生產的意義以什么方式服務于統治關系的權力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態?西方媒介對西藏“3·14事件”的報道,從現有的各種報道形式看,它們建立了哪些意識形態表達模式以及相應的象征性建構謀略?
合法化—合理化模式。根據馬克斯·韋伯和湯普森的分析,意識形態是可以通過將統治關系描述為合法而得以運行的。合法的,往往是正義的,它依據政策法令、神圣的永恒傳統和卓越的領袖權威,依靠合理化的象征建構典型謀略,“構建一系列理由來設法捍衛或辯解一套社會關系或社會體制”[2](P69),贏得支持和信賴。以 BBC、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為主流的西方媒介對西藏事件的報道,充分建構了這種敘事模式。查閱大量的報道文本就會發現:西方大眾媒介對于西藏“3·14事件”的報道,就是建立在一個達賴喇嘛是神的化身和英雄領袖的神話上,盡管這是“西方人對東方的無知和偏見制造出來的一個神話”[4](P7)。《紐約時報》在3月14日題為Monk Protests in Tibet Draw Chinese Security的報道中寫道:“The Dalai Lama has said thathe acceptsChinese rule butthatTibetansneed greater autonomy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這建構了一個安分守己、顧全大局而又追求宗教自由的達賴喇嘛形象,從側面抨擊了中國政府的不合理。在3月20日題為In Tibetan areas,parallel worlds now collide 的報道中寫道:“All Tibetans are the same:100 percent of us adore the Dalai Lama.”(所有的藏族人都是一樣:我們100%崇拜達賴喇嘛);在3月22日的報道中又寫道:“He has been pressing……to return to China to advocate for greate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for his followers.”(達賴喇嘛一直在為自己的同胞尋求更大的文化和宗教自由)。
以上的一系列象征形式正好印證了學者的觀點。溫哥華的華裔學者丁果和加拿大的華裔學者趙月枝在對話中談到:在西方媒體眼中,達賴喇嘛不僅是一個政治角色,更多的是“心靈導師”的角色,他不僅代表自由主義人權的“共識”,而且是世界級的精神文化領袖。這樣,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權的一個重要符號,深入到民意的基層,形成西方媒體深層的預定“共識”[3]。因此,西方媒體的象征形式中多是維護達賴喇嘛形象的描述,他是西藏宗教合法的管理者和領袖,他所倡導的理念和措施以及他們的抗議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都是合理的,理應受到全球的支持和擁護。相應地,從另一側面彰顯出,中國政府對達賴集團的抗議給予打壓是不合法的,是對自由和人權的侵害,試圖以此激起全球的譴責。于是,與達賴“親和、友愛”的形象相比,西方媒體中的中國領導人形象是“殘酷、無人性的”。
虛飾化—轉義模式。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也可通過掩蓋、模糊語言或借喻等象征方式加以表達,在注意力轉移或將一事物加以美化的描述中,促進社會關系的虛飾化,更有效地建立和支撐統治關系。含糊其辭是這種模式中常用的建構謀略。對于西藏“3·14”事件的報道,以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為例,從3月14日至9月12日的報道、標題和正文中充滿了“protester”的稱謂,將達賴集團視為“抗議者”,將其藏獨行動視為“抗議”,試圖以中性詞的含義(在西方媒體中似有突出褒義之意)掩蓋暴動者的“打、砸、搶、燒”行為及其對于社會的破壞,從而喚起受眾的同情和對施行鎮壓者——中國政府的抗議。又如《紐約時報》3月15日的報道聯想實施“種族滅絕”的蘇丹,與中國的西藏事件相對應。
為了更有效果地轉義,西方媒體大量地采用不確定新聞源和負面新聞源提供的信息。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負面和簡單化是有研究結果可以證明的。例如,古德曼在199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道中,24%是有關嚴重危機的,70%和沖突有關,32%和暴力有關。[5](P380)有人專就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報道的信息源使用做了詳細的統計分析,發現大部分信息并非媒體直接采訪或親自調查,多采用“西藏流亡政府”、發來郵件的藏區民眾、“目擊者(witnesses)”、“游客(a tourist)”等不確定的信息源。而且,西方媒體更傾向于選擇境內外“藏獨”分裂勢力、對“西藏問題”持批評態度的西方政客所提供的信息。[6]它們技巧地將中方和偏中方的話語權完全轉交給達賴方和批中方,借用“達賴喇嘛(Dalai Lama)”、西藏“人權組織”、“藏青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的語言,構造一個虛飾化意識形態表達的互動場所。
美化也是這種建構模式較常用的手段。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美國政府向世人宣稱:龐大的軍隊和大規模的坦克裝備開進伊拉克并不是“入侵”,而是“解放”和“拯救”。2008年3月14日,中國西藏發生暴亂事件,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再次以救世主和自由神的化身,美化達賴集團的“和平與 忍 耐 ”(peace and tolerance)、“ 和 平 游 行 ”(peaceful marches)等,稱贊達賴集團在抗議中的“無罪”(innocent)、“堅韌”(tough)、“勇敢”(brave)。在美化一方的同時,也就丑化或攻擊了對方。所以,西方媒體在描述中國政府的平息行為時,更多的是“大屠殺”(massacre)、“鎮壓”(crackdown),手段是“殘忍的”(brutal)、“鐵腕的”(iron-fisted)。
梳覽西方某些媒體的報道,有學者從話語分析的角度認為它們基本沒有采納中國的“分裂國家”和“違法犯罪”的話語包,而是訴諸“種族矛盾與對立、侵略與反侵略”的話語包。話語包中顯示的符號意義自然便有:種族屠殺、種族滅絕、種族仇恨、血腥鎮壓、武力侵占、民族領袖、流亡政府等等[7],西方媒體以文字修辭手法來使用語言或象征形式,在“美”與“丑”的意義轉換中,建立起所要表達的意識形態,對“中國沒有人權”的一貫譴責。
《泰晤士報》更是直接摘自《紐約時報》或其網站,在標題之前大多標注“From The Times”或“From Times Online”,這樣,將美國意識形態的虛飾化—轉義模式進行了復制生產,在時間、空間、規模等方面進一步延伸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摘錄表達了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此事的一致性認同和共通的意識形態,形成強大的輿論規模,重擊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分散化—排他模式。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支撐還可依靠分散對統治集團造成巨大挑戰和破壞的人或集團,使之與主流形成對立。這種意識形態的運行模式,可以通過排他的象征建構典型謀略來實現。首先構造一個敵人,把它描述成罪惡的化身,引起世人的一致攻擊,從而團結起來共同與之對抗。西方媒介參與西藏事件的報道,較多地采用了這種模式。如《華盛頓郵報》3月18日在題為“Far-Flung Tibetans Find Unity In Protest”的報道中指出,所有的藏人都擁護達賴喇嘛,所有的藏人都希望在抗議中團結一致。文中把“所有的藏人”看成是向全中國挑戰的他人,而且把這種對立夸大成代表民主、人權、自由的西方社會與中國政府管制的沖突勢力,因此把“所有的藏人”視為賦予中國政府對民主自由規制的理想人物,而試圖把中國政府的平息行為視為一種對正義的壓制,中國成了更多世界的敵人,遭至強大的抵抗。
探究中國西藏歷史,“西藏問題”只是西藏上層農奴主階級追求特權的“流亡政府”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的對立,他們并不能代表所有藏人。而在西方媒體中,“西藏問題”就是中國政府與藏族人民抑或漢族與藏族的對立。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is irreconcilable”(漢族和藏族之間的關系是勢不兩立的)[8]。
運用這種模式的更為明顯的表現是:分化。西方媒體在西藏事件報道中盡可能表明:西藏不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不屬于中國政府的管制范圍,將藏族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它們盡力鼓吹西藏與中國政府的分離,阻止中國政府在西藏有效地行使權力。如CNN網站3月14日題為“Clashes leave 10 dead in Tibet”的報道結尾寫道“China go home!”(中國滾蛋!)
話語霸權與意義輸出
在意識形態的運行模式和西方媒體的象征建構典型謀略形成的互動場域中,我們似乎已能意識到意義和權力互相影響的關系話題。
米歇爾·福柯曾經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與規訓社會相對比的控制社會。在控制社會中,“權力已伸展到社會結構的每一個神經末梢,伸展到社會的發展過程之中。社會已完全被納入到這種權力之中,如一個單一體般對權力發生反應。權力已表現為一種控制,它伸展到民眾的意識和肉體的最深處,同時也跨越社會關系的全部”[9](P25)。西方大眾傳播媒介通過文字、符號、意義的意識形態生產與建構,承載著種種權力和政治化生態,形成新的權力規則的邏輯和結構,在政治邏輯和文化邏輯的整合框架中,一個帝國的主權形式得以確立,并被近年來信息網絡聯絡在一起的工業生產中的通訊交往勞動所規約。“權力,在生產之同時,也在組織;在組織之同時,也在自我表述,宣稱自己為權威。語言,在實現交流之同時,不僅在生產商品,更在創造主體,把他們固定在各種關系中,向他們發布命令。通訊交往工業把象征和想象一起織入生態政治之圖景中,不僅使此二者為權力服務,而且實際上已把它們融入權力的職能。”[9](P33)因此,可以說,西方媒體對于西藏事件的報道,遵守對華報道慣用的意識形態框架,運用情緒化了的文字、不真實的語言描述、涂改了的圖像等交織了一張服務于權力的意義生產網絡,這是西方媒體服務于意識形態運用自如的游戲規則。
在大眾傳播媒介居于社會中心位置的全球化時期,以新聞媒體和宗教組織為實體的道德干涉遠甚于軍事干涉、法律干涉。西方媒體早已意識到這一點,并以虛假姿態,“為了確定普遍需要和捍衛人權而竭盡全力。它們通過自己的語言與行動,首先把敵手界定為匱乏,然而在敵手身上釘上罪惡之名”[9](P36)。西方媒體所宣稱的,達賴集團暴亂是為了人權和自由而戰的“和平示威”,中國政府卻對此施以暴力(violence)、酷刑(torture)和血腥鎮壓(crackdown)等,就是這種以新聞媒體和宗教組織為實體生發強大譴責力量的道德干涉,干涉中又總是建立或強化自己的意識形態。
由此,西方大眾媒介和意識形態建構起了特殊的親密關系。大眾媒介并不是如英國學者湯林森所說是中性地、平等地擴散而沒有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于第三世界,而是如李金銓等學者所說:“國際新聞的生產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媒介按照民族利益和文化假設將新聞國內化。”受到了權力結構、文化形態和政治經濟利益的制約,西方各國媒體通過主流意識形態折射、再現同一事件時,存在著顯著不同,這就是“內在化”的過程。[10](P286,294)西方主流媒體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在戰爭時期,在對外關系中,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美國的媒體和政治權力一般都保持著密切的‘情人’或‘共生’關系,而不是流行觀念中的總是對政治權力制衡和監督的‘看門狗’”。[5](P227)在外交和國防上,媒體幾乎和政府亦步亦趨,基本認同。在海灣戰爭期間,CNN成為美伊口頭攻擊的舞臺,甚至為最后的武裝沖突鋪路。伊拉克戰爭中美英政府導演的一幕幕假新聞,嵌入了近600名美國和世界主要媒體的記者,使他們從英美的立場報道戰爭。在中國西藏暴亂事件中,英美政府和主流媒體的“情人”關系再次生效,依然采用了“偽事件”的制造和歪曲報道的傳播手段,“可信的謊言”加上“共謀的媒體”[11],西方媒體將對中國西藏事件的報道毫無保留地意識形態化,服務于自己的統治集團利益和社會結構關系。
利用大眾媒介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是西方媒體固有的傳播框架之一。“意識形態在性質上就是霸權的,就是說它必定服務于建立和支撐統治關系,從而重建一個有利于統治人物與集團的社會秩序。”[2](P76)對于西藏事件的報道,西方媒體從宗教自由、人權法制、民俗民風等方面尋找題材,賦予西方化的解答,以攻擊中國政府。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借助于高技術手段進行大批量生產和通過大眾媒介廣為傳播的西方文化,其實是意識形態控制的新形式。在世界范圍內將文化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至少是美國文化帝國的一種延伸。[4](P9)西方媒體及政府對西藏事件的干預,再次體現了自“9·11事件”以來帝國“危及整個世界的暴力邏輯”,而美國是“這種暴力邏輯發動機的主要元件”[12](P15)。在西藏事件的報道中,美國主流媒體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聯社等都使出各種傳播路數,或選擇不實、負面新聞源;或含糊其辭地美化達賴喇嘛,分化中華民族與藏族的關聯;或細致地描述藏民的死亡卻忽視暴民的暴亂行徑;或肆意篡改圖像,歪曲本有的事實等等,從而按照固定成見建構不同于西藏事件客觀事實的媒介世界。于是,為權力服務的大眾媒介的意義生產成為了文化霸權和話語霸權下的意識形態表達。借用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陣勢,從制造對立來施加壓力而最終獲得國家利益,這是西方政府行事的慣有邏輯,西藏“3·14事件”再次提供了證詞。
[1][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張 銳譯)[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2][英]約翰·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譯)[M].上海: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8.
[3]趙月枝.為什么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J].新聞大學,2008,(2):9-16.
[4][英]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張巨巖.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6]張成良.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相更遠[J].新聞記者,2008,(5):7-11.
[7]曾慶香.西方某些媒體“3·14”報道的話語分析[J].國際新聞界,2008,(5):25-31.
[8]In Tibetan Areas,Parallel Worlds Now Collide,March 20,2008,The New York Times.
[9][美]麥克爾·哈特.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譯)[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10]李金銓.一起多國視野中的全球性“媒介事件”[A].載[英]詹姆斯·庫蘭.大眾媒介與社會(楊擊譯)[C].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11]英國《衛報》評論語,2003年4月4日。
[12][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控訴帝國(肖維青譯)[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校:彭大成)
Mass Media and Ideology——Analysis of Tibet March 14th Event Reported by the West Press
Wu Guo-zhong,DENG Shuang-x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 this article it is considered that March 14th event i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mass media and ideology.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social-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has been mastered and used in the ideology among three aspects of west mas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production/transmission,construction and receive/occupation,the article tries to infer the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which symbolize forms between mass media and ideology,and explain in depth the various discourse rights behind these reports and forms of rights which institutionalized in modern countr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the nation.It gives an unique view to analyze the report about March 14th event.
Tibet;march 14th event;mass media;ideology
G206.2
A
1000-2529(2010)04-0136-04
2010-01-05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外籍人士在近代湖南的辦報活動”[08YBB168]
吳果中(1969-),女,湖南安化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鄧雙喜(1984-),女,湖南城步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