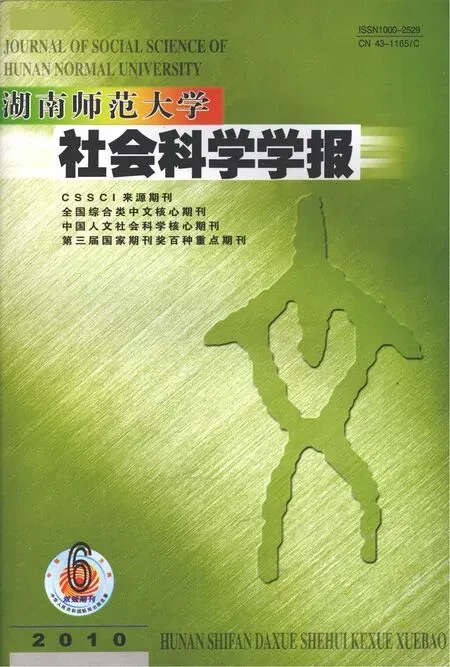論宗教對世界倫理建構的作用及其局限
聶文軍
(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
論宗教對世界倫理建構的作用及其局限
聶文軍
(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
宗教與世界倫理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關聯。在當代,宗教對于世界倫理的建構既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又存在著很多的局限。我們應充分認識世界倫理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在人類生產實踐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步解決這一歷史性課題。
宗教;世界倫理;局限
一、全球倫理的歷史發展與當前的主要論爭
世界倫理或普遍倫理就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倫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宗教與世界倫理都有著密切的關聯;人類對世界倫理的追求和實踐決不是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的事情。世界倫理曾經是人類道德的烏托邦追求,遠在現當代社會之前,它即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希臘化時期的斯多葛派對“世界主義”倫理的追求,即是世界倫理的一種表現;就基督教文明主宰歐洲社會發展的中世紀而言,西方社會把傳統的基督教倫理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倫理;中國古代儒家的普遍倫理也是世界倫理的一種表現形式。就理論自身的邏輯來看,康德建立在純粹理性基礎上的義務論倫理學毫無疑問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倫理學,康德的理性主義倫理學因其極端的抽象性和形式主義而未能在現實中得到切實貫徹。這些都成為當代世界倫理運動和理論研究的歷史資源。
從歷史的發生發展來看,現當代的世界倫理首先是一種現實的實踐活動,然后進入到理論研究的領域。1948年12月,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即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世界人權宣言》即呈現出一定的世界倫理的性質。20世紀70年代,宗教界也開始了建構世界倫理的積極努力。1970年國際宗教界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宗教和平會議”上所發表的宣言,已經較為明確地蘊涵了朝向世界倫理的積極努力[1](P81-82)。1993 年,“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發表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使世界倫理運動明確進入了人們的視野。1995年,在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的領導下,“全球政治管理委員會”在發表的一份名為《全球是鄰居》的報告中倡導以“全球性的公民倫理”作為不同國家與文化之間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道德基礎;同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領導的“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呼吁建立一種由共同的倫理價值和原則構成的“全球倫理”。1996年,由30位前任政府首腦組成的“全球互動委員會”主張制定一套“全球倫理標準”以應付人類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普遍倫理計劃”的研究項目,多次召開國際會議,組織多學科的專家學者探討建立全球性的普遍倫理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現當代的世界倫理運動雖由宗教界發起,而發起這一運動的宗教界正確地把世界倫理看作是非局限于宗教和超越宗教的“一種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標準和態度”。從歷史的發生發展和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來看,世界倫理雖然主要發軔于宗教,卻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宗教的范圍。
究竟什么是世界倫理或全球倫理?20世紀末世界宗教議會大會所給予的界定是:“我們所說的全球倫理,并不是指一種全球的意識形態,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現存宗教的一種單一的統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種宗教來支配所有別的宗教。我們所說的全球倫理,指的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沒有這樣一種在倫理上的基本共識,社會或遲或早都會受到混亂或獨裁的威脅,而個人或遲或早也會感到絕望。”[2](P12)雖然世界倫理在現當代主要發軔于宗教界的努力,但世界倫理卻是超越宗教的。“一種適用于全人類的倫理是必不可少的。在過去的幾年中,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當這個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甚而互相斗爭的倫理學地帶,那么,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才有一個生存的機會,這樣一個世界需要這樣一種基礎倫理;這樣一個世界共同體無疑不需要一種統一的宗教或統一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卻需要一些相互有聯系的、有約束力的準則、價值、理想與目標。”[1](前言P4)
目前關于世界倫理的問題存在十分尖銳的爭論。爭論的所指主要是關于世界倫理的界定問題、世界倫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問題、世界倫理的內容和如何建構等問題。我認為關于世界倫理的界定、內容和如何建構等問題不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人們雖然關于這些問題存在著大量的分歧和爭議,但這些問題能夠在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過程中逐步求同存異,達成廣泛的共識從而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我認為關于世界倫理最根本的問題是世界倫理是否可能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世界倫理的建構是不可能的,倫理相對主義特別是文化的倫理相對主義基本上贊同這一觀點。大多數學者主張世界倫理是可能的,即使不同文化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有所不同,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支配人們行為的根本道德原則是不同的。世界倫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問題主要不是一個理論的、邏輯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實踐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世界倫理的發生發展從根本上有賴于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們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范圍受制于其生產力的發展進程,隨著生產力的逐步提升,各個相互孤立的地方性的共同體便會逐漸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P88)。人們的活動愈益具有世界歷史的性質,也就是愈益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不僅“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5](P276)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文學”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倫理等內容;具有普遍性的真正人類的精神產品的形成必定吸納了各民族精神產品的積極內容;作為精神產品的倫理的世界性建立在人類物質生產的普遍性或世界性基礎上,伴隨著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倫理的世界性內容必然逐步增加。
實際上,世界倫理的建構早已超出單純理論的思辨,它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迫切的客觀的需要。天主教著名神學家漢斯·昆在《世界倫理構想》一書的《前言》中嚴肅地指出,“沒有世界倫理,則人類無法生存。”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以大量的客觀事實揭示了我們對世界倫理的需要程度:“每一分鐘內全世界各國要為其軍備花費180萬美元;每一小時內有1500名兒童死于饑餓或死于饑餓引起的疾病;每一天內就有一種動物種類或植物品種絕種;80年代的每一星期中被捕的、受刑拷打的、遭殺害的、被迫逃難的,或是被專制政府用其他手段加以迫害的總人數已經超過歷史上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外的任何時候,……面對這些還可以任意加以補充或者替換的數字,難道還需要用什么繁瑣的理由來說明我們為什么為了生存需要一種全球性的倫理?”[1](P3)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告訴我們,一種讓我們共同生存和生活于同一個地球同一個世界上的世界倫理乃是當務之急。當然,不僅當今世界存在的各種急需解決的問題需要世界倫理的“出場”,而且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和生活實踐更需要世界倫理的“出場”。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之一的宗教對世界倫理的追求,不過是以特殊的形式從根本上反映了整個人類社會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曾明確地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4](P33)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既然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就表明完成這一任務的客觀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正在形成;當然,完成這一巨大的歷史任務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與此相似,建構世界倫理的任務既已提出,這意味著完成或解決這一任務的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或者這一客觀條件正處于生成完善的過程中。
就世界文明本身的歷史發展來看,真正意義的世界倫理決非中世紀的基督教倫理和中國古代的儒家倫理,而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不斷發展的產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具有世界性的本性,它不僅要把世界各國各民族納入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之中,而且試圖把資本主義所需要的道德體系推廣到全世界。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由于社會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極大擴展,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愈益多元化,由此又造成了倫理的多元化和倫理相對主義的興盛,似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導向了一種與世界倫理相對立的倫理格局。在現當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人類世界對普遍倫理的需要和建設又再次呈現在我們面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確乎走出了辯證的正反合的過程。
二、宗教對世界倫理建設的積極作用
宗教對世界倫理的積極作用可從如下幾方面來看。
首先,宗教的超越性可以為世界倫理的建設提供強勁的精神動力。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使得單個民族、國家和地區性組織都無力解決諸多的全球性問題,這些世界性問題或世界性危機的解決不僅需要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廣泛合作,也離不開世界各宗教的攜手合作。從宗教理論本身來看,各宗教的主要目的在于出世,它們更多地是追求一種彼岸世界,追求一種超越現世的精神境界,所以,宗教總是具有一種強烈的超越性。宗教的這種超越性不僅能夠使得其信徒擺脫日常世俗生活中的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從而化解沖突,造成社會的普遍和諧,而且對于非宗教信徒也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促進和提升他們的道德境界。宗教的出世倫理(神學倫理)和在世倫理(世俗倫理)都服務于宗教對彼岸世界的追求和實踐,宗教總是力圖超越現世、超越現實。世界各宗教超越現實、超越現世的宗教倫理——包括神學倫理和世俗倫理——能夠為現當代的人類建構和實踐世界倫理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其次,宗教可以為世界倫理的建設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宗教對世界倫理建構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在全世界60多億人口中有宗教信仰者幾近50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在世界范圍內都得到廣泛傳播,它們各自的教義和倫理規范在這些廣大信眾中產生了廣泛深入的影響,充分利用和挖掘其中的思想資源將對世界倫理的建構發揮十分有益的作用。從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基本教義來看,它們的倫理內容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基督教倡導自由、仁愛、平等、正義、尊嚴、慈善、忍耐等理念,佛教倡導慈悲利他、眾生平等、止惡修善、謙忍和順等理念,伊斯蘭教倡導自由、自立、悔罪、良知等理念,它們在對信徒的世俗生活的倫理要求上表現出很大的相似。被視為道德金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眾多宗教中都有相似的表述,基督教經典指出:“無論何事,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圣經·馬太福音》17:12)伊斯蘭教經典也曾這樣言說:“你自己所討厭的,不要施與別人;你自己所喜歡的,施及于人。”(《古蘭經》49:13)與此相似的話語在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經典中也有相應的表述。這就為當今世界倫理的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最后,各宗教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寬容有助于世界和平,從而為世界倫理的建設創造必要的前提。從當今世界的現實來看,作為建構世界倫理必要條件的世界和平的存在,不僅依賴世界各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宗教的積極參與。我們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說,當今世界若沒有各宗教之間的和平,決沒有世界的和平。世界各種宗教首先要消除隔閡和隔膜,倡導對話和交流,這種對話和交流需要把對自己的信仰立場的堅持和對他人(他種宗教)的理解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能切實地實現各宗教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寬容,這樣至少可以減少宗教沖突,促進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或和解,從而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貢獻,間接地為普遍倫理或世界倫理的建構做出貢獻。
三、宗教對世界倫理建設的局限性
世界倫理的建設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歷史任務。宗教對于世界倫理的建構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我們既不能片面夸大,也不能予以否定。從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宗教對于世界倫理的建設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從理論層面上來看,宗教的消極性從根本上制約了它對世界倫理建設的作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5](P666-667)“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3](P2)宗教是對物質世界和社會存在的歪曲反映,它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是不平等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壓迫和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它雖然在一定條件下也滿足了廣大群眾的精神生活需要,但更多地是起到了麻醉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意志的消極作用。無論哪一種宗教,都不能克服其追求出世與不得不在世的根本的內在的矛盾,而且都是把在世作為其出世的手段,這就決定了宗教不會把自己的重心和注意力放在解決現世社會與生活的矛盾上,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逃避現實的道路。從唯物史觀的觀點來看,希望通過各宗教的合作或形成一種普世宗教來建構當今時代的世界倫理,無論從理論層面上還是從現實層面上看都有很大困難。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各個宗教都既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表現出積極的、有利于社會文明進步和道德建設的作用,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現出消極的、有礙社會文明進步和道德發展的東西,“任何一種大型世界宗教除它們那些或多或少的偉大的功績史外,也都還有一部丑聞記錄”[1](P47)。宗教的消極性可以說比比皆是,“宗教可以制造恐懼、狹隘、不寬恕、非正義、失意以及社會性的禁欲;宗教還可以使不道德的事、社會上不良現象以及一個民族中的或民族之間的戰爭合法化,并對之加以鼓勵。”[1](P59)應當說,從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宗教的消極性是根本的,長期的。宗教對世界倫理所發揮的作用有賴于社會各階層的進步要求和發展要求,有賴于全社會對宗教中所蘊涵的積極因素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正如漢斯·昆清醒地指出的,“如果我們不能為倫理的綱領贏得來自政界、經濟界以及金融界的代表人物們的支持,那么,不論所有宗教與教會的初衷有多好,他們提出的倫理要求都將落空”[1](P5)。通過靜態地比較各宗教而獲得的其在倫理上的共同點并非就能真正成為世界倫理或普遍倫理的內容,因為通過比較所得到的共同的宗教倫理并不能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遍有效地實行,它們看起來是共同的宗教倫理,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實質上仍然各自在極其有限的范圍內發揮作用。各宗教所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行為倫理準則——通過抽象地比較而形成形式上的世界性或普遍的倫理準則——各自建立在自己特殊的哲學和神學理論基礎上。而各宗教的哲學和神學理論基礎是很不相同的,對看起來是共同的行為倫理準則的遵行在不同的宗教中往往具有極為不同的價值和意義,這些抽象的共同的倫理準則一旦運用于各自特殊的宗教社會中,必然受到各宗教所具有的哲學和神學的巨大制約,人們會根據它們在本宗教中的價值重要性進行理解、操作和取舍。如果各宗教不在哲學和神學基礎方面達成共識,就很難使這些行為倫理準則得到真正的普遍遵行;在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尚未達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要各宗教在其哲學和神學基礎方面自覺地作出改變或調整,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其次,從歷史與現實的層面來看,各宗教之間、宗教的各教派之間的矛盾沖突使得宗教對世界倫理的作用非常有限。各宗教之間的矛盾沖突、宗教的各教派之間的矛盾沖突既包括認識上、觀念上的差異與對立,也包括行為實踐上的差異、沖突與對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宗教的產生和存在有著極其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宗教觀念的差異和對立不僅會在不同程度上引發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民族或種族的沖突,而且宗教的差異和對立常常直接反映了民族、社會或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世界倫理或普遍倫理的建設,首先必須有世界和平的存在,世界和平當然首先取決于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狀況,而不是取決于宗教的主觀努力。不同的宗教建立在極為不同的哲學或神學理論的基礎上,各個宗教通常把自己視為最高的、終極的真理,主張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常常表現出宗教認識和實踐上的優越性、獨斷性和排他性,從而造成嚴重的宗教偏執和宗教狂熱。要在哲學層面或宗教神學層面消除各宗教之間的理論差異或對立,把各種宗教看作對一種“終極實在”的不同認識,實現各宗教之間的多元平等,不僅需要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領袖有改革宗教、創新宗教思想觀念的勇氣和智慧,而且需要世界各宗教的廣大信徒有相當的知識修養和文化視野,有與世俱進的意識和敢于創新、敢于實踐的勇氣。當今世界人口60多億中有近50億人口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們的經濟生活狀況、知識或教育水平彼此差異甚至相互懸殊,價值觀念和民族文化傳統極為不同,從這些基本狀況來看,要在短期內消除世界各宗教之間的沖突、實現各宗教之間的和平相處是一件不太現實的事情。這就使得各宗教之間的和平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宗教思想家(宗教學者)、宗教領袖等少數上層人物身上,不能擴展到廣大普通信眾之中。世界各宗教之間的沖突或對立如果不能普遍地得到化解,那么宗教對世界倫理建構所能發揮的作用將受到極大的阻礙。
四、簡要結語
從根本上說,世界倫理的發展進程受到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的制約,因為人們總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5](P434)。世界倫理的建構從根本上依賴于人類社會生產實踐的發展,依賴于階級的消滅和國家的消亡。“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5](P435)只有在未來消滅了階級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類才能消滅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矛盾沖突,才能消除人與人之間根本利益的沖突和對立,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能成為目的,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P294)。在這一無剝削無壓迫無根本利益沖突的人類社會才會徹底實現人人自由平等、互助、和諧的世界倫理。
宗教在現實社會歷史中確實表現出兩面性,它既阻礙人類文明的進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各宗教也可以產生解放性的、指向未來的以及對人有益的作用,并曾經常這樣做過:宗教可以傳播對生活的信念、慷慨、寬恕、團結、獨創性以及社會義務。宗教還可以促進精神煥發、社會改革以及世界和平。”[1](P59)宗教在世界倫理的建構中確實能夠發揮一定的或很大的建設性作用。“各宗教可以通過個人、宗教團體或者整個宗教組織持續地力主塵世上的和平、社會上的正義、非暴力以及博愛。”[1](P96)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一些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已經在這方面發揮了十分有益的建設性作用。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以宗教界領袖、神學家為主體的6500名學者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了“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會后發表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力圖在多元民主和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建構超越宗教的全球倫理或世界倫理,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各個國家、民族或地區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普遍聯系的不斷推進,我們行進在世界倫理建構的路途之中。世界倫理的建構具有多種方式或形式。以基督教為代表的世界性宗教在當代世界倫理的建設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世界倫理的建構決不僅僅局限于宗教;國際學術界也作出了巨大努力。以德國實踐哲學家阿佩爾、人類學家H.尤納斯為代表的宏觀倫理學(Macro-ethics),麥金泰爾的德性倫理學,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又譯“辯談倫理”、“對話倫理”)等等無疑也是建構世界倫理的重要理論嘗試。正如漢思·昆所說,若沒有宗教的貢獻,世界倫理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既要看到宗教對當今世界倫理建構所具有的積極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充分利用和發揮世界各宗教在推進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推動世界和平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又要清醒地看到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局限性,充分認識世界倫理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排除幻想和空想,腳踏實地地從人們當前的物質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出發,在人類社會生產實踐發展的基礎上逐步解決這一歷史性課題。
注 釋:
① The Universal Ethics或者global ethics均有多種譯法,可譯為“世界倫理”、“普遍倫理”、“全球倫理”、“普世倫理”等;“普世倫理”的譯名則帶有相當成分的基督教宗教意味和西方價值中心主義的色彩。
[1]漢斯·昆.世界倫理構想(周 藝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2]孔漢思,庫舍爾.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何光滬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On the Function and Limitation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al Ethics of Religion
NIE Wen-jun
(Research Center of Moral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re has been clos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universal ethics.At present,religion has both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and many limitations for constructing the universal ethics.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longness and arduousn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al ethics and settle progressively this historical task on the basis of human productive practice.
religion;the universal ethics
D091
A
1000-2529(2010)06-0035-04
2010-08-23
聶文軍(1964-),男,湖南澧縣人,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責任編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