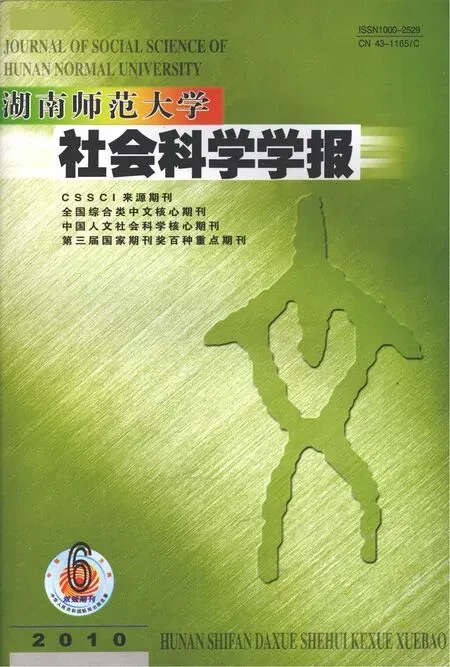我國政治轉型與文化軟實力之構建
陳宇翔,薛光遠
(1.湖南大學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2;2.長沙理工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4)
我國政治轉型與文化軟實力之構建
陳宇翔1,薛光遠2
(1.湖南大學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2;2.長沙理工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4)
正處于深刻社會變革和政治轉型時期的中國,建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顯得格外迫切和需要。如何在變革中促使國家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并在由“民族國家”過渡到“文明國家”的過程中,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水平,為“中國模式”的成功構建和發展提供內在支撐,既關乎當下中國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更攸關中華民族可否復興。
政治轉型;文化;文化軟實力
自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以來,“軟實力”及其各種衍生符號隨即成為學界分析國際關系和解讀國家發展走向的“利器”。而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將“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列為國家發展戰略后,關于文化軟實力的論述也迅速升溫。政治轉型與文化軟實力的互動也已成為國家發展理論的共識。從世界變遷的大視角觀察處于深刻變革中的中國,我們確信文化在中國社會整合及價值重塑方面的作用必將得到極大凸顯。
一、政治轉型與文化發展的互動
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政治制度與文化始終相伴成長,并以其特有的滲透力彌漫于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和環節,影響著人類文明的變遷。但凡一國、一地區、一民族文化之發展,其后必有一定的政治體系為之支撐;而政治體系之發展,則必有文化發展為之配合、驅動。依照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任何具體的政治制度,最終都上升到觀念層面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觀念體系,而這個觀念體系則構成了文化的具體內容。同時,特定的文化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的政治選擇和發展方向。人類社會始終處于發展之中,使得整個社會不僅在價值觀念上而且同時在社會利益和權力結構上發生著深刻變化,人們隨著新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階層結構及其關系形成新的固定化模式,從經濟到政治再到社會生活的每一方面,新的固定化模式的不斷形成標志著社會的整個制度體制也在實現著新舊交替。所以,諾斯堅持認為社會的變遷就是指制度的創立、變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1](P225)。在這樣不斷新舊交替的變化過程中,基于社會變遷所形成的普遍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則構成了社會文化的核心內容。縱觀人類歷史發展變遷,世界各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托本國的政治構造,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形態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成熟。古代中國漢唐時期的政治體系、近代西方國家確立的三權分立的代議制政治體系等,都在不同時期實現了各自的文化繁榮,成為文化軟實力得到極大發展的先例。
然則在當下,無論是中國的政治模式還是中國文化的發展都遭遇了“轉型危機”。有學者認為,整個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在某些方面,這些變革甚至是“革命性”的。高全喜即認為,從國內政治角度看,“中國發展為現代民族國家在20世紀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屬于民國時期國民黨主導的政治訴求。第二個階段屬于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政治訴求,盡管它們具有明顯的區別,但追求政治國家的合法性權威一直作為一條基本的原則或隱或顯地貫穿于其中。進入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合法性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從政黨政治逐漸轉變為國家政治,因此,過去所謂作為人民主權制的政黨原則開始為公民代議制的國家原則所取代,因此,國家利益問題就日益凸顯出來,成為中國新時期政治社會轉型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具有重要的政體意義”[2]。王逸舟分析道,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由傳統的“革命型政黨”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動員方式,向新的更加民主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依法治國方向的轉變,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中國的政治轉型。[3]
中國的政治轉型就是通過現代化建設,使中國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其中,最深刻也最難處理的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文化軟實力的提出不是脫離中國現代化這一歷史進程所發的抽象議論,而恰恰是中國現代化事業本身所提出來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和任務。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最終必然是文化的現代化,沒有文化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達成。著眼于文化和中國現代化之間的現實關系,是我們當今提出文化軟實力的基本出發點。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成為世界大國關系中重要的變量,如何積極積累和調動中國國家戰略的軟實力資源,以提高和拓展中國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國偉大復興的前提性條件。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還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崛起,而一個國家的崛起最終意義上必然是文化上的崛起。文化軟實力作為中國在追求“現代性”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其重塑與建構顯得格外迫切和需要。
二、走向“政治成熟”
韋伯曾經對德國從一個長期積弱的經濟落后國家迅速崛起為一個歐洲經濟大國感到憂慮。因為他認為,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后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愿望付諸流水,甚至還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自身的解體。終其一生,使韋伯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無法走向“政治成熟”。[4](P74)韋伯的這一擔憂事實上為德國日后的發展所證實。韋伯死后,德國的“魏瑪共和”在今日幾乎成為“政治不成熟”的同義詞,其結果就是希特勒的上臺以及戰敗后兩德分裂,并被迫分別依附于美、蘇兩大強權國家。學者甘陽指出,中國問題和韋伯的德國問題幾乎具有同樣的背景。他認為,在改革多年后,社會分殊化的程度已相當之高,從而使中國在社會層面已具有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乃至同一地區的不同“單位”之間的利益都已有極大的差異、矛盾和沖突。所有這些不斷增生中的新的社會差異、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事實上都突出了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高度分殊化發展后,中國將以什么樣的政治機制和政治過程來達成社會整合?從韋伯的“政治民族”問題意識出發,甘陽提出當前中國改革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從“政治不成熟”走向“政治成熟”[5]。
如何走向“政治成熟”或者說“政治成熟”的著力點何在便成為各民族國家發展思考中的重點。這一“政治成熟”最終必然要反應到文化上。社會的急劇變革使得文化在不同的維度中彰顯出前所未有的張力。具體到中國而言,所謂“政治成熟”,也是“文化自覺”的過程。費孝通曾指出:“在中國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認識我們中國人的真實面貌,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才能談得到讓人家認識我們和我們認識人家。科學地相互認識是人們建立和平共處的起點,人文學科就是以認識文化傳統及其演變為目的,也就是我常說的‘文化自覺’。在文化傳統上說,我們中國人有責任用現代科學方法去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繼往開來地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為人類的明天作出貢獻。”同時,他進一步解釋說:“文化自覺,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6](P98)亨廷頓曾經考察了一些在現代化進程中“無所適從的國家”。這些國家由于缺乏本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自覺,結果因沒有文化認同而在西化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尤其是服膺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所支撐的強大文化,主動放棄了本國的文化認同,最終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亨氏所指出的困境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一直沒有從民族心理認同和價值肯定上得到應有的“復興”,雖然近年來“文化熱”此起彼伏,卻大都參雜進更多政治或經濟成分,無法衍生為國民價值評判的標準和民族凝聚力的有效保證。加之改革開放以來,本國的文化影響過多的依賴高速的經濟發展,如果經濟步伐一旦放緩,文化影響力不是建立在國民心理上,那么依托何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也在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繁榮中顯得力不從心,制度瓶頸的存在也限制了國家的整體發展。只有在社會轉型之際,以“文化自覺”為核心推動國家軟實力的發展,使文化真正維系國家發展的價值構成,才能避免在現代化大潮中成為“無所適從的國家”,更不是“魏瑪共和國”的翻版,而是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同時在國家發展層面上實現從“民族國家”到“文明國家”的過渡。
三、從“民族國家”到“文明國家”
從歷史上看,所謂“民族國家”,是歐洲國家政治轉型與歐洲思想文化發展的結果。“作為一個歷史的人為建構過程和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與出現,與各個民族國家所建構的文化主體意識及其所提供的歷史合法性與合理性支撐是分不開的。”[7](P121)在人類歷史上首先出現于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在克服國內割據勢力、戰勝教會和應付國家競爭等語境下出現的。在此過程中,以民族語言為代表的民族國家文化逐漸掙脫了統一的歐洲文明,它的出現與建構,為民族國家奠定了文化政治的基礎,也在加強國家內部凝聚力的同時,驅使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傳統歐洲大國不斷進行對外競爭與擴張,逐漸在世界范圍內確立其無可比擬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優勢。
中國有著與歐洲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進程。假如說“民族國家”是近代歐洲的獨特產物,那么它在中國則完全是一個異質性的舶來品,與中國源遠流長的帝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可謂格格不入。以儒家文化為主線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傳統一直成為凝聚國家精神、維系“大一統”局面的內在支撐。而近代以來,來自西方主要民族國家的沖擊和挑戰,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國家危機。其中不僅包括中國傳統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出現了嚴重衰竭,而且也導致了傳統中國走向最終的崩潰。在這場“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中,文化危機成為最深重的危機形式。誠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之前的中國意識乃是一大一統的‘天下’意識,血統中國、地理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道德中國都成一體。”而非“民族國家”所代表的世俗性的國家形態。在列文森看來,近代中國所遭遇的文化危機從根本上看,是傳統中國“天下”的世界觀逐步讓位于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和視野的國家體系和國際法體系,普遍主義的帝國被置換、“降低”為特殊主義的國家。如其所論:“中國開始從‘天上’掉下來,變成現代‘人間’的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而且在現代的‘世俗’變化中,血統、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撐力量,也逐漸‘退回’其本來的角度,使中國變成沒有神圣色彩的‘國家’。”[8](P187)列文森的看法與 20 世紀初梁啟超的觀點暗合。梁氏認為,20世紀是西方“民族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于中國,舍新民未由。”[9](P6)梁啟超的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確實與西方現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建構“民族—國家”的路向相當一致,都是力圖以“啟蒙運動”的新思想新道德來造就“新國民”,從而將中國轉成一個“現代民族”。這種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與渴望一直是縈繞國人耳旁的聲音,它主導了近代以來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
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最終完成。然而國家形態背后的文化反思和論證卻并沒有因此而停滯下來。相反,隨著全球化加深,出現在國際視野中的“民族國家”已經逐漸失去其現代化大潮中的主體地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深刻地指出,這是一個民族國家正在過去而世界政治正在到來的時代,“民族國家是未完成的國家……誰在世界性的超級游戲中只打民族國家的牌,誰就輸。”[10](P4)歷史上所有的大國崛起都不只是經濟物質層面的崛起,更根本的是文化精神層面的崛起。國家崛起在最終意義上都是文化崛起。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制度層面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機,以至于在西方列強的挑戰之下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在這種情況下,與以往普遍主義的自我認知和自我確證相比,“中國”的文化主體位置被相對化、特殊化和最終客體化了。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同文化的主體性地位再一次成為論爭的焦點。改革開放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審視傳統在現代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傳統對于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每一代人的文化創造活動都不可能從空白起步,每一代人對過去傳統的回眸在某種意義上都蘊含著對當今現實的渴望。人的某種現實需求往往喚醒了傳統的某一部分和某個側面,這種傳統的價值在當下凸顯出來,進而成了現實文化生成的有機部分。可以這樣說,改革開放促使傳統文化發生現代轉換,促使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思維范式從反傳統逐步轉化為繼承傳統、光大傳統,從而重塑文化在國民心理上的價值意義,并形成對內的凝聚力和對外的輻射力,改變文化的身份認同。費孝通認為,無論是戊戌變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1949年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與“現代化”對立起來,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現代化的敵人。在他看來,文化的現代化不僅僅是“破舊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對傳統的繼承。此處所謂的“文化復興”則構成了現代中國“文明—國家”的內在支撐。換言之,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長遠之計,在于發揚宏大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特有的文化軟實力,否則中國就會成為在現代化中“無所適從的國家”,在現代轉型中迷失自己,從而導致文明的萎縮和滅亡。
四、不斷豐富“中國模式”的內涵
在現代化語境下,一個國家社會發展模式不僅反映著一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該國人民對于社會的認識與改造能力,而且這種模式的實踐效果如何往往也表明該國是否具有對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經驗的能力水平,在此基礎上,進而還能產生對該國的發展模式及其內在價值觀的“認同”效應,這本身就構成一國“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其中政治制度體系和文化感召力成為國家間“認同”的主要吸引力。在許紀霖看來,所謂大國,是指它不僅在經濟、科技、軍事和國際政治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成為當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話語,影響遍及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和各個角落。也就是說真正的大國,是能夠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輻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國家。[12]
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依靠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率贏得了世界的目光,與此同時,與經濟發展相互支撐的政治、文化體制也逐漸走向成熟。在政治轉型與文化發展之際,“中國模式”初見端倪。
“中國模式”的初具雛形與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是分不開的。二戰后,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把美國的發展模式視為實現現代化必須效仿、照搬的一般模式。而拉美等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這種效仿難以奏效。許多拉美國家至今尚在飽嘗實施“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苦果。正如W·茨阿波夫所言,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是一種“特殊性”,它們對全球不具有普遍意義,不是眾多國家可以模仿的路徑。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恩也指出:“現代化不再意味著美國化和西方化,雖然還可以從西方學到許多東西……各個國家將找到自己的道路。”[11](P38)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在西化大潮中尋求國家富強的道路,經過長期的戰爭和社會動蕩,終于摸索出了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順應世界全球化趨勢和世界文明發展方向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由于制度本身的安排是與核心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制度不僅得到國內廣大民眾的支持,而且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仿效和追隨,那么它將為這個國家帶來極大的文化吸引力,進而成為該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以世界工廠的姿態重新崛起。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發展途徑也越來越為世界矚目。但就總體而言,目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還多集中在經濟和貿易層面,政治方面的影響基本上是區域性的,在制度層面和思想觀念文化層面的“軟實力”對世界的影響還有待加強。“中國文化”還處于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多種論爭和博弈之中,尚未定型;在中國社會快速的現代化轉型中,“文化的現代化”尚未完成。作為一個正在再度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而如果沒有在文化政治上產生對世界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和貢獻,中國很難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可以說,這既是中國在未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是我們所提出的文化軟實力應著力解決的問題。就此而言,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必須具備大國的文化政治意識及相應的進取性和主動性,推動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歷史性崛起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呈現出強弱失衡的局面下,在多元思潮的激烈沖突下,“中國模式”的日漸成熟昭示著我國政治制度體系在現代化大潮中的生命力,而相伴演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則構成了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要素,并在凝聚全體國民的政治信仰、道德意識和價值共識的基礎上,成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斷發展和完善的背景下,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國力不斷強大、國際形象不斷改善的現代化強國,才能達到文化軟實力所能企及的高度。
[1]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 郁,羅華平譯)[M].上海:三聯書店,1994.
[2]高全喜.論國家利益——一種基于中國政治社會的理論考察[J].大國,2005,(2):1.
[3]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2002,(2):167.
[4]馬克思·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M].北京:三聯書店,1997.
[5]甘 陽.走向“政治民族”[J].讀書,2003,(4):6.
[6]費宗惠,張榮華.費孝通論文化自覺[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7]藝 衡.文化主權與國家文化軟實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8]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9]梁啟超.新民說(宋志明選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0]烏爾里希·貝克.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蔣仁祥,胡 頤譯)[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1]安德魯·韋伯斯特.發展社會學(陳一筠譯)[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12]許紀霖.大國之道與中國問題[J].大國,2005,(4):53.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CHEN Yu-xiang,XUE Guang-yuan
(1.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2.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16,China)
There is pressing need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soft power for china which is now undergoing deep social revolution transition.It is a crucial matter concerning not just whether current China can be successful in modernization but also whether Chinese nation can be revived as to how to enhance China stepping into“ripe politics”and how to offer internal support for th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Chinese Mode”.
political transition;culture;cultural soft power
D091
A
1000-2529(2010)06-0047-04
2010-01-05
陳宇翔(1965-),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學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博士;薛光遠(1983-),男,河南平頂山人,長沙理工大學教師。
(責任編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