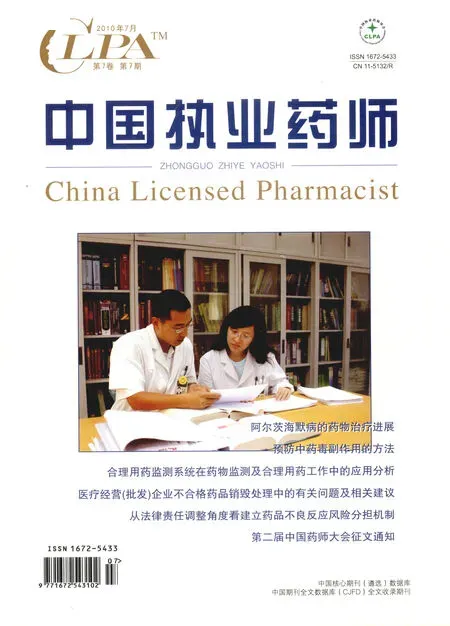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治療進展
任曉蕾韓冬李玉珍
(1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藥劑科,北京 100044;2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藥劑科,北京 100034)
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治療進展
任曉蕾1韓冬2李玉珍1
(1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藥劑科,北京 100044;2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藥劑科,北京 100034)
【摘要】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以進行性癡呆為特征的大腦退行性變性疾病,目前治療缺乏特異有效的手段。本文對其發病因素、發病機制及目前用于治療AD的相關藥物進行綜述,以期對臨床治療和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阿爾茨海默病;發病因素;發病機制;藥物療法
老年期癡呆根據病因不同,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①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即老年性癡呆;②血管性癡呆(Vascular dementia,VD);③混合型癡呆;④其他,如腦外傷,中毒,維生素B族缺乏,腦積水,帕金森病,慢性病毒腦炎等引起的癡呆。老年期癡呆根據癥狀可分為兩類:①因認知功能減退所致記憶、智能下降的癡呆;②為非認知性癥狀,即行為精神方面的癡呆。阿爾茨海默病是老年期癡呆中最常見的,占60%~65%,血管性癡呆和混合型癡呆各占15%~20%[2]。
AD又稱老年性癡呆,是一種多發于老年人,以進行性認知障礙和記憶能力損害為主的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也是大腦變性病中最常見的疾病,也稱Alzheimer型癡呆[3]。在發達國家,AD是繼心臟病、癌癥、中風后的第四位死因,據估計我國現有約500萬患者[4]。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起,提前進入人口老齡化的行列。60歲以上的老人已達1.26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0%,并以年均3.3%的速度上升,據估計至2025年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5]。隨著人類平均壽命延長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AD對人類健康的危害變得日益突出,是威脅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高發病,成為當前老年醫學面臨的最為嚴峻的醫學問題之一。此外,AD的治療和護理費用昂貴,英國每年用于AD醫護的費用為110億美元,而美國更高達839億美元[6]。
1 發病因素
年齡和性別是AD公認的危險因素,AD的患病率和發病率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女性顯著高于男性[7]。AD的危險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低、頭部外傷、性激素水平降低、家族史、血管性因素、高同型半胱氨酸(Hcy)升高、低體溫、社會活動減少、輕度認知損傷(MCI)、病毒感染等多種因素。此外,飲食營養因素(如血清維生素B6、B12、葉酸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社會心理因素(婚姻狀態、抑郁情緒)以及睡眠狀況等與AD的關系,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7]。
AD的發病是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及多種不良環境暴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針對于此,我們應當盡量避免和減少各種AD危險因素,篩檢出AD的高危人群,即將高齡、文化程度低、女性作為預防的重點[8]。
2 發病機制
AD的發病機制目前學說眾多,如膽堿能學說、自由基損傷學說、興奮性氨基酸毒性學說、鈣平衡失調學說等,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滲入,對AD的分子機制也有了進一步深入的認識。下面對目前比較公認的AD的發病機制進行概述。
2.1 分子機制
2.1.1 β-淀粉樣蛋白 (β-amyloid,Aβ)Aβ是老年斑(senile plaques,SP)的主要成分,它的沉積可能是所有因素導致AD的共同途徑。Aβ的神經毒性作用已經被公認是AD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其具體機制包括破壞細胞內Ca2+穩態,促進自由基的生成,降低 K+通道的功能,增加致炎細胞因子引起的炎癥反應,激活補體系統,增加腦內興奮性氨基酸(主要是谷氨酸)的含量等[9]。由Aβ誘發的慢性炎癥反應是介導神經元損傷的主要途徑,而老年斑周圍的神經膠質細胞及其分泌產物在這一機制中起主要作用[10]。

2.1.2 T形(tau)微管聯合蛋白與神經元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 tangles,NFT) AD的主要腦病理改變是NFT和SP,且前者與AD臨床癡呆癥狀呈相關關系。NFT的主要成分是以成對雙螺旋絲樣結構 (paired helical filament,PHF)形成聚集的異常磷酸化的tau蛋白。當tau蛋白發生高度磷酸化、異常糖基化、異常糖化以及泛素蛋白化時,tau蛋白失去對穩定微管的束縛,神經纖維退化,產生AD[9]。tau蛋白的病理變化出現在AD的早期,大多數病人腦脊液中的tau蛋白升高,因此,量化測定腦脊液中的tau蛋白可能成為AD早期診斷的一項有用指標[11]。
2.1.3 載脂蛋白E(ApoE)及其基因多態性[9]體外實驗表明,ApoE各種表型中,ApoE4基因型相對應的ApoE4將Aβ單體凝結成不溶性物質,從而促進SP形成,又可活化微管,形成NFT。臨床研究表明攜帶ApoE4等位基因的AD患者使用乙酰膽堿酯酶抑制劑如四氫氨基吖啶不如無ApoE4的AD患者有效。故可認為ApoE4在AD神經進行性病變中起重要作用。
2.1.4 c-fos過度表達[9]c-fos是早期快反應基因中研究最多的一種。近年的研究發現AD患者的大腦皮層及海馬中c-fos有過度表達。c-fos的過度表達可能通過誘導神經元凋亡或淀粉樣前體蛋白(APP)過量生成而參與AD的病理過程。
2.1.5 早老蛋白與AD[12-13]目前證實早老蛋白(presenilin,PS)1、2基因突變可導致家庭性早發型AD和散發性AD,PS不僅參與老年斑核心物質β-淀粉樣蛋白的形成,PS-1基因突變是導致早發性AD的主要原因,PS-2突變引發AD發生率較少。有研究表明,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和家族性阿爾茨海默病的致病原因存在差異,在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中早老素1基因第5號和第8號外顯子不存在突變或突變率極低,并非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致病的重要因素。
2.2 炎癥反應及神經毒損傷[9]
近年來的大量報道表明,在AD的發病過程中,炎癥反應是神經元丟失的重要原因。由于過量的Aβ聚集和纖維化,激活補體,活化神經膠質細胞(neuroglial,NG),異常活化的NG又分泌細胞因子、補體、氧自由基,啟動炎癥反應。
2.3 氧化應激和自由基損傷[14]
氧化應激是機體內產生自由基和氧化防御系統失衡所致,是與衰老相關的各種退化性疾病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礎。需氧細胞代謝過程中產生的超氧自由基會對腦組織造成損害,促進腦細胞的衰老和死亡。自由基還能損害細胞染色體,使第21號染色體畸變而發生AD。另有研究認為腦部的小膠質細胞可與Aβ聚集結合,并釋放出自由基吞噬并清除Aβ。正常情況下,只有少數Aβ聚集,容易被吞噬清除,但在病態下小膠質細胞很難清除眾多Aβ聚結而成的淀粉樣蛋白(AP),雖然膠質細胞仍會與之結合,且不斷釋放自由基企圖清除AP,但過量的自由基會對腦造成傷害,而且可能導致更多的Aβ聚結,造成惡性循環。
2.4 膽堿能損傷假說
在AD的發病機制中,此學說是目前較為公認的。老年腦和老年性癡呆患者皮質的膽堿能系統發生嚴重的潰變,引起老年性學習記憶減退和認知障礙,產生癡呆癥狀。這一假說已被尸檢所證明[15]。
患者腦內基底核和前腦的膽堿能神經最易受損,隨著疾病進展,90%膽堿能神經元都會被破壞,使腦內乙酰膽堿(Ach)水平降低,降低程度與患者認知能力降低呈顯著相關,提高腦內Ach水平,患者的記憶力、認知力就能得到改善[14]。
2.5 興奮性氨基酸毒性學說[15]
近年來,興奮性氨基酸尤其是谷氨酸(Glu)的興奮性神經毒性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Glu及谷氨酸受體 (GluR)在中樞神經系統(CNS)功能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參與了神經元的興奮性突觸傳遞,調節腦多種形式的學習和記憶等。Glu參與AD發病的機制可能為:Glu的快速興奮作用,引起去極化,Cl-、Na+及水內流,導致細胞滲透性溶解;因去極化激活膜電位依賴式GluR,使大量Ca2+內流,細胞內Ca2+超載,激活磷酸肌醇環路,破壞細胞的超微結構,使神經元潰變死亡。
2.6 鈣平衡失調學說[15]
近年來鈣代謝自體平衡失調與腦老化和老年癡呆的關系已引起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細胞內Ca2+濃度過高或Ca2+超負荷會使鈣依賴性生理生化反應超常運轉,耗竭ATP,產生自由基,甚至引起細胞死亡。對老化或AD患者的研究發現,在含有神經元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的腦細胞和來源于AD患者的成纖維細胞內均可見到Ca2+的堆積。
2.7 基因突變學說[15]
目前至少已發現四種基因的突變或多型性與AD有關。這些AD相關基因包括:第21號染色體上的淀粉樣前體蛋白(βAPP)基因,第14號染色體上的早老素(PS-1)基因,第1號染色體上的早老素(PS-2)基因和第19號染色體上的載脂蛋白E(ApoE)基因。其中βAPP基因、PS-1和PS-2基因與早發型家族性AD有關,每一早發型家族性AD病例至少有其中之一的異常;ApoE基因與遲發型家族性AD關系較為密切,與散發性AD亦有一定關系。
2.8 其他機制:雌激素減少、金屬離子假說等
3 治療
由于目前AD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針對目前的各種假說也提出了各種治療方案,現分別介紹如下。其中膽堿酯酶抑制劑和美金剛已得到FDA的批準,臨床效果也較其他為好。
3.1 膽堿能強化途徑
3.1.1 Ach前體[16]Ach前體藥物中較有意義的是鹽酸乙酰L-肉堿(Levacecarnine hydrochloride,ALCAR),它具有神經保護作用和線粒體保護作用(線粒體代謝異常可導致神經損傷),能主動透過血腦屏障,轉化為Ach,還有膜穩定作用,能提高神經生長因子水平。該藥1986年已在意大利上市,在美國和歐洲進行的早老性癡呆II期試驗表明該藥品有效,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其對早期AD病人的療效不甚理想。
3.1.2 膽堿酯酶抑制劑 (ChEIs)[16-18]神經化學研究顯示,在大腦皮質和海馬中的突觸含有Ach、谷氨酸、5-羥色胺(5-HT)等遞質,在老年癡呆的早期,膽堿功能缺乏的癥狀早于其他任何癥狀,AD特征之一的神經元凋亡也主要發生在膽堿神經元。突觸功能異常或喪失是發生癡呆的決定性因素。膽堿能替代療法主要是提高腦中Ach水平,恢復膽堿能神經傳導,從而改善病人記憶、認知和行為能力,但不能使病人完全恢復,不能阻止該病的形成。ChEIs可阻滯突觸中Ach的水解,提高對膽堿能(毒蕈堿和煙堿)受體的作用。目前,膽堿酯酶抑制劑是用于阿爾茨海默病治療的一線藥物,為輕、中度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標準治療藥物。現在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使用的藥物,包括他克林、多奈哌齊、卡巴拉汀和加蘭他敏。在我國還有石杉堿甲。
3.1.2.1 他克林(9-氨基四氫味丫啶) 是1993年第一個獲美國FDA批準治療AD的藥物,是一種可逆性ChEI,可以延緩膽堿能神經元分泌的Ach降解而提高腦皮質內Ach的水平,臨床試驗表明大劑量應用他克林可以明顯改善輕中度AD患者的認知功能,但肝功能異常、消化道副反應常見。尤其是引起轉氨酶(ALT)水平升高,由于較多的患者不能耐受他克林治療,因此有逐漸被其他膽堿酯酶抑制劑所取代的趨勢。
3.1.2.2 多奈哌齊(安理申) FDA于1996年批準在美國首次上市,是目前全世界應用最廣泛的ChEIs。開始劑量5 mg/d,4~6周后可加量至10 mg/d。該藥的半衰期為70 h,每天只需給藥1次,對老年或腎臟、肝臟有損害的病人也無須減少劑量,未顯示肝毒性,主要為膽堿能作用,如惡心、腹瀉、肌肉痙攣和乏力等。另有實驗證明,多奈哌齊對中重度AD有效[19]。
3.1.2.3 利凡斯的明,即卡巴拉汀 是從由豆科植物毒扁豆種子中提取的一種生物堿。能選擇性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膽堿酯酶。起始劑量每次1.5 mg,每天2次,服藥至少兩周后,劑量可逐漸增加至3 mg,每天2次,最大劑量6 mg,每天2次。外周的毒副作用,限制了它的臨床應用,本品對于日常生活認知行為和綜合能力有顯著療效。
3.1.2.4 加蘭他敏 從雪花蓮屬植物以及我國石蒜植物內分離得到的生物堿,是AchE的競爭性抑制藥,對神經元中的AchE有高度選擇性,推薦劑量30~60 mg/d,1個療程至少8~10周,對AD病人的認知力、功能性及行為癥狀有明顯改善。
3.1.2.5 石杉堿甲片(雙益平、哈伯因) 為可逆性膽堿酯酶抑制劑,對真性膽堿酯酶有選擇性抑制作用,易通過血腦屏障,臨床上對AD的應用比較廣泛。口服,每天2次,每次100~200 μg,一日劑量不能超過450 μg。
3.1.3 M1受體激動藥[14]突觸后M受體中主要是M1受體,不受膽堿能神經纖維退變的影響。M1受體激動藥不僅使膽堿能系統活力基礎水平提高,而且可促進APP的Aβ的非Aβ代謝,減少Aβ的產生,并可降低tau蛋白磷酸化程度,從而改善腦內膽堿能神經的退變,減輕AD癥狀,延緩病情發展。目前正在廣泛研究的有占諾美林、他沙利定和AF系列化合物等。
3.1.4 Ach釋放調節劑[16]促進Ach釋放的藥物主要分為M2受體拮抗劑、煙堿受體激動劑、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組胺H3受體阻斷劑等幾類。
3.2 鈣離子拮抗劑[10,17]
AD患者細胞內的Ca2+超載造成神經細胞損傷和凋亡,鈣離子拮抗劑可以抑制Ca2+的超載,減輕血管的張力,預防血管痙攣。尼莫地平,雙氫吡啶類第二代鈣拮抗劑,是目前臨床上用得最多的治療AD的Ca2+拮抗劑。尼莫地平對中樞神經系統具有直接作用,易通過血腦屏障,主要分布在皮層和海馬等參與學習和記憶有關的區域,并能與該區域的特異性受體結合,有抗抑郁、改善意識及記憶功能的作用,并可促進受傷神經的再生和感覺運動功能的恢復,對情感和社會行為等方面也有明顯改善。在病理學方面,尼莫地平使腦老化過程中常見的纖維變性基膜變厚,淀粉樣蛋白和脂質沉淀的發生率明顯降低。
3.3 抗氧化性藥物[10,17]
3.3.1 維生素E易被氧化,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故在體內可保護其他易被氧化的物質 (如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A),減少過氧化脂質的生成。
3.3.2 褪黑激素(MT)是由哺乳動物和人腦松果體腺分泌的一種具有多種生物活性的吲哚類物質,作為一個內源性自由基清除藥具有以下一些特點:①可清除·OH、H2O2、單線氧、NO、過氧化亞硝酸陰離子(ONOO-)等,還可通過基因調節,提高SOD和谷胱甘肽還原酶的活性。②能夠有效地抵御大多數自由基生成藥(氰化鉀、乙醇等),自由基生成過程(缺血-再灌注、過度運動)和大劑量化學致癌物黃樟醚以及電離輻射造成的DNA破壞及基因損傷等。AD病人血、腦脊液中MT水平明顯低于正常老年人,且MT極易通過血腦屏障。
3.4 抗炎藥物[17]
鑒于AD病人腦內老年斑周圍有小膠質增生,為炎性免疫反應的改變,可能造成Aβ,該沉積及小膠質活動的產物可能具有神經毒性,引起神經細胞蛻變,出現癡呆的臨床癥狀。因此主張應用非甾體類抗炎藥物(NSAID),如阿司匹林、吲哚美辛等。研究顯示,隨著非甾體抗炎藥使用年限的增加,患AD的危險性降低,減緩進程,減輕認知癥狀的嚴重性。
3.5 他汀類[17]
最新的流行病學和藥理學研究表明,他汀類藥物對于AD具有潛在的治療作用。AD和脂質的相關性研究提示高脂血癥是AD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膽固醇在AD的發生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AD最主要的纖維特征就是細胞外存在大量呈纖狀、相對分子質量為4 000的Aβ組成的老年斑,研究發現AD的神經化學和神經病理學改變與Aβ有密切關系,而Aβ的形成或消除可能受膽固醇調節。他汀類藥物通過降低膽固醇水平,APP蛋白酶活性減弱,APP的轉運及消除發生改變,Aβ40、Aβ42的合成和積累受到抑制,可能起到推遲AD的發生或延緩AD的進程。
3.6 腦代謝改善途徑[16]
腦供血、腦攝取營養不足及腦老化現象是AD患者普遍存在的臨床癥狀,因此改善腦代謝、增加腦部營養可以緩解癥狀。
3.6.1 吡咯烷類衍生物這類藥物化學結構上均具有吡咯烷酮的結構,屬GABA(γ-氨基丁酸)衍生物,但其實其藥理上并不顯示GABA樣作用,而屬于腦能量代謝改善藥物,具有激活、保護和修復神經細胞的作用,常常被稱為促智藥或認知促進劑。吡拉西坦系20世紀80年代開發的藥物,隨后相繼研制了奧拉西坦,普拉西坦,阿尼西坦,左乙拉西坦,奈布西坦等系列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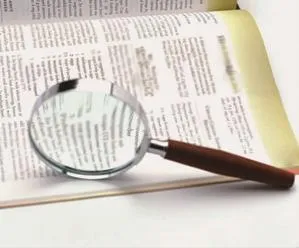
3.6.2 腦血管擴張劑類這類藥物主要是通過擴張腦毛細血管,增加腦供血,促進微循環來改善腦對能量和氧的利用,改善腦代謝,促進腦細胞恢復。麥角生物堿類藥物中最早應用的是氫麥角,20余年前已由美國FDA認可用于癡呆治療,以后又有尼麥角林,舒腦寧等類似制劑。還有都可喜、艾地苯醌、長春西汀以及臨床上早已廣泛使用的心腦血管擴張劑煙酸等。
3.7 雌激素[18]
女性AD患者明顯多于男性。女性絕經后雌激素缺乏可能與AD發病有關。流行病學研究表明,雌激素可延緩或降低AD的發病,是AD的保護因素。但雌激素對AD的療效目前還沒有一致性的結論。
3.8 抗菌藥物治療[20]
相繼發現一些抗菌藥物例如四環素、利福平和兩性霉素B等具有抗Aβ作用,具體機制尚不明確,體外實驗表明此類藥物可以干擾Aβ聚集。
3.9 天然藥物[21-22]
銀杏葉提取物(EGb),有效成分為黃酮,可提高腦缺氧的耐受性,增加大腦能量的代謝,清除自由基,減少腦水腫,有保護腦組織的作用,可使記憶力和認知力明顯改善。EGb在德國已被批準用于癡呆的治療。
3.10 神經營養因子[1]
3.1 0.1 腦活素為腦蛋白水解酶,可直接通過血腦屏障進入腦神經細胞,促使神經細胞蛋白質合成,使已損傷但未變性的神經細胞恢復功能;同時可加速葡萄糖通過血腦屏障的轉運速度,改善腦能量供應,增加腺苷酸環化酶的活性,有利于腦細胞記憶功能的恢復。可改善血管性癡呆及老年性癡呆的記憶功能、情緒、疲勞等癥狀,耐受性較好,偶見過敏反應及輕度發熱反應。
3.1 0.2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是從小牛血清中提取而得的,是一種大腦所特有的肽能神經營養藥物,能以多種方式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調節和改善神經元的代謝,促進突觸的形成,誘導神經元的分化,并進一步保護神經細胞免受各種缺血和神經毒性的損害,其神經營養活性可以延緩AD進程。
3.11 美金剛[23]谷氨酸鹽是中樞神經系統內最豐富的興奮性神經遞質,可激活對鈣離子高度通透的電壓依賴型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導致細胞內鈣超載而損傷神經元。美金剛是一種低親和力、非競爭性的NMDA受體低中度親和力的非競爭性拮抗劑,能顯著改善重度AD患者的臨床癥狀,美國FDA在2003年11月批準其應用于中度至重度AD,與膽堿酯酶抑制劑相比,美金剛不僅對輕度癡呆有效,并且對重度癡呆同樣有效,且美金剛可以和ChEIs合用以增強療效。美金剛具有保護神經細胞免遭過量興奮性氨基酸造成的毒性作用。
3.12 針對Aβ的治療[23]
老年斑是AD的特征性病理變化,其核心成分是由Aβ在腦內沉積所致。減少Aβ的產生或者促進其降解是AD治療的關鍵,這些已在動物實驗得到證明。這方面的治療措施大多處于動物實驗階段,部分已進入II期和III期臨床。包括:①β分泌酶和γ分泌酶抑制劑;②Aβ聚集抑制劑和降解促進劑;③免疫治療。
3.13 神經生長因子途徑[16]
神經生長因子(NGF)是對神經元的存活、生長發育、分化、再生和功能維持起調控作用的分子。NGF對中樞膽堿能神經元有促進作用,外源性NGF可引起膽堿能神經元增生和延長存活時間。體內體外及初步的臨床試驗證實NGF有可能用于AD治療。
3.14 基因治療[24]
分子遺傳學研究證實,一些相關基因如AP前體蛋白基因、PS-1基因、PS-2基因突變及ApoE4型基因與AD的發病有關。因此認為可利用克隆、基因重組技術將正常基因替代缺陷基因,達到根治基因缺陷的目的。但因技術復雜,目前尚在研究階段。
3.15 行為癥狀的治療及康復治療
90%的癡呆病人表現一種或幾種精神及其他伴隨癥狀,如抑郁狀態、睡眠障礙、焦慮及譫妄等,應予對癥治療[10]。
綜上,根據AD的病因、發病機制和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目前存在多種治療策略,但其中許多藥物的療效都有待于大量臨床試驗證實。雖然近幾年在AD治療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尋找出有效的治療方案對于提高老年人生命質量及減輕國家及家庭的負擔都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王璐華,童如鏡,沈菊芳.老年癡呆癥的藥物治療及進展[J].中國藥師,2003,6(4):233-235.
[2]Francoise AN,Li Y.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Alzheimer’s disease[J].J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2005,19(6):279-283.
[3]管姝軼,曲麗麗.阿爾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學研究與臨床[J].中國社區醫師,2004,20(20):10-11.
[4]洪震.我國近年阿爾茨海默病流行病學研究現狀與展望[J].老年醫學與保健,2005,11(4):195-197.
[5]楊期東,周琳.中國阿爾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學特征[J].中國臨床康復,2004,8(31):6982-6983.
[6]Wimo A,Winblad B.Economic aspects on drug therapy of dementia[J].Curr Pharm Des,2004,10(3):295-301.
[7]譚紀萍,張曉紅,王魯寧.阿爾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學研究概況[J].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5,39(2):146-147.
[8]洪玉.阿爾茨海默病流行病學研究現狀[J].新疆醫科大學學報,2003,26(5):510-511.
[9]王鐵楓.賀娟.阿爾茨海默病發病機制研究進展[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3,12(4):476-477.
[10]馮麗莎,王紀佐.Alzheimer病的研究與治療進展[J].天津醫藥,2003,31(2):124-125.
[11]Andreasen N,Mint hon L,Clarberg A,et al.Sensitivity,specificity,and stability of CSF-tau in AD in a community based patient sample[J].Neurology,1999,53(7):1488-1494.
[12]徐如祥.阿爾茨海默病的分子機制與神經干細胞移植治療[J].老年醫學與保健,2004,10(3):177-178.
[13]Wu Q,Fang YY,Han J.Analysis of the 5th and 8th exon mutation in presenilin-1 gene in sporadic Alzheimer disease[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2005,9(37):136-137.
[14]吳方建.阿爾茨海默病發病機制及藥物治療[J].醫藥導報,2004,23(2):68-69.
[15]常艷,薛毅瓏.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病機制及其研究進展[J].中國臨床康復,2004,8(4):693-694.
[16]朱杰,張學景,鄒永.阿爾茨海默氏病及其藥物治療研究進展[J].廣州化學,2004,29(2):36-37.
[17]張娟,張建英,董圣山,等.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藥物應用現狀[J].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05,3(4):343-344.
[18]趙萬中.阿爾茨海默氏病的臨床藥物治療 [J].天津藥學,2005,17(2):53-54.
[19]Wilkinson DG,Passmore AP,Bullock R,et al.A multinational,randomized,12-week,comparative stydy of donepezil and rivastigmine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J].Int J Chin Pract,2002,56(6):441-446.
[20]Hartsel SC,Weiland TR.Amphotericin B binds to amyloid fibrils and delays their formation:a therapeutic mechanism? [J].Biochemistry,2003,42(20):6228-6233.
[21]陳曉紅,王蔭華.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新進展[J].中國全科醫學,2001,4(2):940-941.
[22]劉小紅,婁紅祥.治療老年性癡呆病的天然藥物成分[J].齊魯藥事,2004,123(1):42-43.
[23]陳生弟,楊紅旗.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策略[J].老年醫學與保健,2005,11(4):193-194.
[24]Cosgays JM.Nerve Growth Factor and Ras Regulateβ-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Gene Expression in PC 12 Cell[J].J N-eurochem,1996,67(1):98-104.
作者簡介:任曉蕾,女,碩士,主管藥師。研究方向:臨床藥學。E-mail:renxiaolei8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