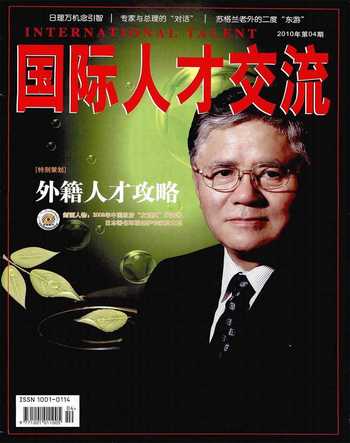后危機時代美國監管制度調整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周艷杰 張繼飛
據初步統計,2009年共有140家銀行破產,2010年新年伊始,已有15家銀行相繼被監管部門接管。美國政府開始對監管政策的漏洞進行反思,并對金融監管政策加以改變和調整。調整后的監管政策對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何種影響,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何種挑戰,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震蕩,并且每一波震蕩都有一個比較鮮明的主題,如2009年一季度世界各國頻現機構震蕩,許多金融機構紛紛更換高管、下調評級;接著全球股市出現震蕩,3月中旬到了最低點;而各國政府在出手相救時,卻造成了財政危機,形成新一輪震蕩。當前,又出現了主權債務風險,震蕩加劇,典型的是迪拜債務危機和希臘債務危機。作為震中的美國,其金融和銀行體系遭受重創,幾乎接近崩潰的邊緣。據初步統計,2009年共有140家銀行破產,2010年新年伊始,已有15家銀行相繼被監管部門接管。美國政府開始對監管政策的漏洞進行反思,并對金融監管政策加以改變和調整。調整后的監管政策對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何種影響,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何種挑戰,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反思美國監管政策
面對危機時的無所作為,不但使世人對美國監管機構口誅筆伐,也使美國金融機構的風險全面暴露出來。美國監管部門不得不對各類金融機構,尤其是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大型銀行的監管進行反思。
反思一:對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大型銀行,沒有設立相應的監管制度和機構。
美國銀行業自從20世紀80年代“大陸伊利諾伊”倒閉之時,提出了所謂“too big to fail”的與系統性風險相聯系的理念。該理念的內涵是由于某家銀行對全社會影響力太大,如果讓它倒閉勢必對整個經濟或金融市場產生嚴重的影響。為此,政府應當竭盡全力將這一過程淡化,或通過救助的形式緩解其負面性影響。然而美國銀行業的根基是私人股東,如果所有私人所有制的銀行由于自身的經營不善卻因為影響太大而不能直接讓它破產,由納稅人的錢去救助,勢必造成道德風險。對于這一問題,多年以來,無論是美國立法當局還是巴塞爾委員會,對有關系統性風險的管理從未有過相關的立法。在日常的監管過程中,美國監管當局主要通過防微杜漸的方式來努力防范各大型銀行的內部風險。換言之,監管機構在對大型銀行進行的現場和非現場檢查發現的風險處罰非常嚴厲,監管非常謹慎,但始終缺乏一套對該銀行與系統性風險相關的專門監控制度和體系。在巴塞爾協議乃至美國所有銀行監管機構的檢查手冊中,最多有9大類別的風險,但沒有一個機構提到系統性風險。與此相應,在諸多的銀行監管機構之中,也沒有一個明確監管系統風險的機構。正是由于管理系統性風險機制和機構的缺位,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肆虐之時,美國金融監管機構束手無策,令其銀行體系在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沖擊下瀕于崩潰的邊緣。
反思二:對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大型銀行,沒有要求其進一步完善風險管理。
這次金融危機揭示出一個平時不太引人注意的問題,即:許多美國大型銀行以及其他國家的大型銀行實際上缺乏足夠的資本金和流動性來保護自己以及整個金融體系。巴塞爾委員會倡導的資本補充機制目前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采納的規則,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國監管當局在要求其大型銀行執行新巴塞爾協議方面,表現很消極。
后危機時代美國金融監管改革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2009年6月,美國政府發布了金融監管改革白皮書,即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拉開了美國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體系改革序幕。改革方案主要體現兩個理念:一是集中監管。美國政府計劃建立強大的“單一機構”,把大型金融機構、重要的支付和清算系統等都納入其監管之下,以改變過去美國金融體系多頭監管存在真空、死角的狀況。同時,成立一個允許監管機構接管即將破產的銀行控股公司的決議機構。二是深化監管。美國政府計劃擴大監管范圍并提高監管深度,大型對沖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等機構以及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將被納入監管。其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首先,加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監管,革新傳統金融監管理念。改革方案指出,所有可能給金融系統帶來嚴重風險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受到嚴格監管。一是強化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成立“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專門管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二是強化對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等基金公司的監管,再次將這三類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范疇;三是強化對銀行類機構的監管,將屬于存款類機構、但不受《銀行控股公司法案》限制的儲蓄貸款控股公司、信用卡銀行、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范疇;四是強化對場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的監管,通過修訂《商品期貨交易現代化法案》和證券交易法規等,將其納入監管范疇,確保監管機構充分掌握場外交易信息,監控衍生品市場風險;五是強化對證券化市場的監管,通過建立證券發行方與購買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降低證券化市場風險;六是強化對保險公司的監管,通過在財政部下設聯邦層面的保險監管機構,加強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管控、信息收集與共享、監管漏洞防范、國際國內監管協調等方面的工作;七是強化對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的監管,提高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要求,并加強研究在危機情況下,能夠真實反映銀行風險水平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八是強化對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監管,降低這類基金的流動性風險和脆弱性風險;九是強化對金融系統重要性支付、清算和結算系統的監管,由美聯儲具體負責,解決回購和衍生品交易結算問題,提前預警風險積聚趨勢,降低金融市場不穩定性;十是強化對金融機構高管薪酬的監管,使金融機構高管薪酬與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相一致、相協調。
其次,賦予政府系統性風險管理職權,規避系統性金融風險。針對本輪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缺失和遺漏,白皮書提出兩方面改進措施:一方面,增設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機構“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主席由財政部長擔任,其他成員由7個聯邦監管機構主席組成,主要負責收集各類監管信息、識別并監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協調各監管機構關系;另—方面,賦予政府必要的政策工具以有效應對金融危機。
第三,調整金融監管機構權限,減少重復監管。為了解決美國銀行業“多頭監管”帶來的監管成本居高不下、監管效能持續走低等問題,—方面對銀行監管權限進行了臺并和重組,將“貨幣監理署”(OCC)與“儲蓄監管辦公室”(OTS)合并成立了“國家銀行監管機構”,對所有聯邦注冊的存款機構進行審批和監管;另一方面,進一步明晰各類金融監管機構交叉監管領域的權限,新設立的“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主要負責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識別、監測和管控,美聯儲將繼續履行對銀行控股公司等大型金融機構的日常監管
職責。此外,還要求各金融監管機構致力于同類金融機構、同類金融業務監管標準一致化建設,有效防止監管套利。
第四,強化對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的保護,促進金融交易公平。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新設獨立于所有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歸并原來分散在除證券和期貨監管機構之外的眾多聯邦監管機構中的消費者保護監管權,在避免監管權限分散帶來的監管力度不夠的同時,有效彌補了“多頭監管”帶來的監管漏洞,保護消費者免受金融消費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詐等行為的侵害,減少或避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確保公平交易。該局的具體職責主要包括:改進各類金融產品信息披露監管要求,金融機構要與消費者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與溝通,要以適當的方式讓消費者深入了解其消費權利與義務,風險與收益;提高金融產品條款設計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向消費者提供透明、公平、合理、不帶有金融欺詐、沒有誤導性的金融產品;要求各類金融產品經紀商和投資顧問嚴格履行受托人職責,避免誤導銷售和欺詐銷售,向消費者和投資者提供最符合其風險收益需求的金融投資決策建議;協調各州監管機構之間的關系,提高監管標準,促使類似金融產品監管標準一致化。
第五,擴大國際監管合作,防止金融風險快速擴散和蔓延。為了避免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要建立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通過國際對話與協調,加強對場外衍生品市場的國際監管和監管標準的一致化;通過巴塞爾協議的完善和推廣,加強國際銀行業的資本監管和監管標準一致化;通過監管信息和手段共享,加強跨國金融機構監管,提升金融危機應對能力;通過完善國際會計準則,減少因會計準則等帶來的技術性風險與沖擊。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出臺,標志著美國加強對金融系統風險管理的力度與決心,意味著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監管體系將日趨完善、成熟和穩定,這為我國銀行進一步大力拓展在美國境內的業務,特別是金融市場方面的各項業務提供了更加規范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使我國在美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可以享受良好的金融環境,能夠更好地經營與發展。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這種調整對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發展帶來—定影響。
一是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門檻更高。改革方案強化了對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的監管,提高了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要求,這使得今后對外國銀行持股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在資本金方面的要求和門檻會更高,對中國銀行業機構在美國境內分支機構經營的流動性監管提出更嚴苛的要求。
二是業務操作更加嚴格。改革方案指出由美聯儲具體負責,強化對金融系統重要性支付、清算和結算系統的金融監管,將使我國銀行在美元支付和清算等方面的業務操作承受的來自美聯儲綜合監管方面的負擔可能會加重,受到操作風險管理的監管要求可能更加嚴格。
三是金融服務更具挑戰。改革方案強化對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的保護,擬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于我國銀行在美國可以敘做零售業務的經營機構,由于其零售業務面對中小消費者,很可能將受到更為趨嚴的監管,在產品的合規管理E可能面臨更嚴峻的監管壓力。
四是國際監管標準更加趨同。改革方案從美國利益出發,強調國際協調和一致性,防止出現資本轉移和套利。如果美國將本國監管標準用之于世界,要求全球采用同樣的監管模式,中資銀行將面臨更多的監管羈絆與束縛,業務創新與風險管理將面臨更多挑戰。
挑戰與機遇總是并存的。面對美國的監管新政,我國銀行業機構一定要加強并提高管理能力,在政策流程、風險管理、業務操作、系統管理等方面不斷加以完善。目前,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銀行)以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為契機,加強全面風險管理,促進了風險管理組織架構的優化整合,推動了風險管理向科學化、精細化方向發展,促進了數據質量和IT基礎的提升。當然最重要的是,促進了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和人才的建設。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大型銀行在此次危機中寫下的讓世人驚嘆的亮麗一筆,可以應對來自美國乃至世界各國監管政策的改變與調整。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出臺,意味著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監管體系將日趨完善、成熟和穩定,這為我國銀行進一步大力拓展在美國境內的業務提供了更加規范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使我國在美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可以享受良好的金融環境,能夠更好地經營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