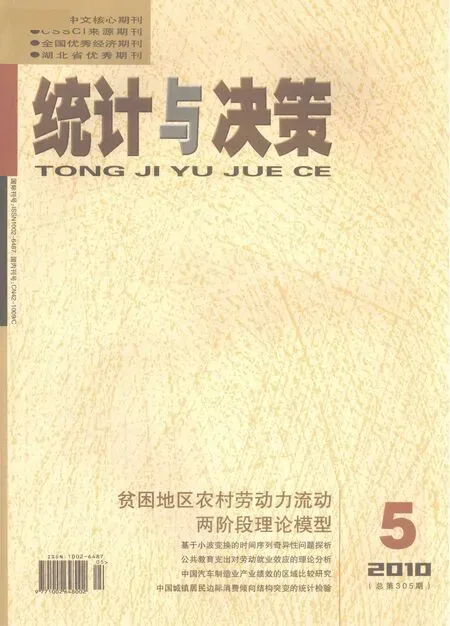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金融政策調控思路
高士成
(中國人民銀行,北京 100800)
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我國經濟正在日益與世界經濟進行融合。因此,我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必須適應這一開放性經濟特征。由此,我們的貨幣政策目標確定、政策工具的選擇運用必須受制于我國目前的國內外經濟均衡和開放經濟條件,具體從內外部經濟均衡角度來看,國際收支和匯率的均衡都需要考慮我國經濟實現內外同時均衡,以確定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
1 內外經濟均衡角度的外部平衡目標確定
盡管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逐漸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并認為浮動匯率能夠自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因而也放棄了國際收支平衡作為經濟調控目標,但是,牙買加體系運行的結果并沒有實現如上所述的效果,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都由于各種不同原因或多或少地對國際收支和匯率進行干預。我國目前正在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其中,幣值穩定就包括了人民幣對外價值的相對穩定,即:實際匯率水平的相對穩定。與此同時,國際收支作為影響外匯供求的一個關鍵變量,對匯率的決定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內外經濟均衡及其調控過程中,將匯率和國際收支作為兩個重要的經濟變量進行研究,探討國際收支平衡和均衡匯率①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均衡匯率”定義為使一國經濟能夠處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的匯率。(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的確定及其形成機制。需要說明的是,現實中匯率決定的影響因素多種多樣,理論界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匯率決定理論,但由于我們是從分析經濟均衡角度來考察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決定,因而我們更多地是關注基本經濟因素(而不是交易技術因素等)決定的“均衡匯率”。
我們所稱的“一般均衡匯率理論”要包括很多理論流派,它們的研究范疇自然有所區別,但目前較成熟的“一般均衡匯率理論”大都沿用國際收支均衡的分析框架,具有兩個明顯的共同特征:
一是在分析國際收支均衡時納入國內經濟均衡的因素,例如,John Williamson(1994)提出的基本要素均衡匯率模型(FEER)和 Stein(1994,1995)提出的自然均衡匯率模型(NATREX)都是沿用這一思路。FEER模型是首先把經常項目表示為國內總需求、國外總需求和實際有效匯率在充分就業條件下的線性函數,然后,令經常項目余額等于可持續的資本項目余額,可求得實際匯率。NATREX模型將儲蓄偏好、勞動生產率、資本密集度等因素納入影響資本流入進而影響均衡匯率的因素。
二是分析區間為中期。無論是FEER模型還是NATREX模型,都將均衡匯率視作一種中長期可持續的匯率。
2 國際收支平衡和均衡匯率決定
為說明上述“一般均衡匯率理論”兩點特征對均衡匯率決定的含義,我們借鑒Obstfeld、Rogoff等人的思想,利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進行分析。
2.1 國際收支平衡
考慮到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我們將在研究國際收支平衡時重點考察經常項目收支。
2.1.1 存在國際借貸時的內部經濟均衡
首先,假定考慮區間為兩期,個人消費者I在兩期的消費量分別為c1和c2,最大化效用函數U,取決于當期消費水平,即:
U=U(c1)+βU(c2) (1)
其中,β為測度個人消費耐心程度的固定偏好參數,一般大于0小于1。
假設每期的效用函數U(c)是消費的嚴格增函數,并且是嚴格凹函數:U(c’)>0,U(c’’)<0。
考慮存在兩期,假定國內消費者可以自由在國際市場上進行借貸,第一期期初和第二期期末的私人外匯資產為零,則預算約束條件為:

其中,C1、C2分別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費;I1、I2分別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投資;y1、y2分別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產出;G1、G2分別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政府消費支出;r是國際借貸市場的實際利率。
假定國內產出是資本投入的函數,即:

其中,Yt為 t期的產出;At為 t期的生產率;Kt為 t期的資本存量。
投資是資本存量的變化,即:

因此,利用等式(3)和(4),求解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問題就是以等式(2)為約束條件求解(1)式最大化,其中,
消費的一階條件為: U'(c1)=(1+r)βU'(c2) (5)
等式(5)表明,當效用最大化時,消費者不能通過各期間轉移消費而獲益。
投資的一階條件為:A2F'(K2)=r (6)
在資本自由流動、所有產品都可以自由貿易的自由開放的小國經濟假設條件下,從等式(6)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投資要擴大到資本的邊際效益等于國際資本市場借貸利率為止;二是本國的最優投資規模與其實際消費水平無關。
2.1.2 存在國際借貸時的經常項目余額
由于存在國際借貸,一定時期內,一國經常項目余額反映的是對其他國家凈債權的變化。
CAt=Bt+1-Bt=Yt+rBt-Ct-Gt-It(7)
其中,CAt、Bt+1、Bt、Yt、Ct、Gt、It和 r分別是 t期經常項目余額、t+1期外匯資產余額、t期外匯資產余額、t期產出總量、t期消費總量、t期政府消費總量、t期投資總量和國際借貸實際利率。
2.1.3 存在國際借貸時的國內外經濟平衡
國民儲蓄總額St代表了國內財富總量的變動,即:
St=Bt+1-Bt+It=Yt+rBt-Ct-Gt(8)
因此,由(7)式和(8)式得,
CAt=St-It(9)
從上式(9)可知,從根本上講,經常項目是一種跨時經濟現象,當國民儲蓄大于國內投資時,國內對國外的凈資產增加,因而會出現經常項目順差。
因此,國內外經濟政策對經常項目均衡的影響要取決于該項措施對投資和儲蓄的影響,一般而言,利率r、生產率A、消費偏好β、政府支出等因素都會對儲蓄或投資產生影響。
以生產率變化為例,在利率r不變的條件下,對(6)式(即:A2F'(K1+I1)=r)的兩邊求導得:F'(k2)+A2*F''(k2)整理得

由(10)式得,如果第二期的生產率提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期的投資量將會增加,進而會在第一期出現經常項目逆差。
利率同樣會對國際收支均衡產生影響。以下圖為例,兩國封閉經濟狀態下的利率將分別為r和r*,而完全開放經濟下的世界實際利率降為r0,此時,兩國的經常項目余額之和將為0,任何高于或低于r0的利率都會產生經常項目的不均衡。

2.2 均衡匯率的確定
2.2.1 全部商品為貿易品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下的國際收支均衡和匯率確定
在資本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凱恩斯的利率平價理論和費雪的實際利率恒等式為國際收支和匯率確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即:

其中,it和it*分別是t期國內外金融市場名義利率;ef和e0分別是直接標價法表示的遠期和即期匯率。

其中,it+1和rt+1分別是t+1期金融市場名義和實際利率;Pt+1和Pt分別是t+1期和t期的全部商品的綜合物價水平。
在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貿易品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情況下,由上圖可獲得國際收支均衡時的世界市場均衡實際利率,根據(12)式可獲得既定貨幣政策(物價水平)下的名義利率,然后根據(11)式可得到均衡匯率的變動趨勢。
但我國面臨的現實情況并非如此:一是在貿易品之外還存在范圍不斷變化的大量非貿易品;二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因此,有必要在此背景下進一步考察非貿易品生產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2.2.2 存在非貿易品情況下的均衡匯率確定
為了進一步考慮實際匯率的確定,我們在模型中引入非貿易品。
令生產函數為資本和勞動投入的齊次函數,即:
y=Y/L=AF(K,L)/L=Af(k) (13)
其中,Y、K、L 分別是總產出、總資本和勞動投入;y、k 分別為單位勞動產出和資本投入;F()和f()是生產函數。
將商品分別區分為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則企業關于勞動和資本的利潤最大化一階條件分別為:
對于貿易部門:

其中,令單位貿易品的價格為1;AT、kT分別為貿易品的生產率及其單位勞動資本投入;r和w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價格;f()為貿易品的生產函數;f'()為貿易品單位勞動資本投入的邊際產出。
由(14)和(15)得,

其中,μLT為貿易品部門勞動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
對于非貿易部門:

其中,令單位非貿易品的價格為pN;AN、kN分別為非貿易品的生產率及其單位勞動資本投入;r和w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價格;g()為非貿易品的生產函數;g'()為非貿易品單位勞動資本投入的邊際產出。
由(18)和(19)式得,

其中,μLN為非貿易品部門勞動收入所占份額。
將方程(17)帶入(21),整理得

再令商品價格指數為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幾何平均數,權數分別為γ和1-γ,因此,國內外物價指數分別表示為:

其中,P為國內價格指數,PN為國內非貿易品價格。

由(25)式可得,本國的實際匯率取決于國內外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
再利用(22),并對(25)式取對數并求導,可得

在μLN大于μLT的情況下,若國內貿易品的生產率優勢大于非貿易品的生產率優勢,則本國實際匯率將升值。在此意義上講,實際匯率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貿易品的存在以及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生產率差異。
3 基于內外部經濟均衡的金融宏觀調控
3.1 開放條件下金融宏觀調控的基本思路
首先,經常項目平衡的調節應該著重關注內部經濟均衡。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經常項目順差實際上是國內超額儲蓄的結果,因此,國際收支均衡的調節根本上應從調節國內外投資和儲蓄出發,從金融調控角度出發,具體可通過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調節利率水平或提高生產率等措施,否則,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是一個缺乏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卻在近年出現了大幅度的經常項目順差,我們認為,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所致,例如,商業銀行限于不良資產率過高而出現“惜貸”現象,中小企業限于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而不能獲得貸款,居民的金融直接投資渠道缺乏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會阻礙國內的居民儲蓄順利轉化為投資,與此相反,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商投資企業卻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包括國外融資)獲得投資資金,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國內投資不足(這又可能造成資本項目順差),其結果是一方面是國內通過經常項目順差向國外輸出“超額儲蓄”資金,另一方面是通過資本項目順差借入國外儲蓄。因此,中央銀行應著重從疏通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出發,來采取措施消除大量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促進經濟更快更健康地發展。
其次,均衡匯率應該是考慮國內外綜合平衡的匯率,實際匯率及其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貿易品范圍(γ)、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生產率水平(AT和AN)。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貿易品的范圍將不斷擴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從(25)式可以看出,這將有利于人民幣實際匯率的穩定;另一方面,隨著我國貿易品范圍的不斷擴大,貿易品的生產率提高速度可能不同于非貿易品生產率提高速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根據(26)式,人民幣實際匯率可能發生波動。這兩種趨勢將會決定著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化,中央銀行應該積極采取措施,跟蹤我國貿易品和非貿易品范圍及其生產率的變化,并積極采取措施適時適度地調整人民幣匯率。
3.2 內外部均衡沖突與金融宏觀調控政策
隨著米德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提出的開放經濟下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很多學者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主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斯旺提出的支出轉換(升值或貶值的匯率政策)和支出變更(擴張或收縮的經濟政策)相搭配的政策配合和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搭配的政策配合。鑒于前一種政策搭配將匯率視作政策工具,容易引起貿易伙伴國的政策報復,因而具有實用的局限性。因此,從長遠來看,我國應主要采用后一種政策搭配策略,根據比較優勢原則,讓貨幣政策在調節外部均衡方面發揮主要作用;讓財政政策在調節內部均衡方面發揮主要作用。但是,根據克魯格曼提出的 “三元悖論”,一國不能同時實現資本完全流動、匯率穩定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三個目標,因此,我國目前還需實行一定的資本流動管制措施。從我國目前的具體情況來看,資本流動管制存在一定的不對稱性:資本流入比較容易、資本流出較困難。這種情況將使得目前人民幣匯率存在升值壓力時資本管制措施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因為外匯資金可能很容易從多種渠道流入國內,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此,我們認為,中央銀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從長遠來看,逐漸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范圍和頻率。這會從根本上杜絕中央銀行為保持匯率穩定而被迫吸納外匯的局面,從而增加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但是,這從另一方面會增加匯率波動性,從而給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更大的經營風險,客觀上要求我們通過進一步完善金融衍生品(如期貨、期權、互換等)市場,來培育更為完善的風險規避措施。
其次,從目前來看,應該積極開發貨幣政策操作工具,避免外匯資金流動對貨幣政策產生較大干擾。目前,處于穩定人民幣匯率的需要,中央銀行被迫大量發行央行票據來沖銷因外匯儲備增加而產生的大量流動性。這種做法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存在高額的操作成本,操作具有被動性,不利于培育外匯金融市場等等。為此,我們建議,中央銀行應該積極培育并參與外匯衍生品市場的開發和推廣。目前,中央銀行一方面應積極開發并推廣銀行間遠期外匯市場,通過參與銀行間遠期交易,中央銀行可以避免即期買賣外匯導致的基礎貨幣大幅波動;另一方面應該積極推廣并參與外幣和人民幣的互換交易,通過互換交易,也可以避免目前大量被動吞吐基礎貨幣的局面。總之,通過積極開發并運用外匯衍生工具,中央銀行可以同樣達到穩定匯率并采取獨立貨幣政策目的。
再次,金融調控政策的制定應綜合考慮我國當前金融管制現狀。眾所周知,我國目前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資本流動不對稱、利率尚未完全自由化,這三大特征將會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人民幣均衡匯率確定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前兩者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居民的消費水平,進而從客觀上促進了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特征和經常項目順差;利率管制也可能通過對儲蓄和投資的影響進而對經常項目收支產生影響。
第四,積極參與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當今各國開放的經濟在相當程度上存在相互依存性,一國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存在一定的溢出性(spill-over effect)。為此,我國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應認真考慮主要貿易伙伴將采取的政策反應,并積極同其進行政策協調。
[1]Barro,R.J.,Gordon,D.Rules,Discretion,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3,(12).
[2]P.Benigno.A Simpl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7).
[3]G.Benigno,P.Benigno.Price Stability in Open Economi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
[4]G.Corsetti,P.Pesenti.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
[5]M.Devereux.Should the Exchange Rate Be a Shock Absorbe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2).
[6]M.Devereux,C.Engel.Monetary Policy in the Open Economy Revisited:Price Setting and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C].NBER Working Paper,No.7665.2000.
[7]R.Dornbusch.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84).
[8]C.Engel.Real Exchange Rates and Relative Pric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
[9]J.A.Fleming.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C].IMF Staff Papers,1962,(9).
[10]P.Krugman.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M].Cambridge MA:MIT Press,1989.
[11]P.R.Lane.The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A Surve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
[12]R.A.Mundell.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63,(29).
[13]M.Obstfeld,K.Rogoff.Exchange Rate Dynamic Redux[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
[14]M.Obstfeld,K.Rogoff.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M].Cambridge,MA:MIT Press,1996.
[15]C.Walsh.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16]龔六堂,動態經濟學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7]Thomas J.Sargent.動態宏觀經濟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