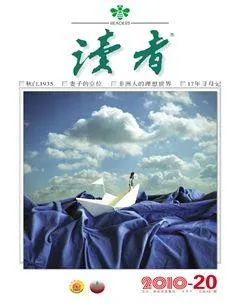考古不是挖寶
高蒙河
考古學(xué)這門學(xué)科的性質(zhì)決定了它必須毀壞所研究的對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發(fā)掘不是在翻閱地下的天書,而是翻一頁就撕掉一頁,甚至像碎紙機一樣粉碎一頁。如果我們沒有讀懂的話,就再也沒有任何機會去復(fù)讀和查證。所以,考古學(xué)沒有辦法像拍電影那樣可以逐條反復(fù)拍攝,不允許也不可能重復(fù)實驗直至成功。
考古結(jié)果無不伴隨著遺憾,猶如考古發(fā)現(xiàn)無不充滿著期待一樣,這已成為考古學(xué)家誰都邁不過去的火焰山。形成這樣的感悟是一個考古學(xué)家在成長中所必經(jīng)的階段,只不過期待往往發(fā)生在考古發(fā)現(xiàn)之前或之中,而遺憾總是出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中或之后。
發(fā)掘定陵是50多年前的一個偶然選擇,卻是那個年代里的一個必然結(jié)果。
定陵,是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合葬的陵寢,位于北京市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區(qū)。定陵的主人萬歷皇帝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歲繼位,22歲開始修建自己未來的壽宮,多次親臨陵址現(xiàn)場督察。陵寢在6年后建成,他卻在紫禁城中度過了30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幾乎從不上朝,也從不理政,直到長眠于這一座閑置了30年的地下宮殿。皇帝的地下玄宮是什么樣子?著名的《永樂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樂皇帝的陵寢里?這樣那樣的疑問一直吸引著人們,也困擾著像明史專家吳晗那樣的學(xué)者們,總想探個究竟。
1955年10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先生作為發(fā)起者,聯(lián)合了當(dāng)時的中國科學(xué)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國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等人,聯(lián)名上書國務(wù)院,請求發(fā)掘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陵墓長陵,獲得批準(zhǔn),盡管當(dāng)時它受到了來自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夏鼐先生等考古專家們的理性反對。
不過,吳晗等人上書請求發(fā)掘的長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積實在太大,一時難以找到墓道,考古學(xué)家們只好放棄原有計劃,決定先找一個小一點的陵墓進(jìn)行試掘,等積累一些經(jīng)驗后再發(fā)掘長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調(diào)查中,他們偶然發(fā)現(xiàn)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書發(fā)掘長陵計劃的試驗品。
當(dāng)兩年以后發(fā)掘完工時,考古人員已在反對無效卻又不得不參與領(lǐng)導(dǎo)的夏鼐先生的指揮下,歷盡艱辛地把地宮內(nèi)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來。遺物總計約3000件,絕大多數(shù)是萬歷皇帝和他的兩個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這些奇珍異寶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宮,原本是為了讓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繼續(xù)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300多年后它們被考古發(fā)掘出來時,大多已經(jīng)腐朽破碎。萬歷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爛,只剩枯骨了,而且他們的葬式看上去顯得很奇特。
在棺槨中發(fā)現(xiàn)的萬歷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細(xì)如發(fā)絲的金線,經(jīng)過拔絲、編織、焊接等非常復(fù)雜的工藝制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紅藍(lán)寶石和5000多顆珍珠鑲嵌的鳳冠,重2320克。色澤瑰麗、典雅莊重的鳳冠,比起輕薄似紗的皇冠要重了許多,肯定不適合經(jīng)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時才偶爾使用。這樣的鳳冠共出4頂。
金器和首飾永遠(yuǎn)是皇家的最愛。金器289件,幾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飾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發(fā)型和發(fā)飾同樣是用來彰顯皇家威儀的,僅次于皇冠和鳳冠。皇室的女性總是引領(lǐng)著新風(fēng)尚,這不由讓人感慨萬千。除了頭飾,定陵出土的衣物467件,也大多是供帝后穿戴的。但說到威儀,那還得說是萬歷大典用的5件袞服(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禮服,是古代最尊貴的禮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圣節(jié)等重大慶典活動時用的禮服)最為惹眼,這種用工10年的十二團(tuán)龍袞服,萬歷皇帝身穿1件,棺內(nèi)還放了4件。
與這些華貴服飾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隨葬品是織錦布料,總計165匹,僅萬歷皇帝身邊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還從沒有發(fā)現(xiàn)過數(shù)量如此眾多的古代絲織品,而且整匹的絲織品在出土?xí)r色彩依然艷麗。但這些每一件都堪稱精品的專為宮廷織造的衣物和絲織品,在發(fā)掘出土后卻慢慢變硬、變脆、變色、變霉……比出土文物的變質(zhì)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還在后面。
那是定陵發(fā)掘10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館大門前的廣場上,一大群紅衛(wèi)兵高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把萬歷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的尸骨砸爛后付之一炬。考古學(xué)家們精心發(fā)掘并用了一年多時間才拼合完整的帝王、帝后的尸骨,從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龔良院長主編的《中國考古大發(fā)現(xiàn)》一書中,特別記錄了有關(guān)萬歷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毀前后的一些細(xì)節(jié)。
郭沫若對萬歷的尸骨十分關(guān)心,他對考古發(fā)掘人員說:“萬歷帝一生多病,有人說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體變形,卻成了不解之謎。將來可用多種手段測試,凡能做到的都要詳細(xì)分析研究。”
“文革”中,吳晗在被捕入獄之前,曾以極其悲傷的心情對夏鼐說:“文獻(xiàn)記載,罌粟在明代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懷疑萬歷生前抽過大煙,可證據(jù)不足。本來萬歷的骨頭可以用來化驗,好證實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別想了。”他含淚說:“作銘(夏鼐的號),在定陵發(fā)掘這件事上,到現(xiàn)在我才明白,當(dāng)初我們的爭論,他和老鄭(指鄭振鐸)是對的,他比我看得遠(yuǎn)。”
“如果”二字,永遠(yuǎn)是遺憾的后悔藥。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幾十年,包括定陵在內(nèi)的整個十三陵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這個成為全人類共同遺產(chǎn)的昔日皇家陵寢,可能就不會被開啟;如果國務(wù)院最后不是出于長陵規(guī)模大,決定先試掘小一點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萬歷皇帝而不是永樂皇帝;如果吳晗先生不提出發(fā)掘可以開展對明史研究的學(xué)術(shù)理由,不認(rèn)為發(fā)掘帝陵建博物館才是貫徹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方針,才能對廣大人民群眾進(jìn)行階級教育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如果吳晗先生不是當(dāng)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專家;如果吳晗先生在鄭振鐸和夏鼐的極力勸阻后,慎重考慮,改變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請國務(wù)院……那就不會給中國考古留下一個永遠(yuǎn)無法痊愈的病灶標(biāo)本。這個標(biāo)本一直吊掛在中國考古的天空下,成為后來無數(shù)發(fā)掘帝陵言論的鎮(zhèn)靜符和冷卻劑。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為當(dāng)時吸取了定陵發(fā)掘結(jié)果不利于保護(hù)文物的教訓(xùn),才停止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掘計劃。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蘭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陜西省咸陽市乾縣附近的農(nóng)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聲過后,在清理碎石時他們發(fā)現(xiàn)了幾根石條。原來這炮點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條就是墓道的階梯。考古學(xué)家隨后對墓道進(jìn)行了清理,還發(fā)現(xiàn)了陵墓入口的金剛墻。如果打開金剛墻,乾陵地宮即可面世。但能不能發(fā)掘皇陵,不是陜西所能決定的。當(dāng)時他們組成代表團(tuán)進(jìn)京請示主管部門,向中央有關(guān)部門遞交了《乾陵發(fā)掘計劃》。當(dāng)時的文物局領(lǐng)導(dǎo)沒有明確表態(tài),建議他們?nèi)⒂^一下正在進(jìn)行發(fā)掘工作的定陵,結(jié)果定陵不盡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計劃再也無法實施下去。現(xiàn)在看來,定陵的發(fā)掘教訓(xùn)可以說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每年都吸引著數(shù)百萬游客來到這里。人們在被這個古老的中國皇陵深深折服,感受著一代皇帝的傳奇和魅力時,可能根本不知道關(guān)于它曾經(jīng)有過一個讓我們受用至今的細(xì)節(jié):當(dāng)年極力反對發(fā)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參加發(fā)掘定陵的鄭振鐸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書國務(wù)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準(zhǔn)發(fā)掘帝王陵墓的申請。當(dāng)年作出同意發(fā)掘批示的周恩來總理立即批準(zhǔn),隨后通令全國,試掘定陵后再發(fā)掘長陵的計劃,就此擱淺。
如果說發(fā)掘定陵有所收獲的話,那就是中國其他帝王的陵墓從此保住了!
(吳山摘自山東畫報出版社《考古不是挖寶》一書,鄺 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