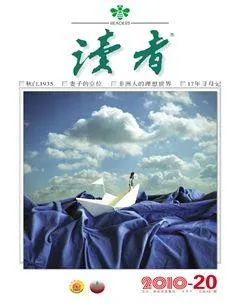得來全不費功夫
〔美〕阿爾·努斯鮑曼
這兩個人為什么選定老態龍鐘的哈特曼太太下手,誰也說不清楚。也許是因為她看上去年老體弱;也許是因為幾分鐘之前她才剛剛從銀行里走出來;也許,他們看中了她緊緊捏在手里的那只大背包;或是因為她徒步走過一個街區后便離開車水馬龍的大路,拐進一條僻靜無人的小巷。
可能他們考慮到其中某些因素,或是所有這些因素。總之,他們注意到她,把她確定為一個很容易對付的作案對象。他們來到她身后,一左一右將她夾在中間。左邊那人伸出腿將她絆倒。與此同時,右邊那人割斷她肩上的背包帶子,想把背包搶走。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并未像他們期待的那樣張開雙臂以避免跌倒,她摟著背包,兩手緊緊抓住不放。她摔倒在人行道上,他們聽得到她的老骨頭在噼啪作響,但是她仍舊攥著背包不放手。
其中一個人把背帶甩來甩去的那一端纏在手上,試圖用力把背包拽走,另一個人則用穿著方頭靴子的腳踢老太太。老太太沒有喊救命,也不曾尖叫。只聽得到幾只腳在地上來回摩擦,發出沙沙聲響,以及這兩個人迫使哈特曼太太放棄背包時發出的沉重喘息聲。他們決意一定要將背包奪到手,每一次猛拽背包帶子之時必定會順便踢老太太幾腳,逼她松手。可是她緊緊咬著牙、不要命地抓著背包帶子不放,表明她也決心堅持到底,就是不讓人搶走她的包。
可惜,這老太太甚至無法與其中一人匹敵,更不用說同時對付他倆。她感到劇痛、筋疲力盡,幾秒鐘之后便失去了知覺。他們從她疲軟無力的手中奪去背包,隨即溜之大吉,聽任她橫臥在人行道上。
沒有人看見那兩個人攻擊、搶劫這位老太太。過了差不多足足15分鐘,行人才發現哈特曼太太躺在路上。警察和救護車馬上趕到,可是那兩個人早已逃得不見蹤影。
人們把她放在擔架上,抬進救護車。這時她恢復了知覺,只是一會兒。她將充滿痛苦的目光投向一位站在她身邊俯身望著她的穿警服的警察。她的聲音十分微弱,幾乎聽不到:“我的錢,他們搶走了我的錢包,我的錢全在里面!”
那警察問:“丟了多少錢,太太?”
過了一會兒,她才回答道:“三萬三千元。”說完,她便又昏過去。
她沒能細說,但是這數額足以將這次搶劫由小過失升格為重罪。通常,攔路搶奪不算很嚴重的罪行。警方派來4位偵探在醫院的急救病房門外等候,以便待她蘇醒后再詢問她細節。與此同時,同樣數量的報社和電視臺記者也齊聚醫院,伺機采訪。
待人們把哈特曼太太推出治療室,她活像木乃伊,兩條胳膊、一條腿打著石膏,頭上裹著繃帶。不過她神志尚算清醒,能回答幾個問題。肯德瑞斯警官,一個40多歲的魁梧漢子,作為代表出來問話。新聞媒體派來的記者只能在一邊湊合著聽聽他們說什么,拍幾張照片。
肯德瑞斯問道:“哈特曼太太,你能聽到我說話嗎?”
“嗯。”她有氣無力地答道。
“在他們發現你的地方,你告訴那位警官你被搶走三萬三千元。是這樣嗎?”
“是的……”
“為什么會隨身帶著那么多現金呢?”
仿佛是在字斟句酌,哈特曼太太踟躕一陣才說:“我……我是一個愚蠢的女人,有時候會犯傻。每年一次,有時是兩次,我會把存款從銀行里全部取出來。我把錢放在家里,看一看、摸一摸。過幾天再存進銀行。這一次……”她的聲音越來越小,“我把錢全弄丟了。”
“你能認出那個賊嗎?”
“他們有兩個人,可我以前從沒見過他們。假如再見面,我沒有把握認出他們,那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時醫生給她服下的鎮靜劑發生作用,她睡著了。
那位護士說:“肯德瑞斯警官,如果你還有問題要問,只好明天再來吧。”
第二天下午,肯德瑞斯警官沖進醫院,像一頭發怒的熊。但是他沒能同哈特曼太太說話。她整天都在睡覺,醫生不準肯德瑞斯喚醒她。
肯德瑞斯第三天又來了。他已平靜一些,可是仍看得出在生悶氣。哈特曼太太靠著床頭坐著,一個高中生年紀的志愿者正在給她讀報。肯德瑞斯讓那姑娘先在門外等等,好讓他同哈特曼太太單獨談話。
那姑娘一出門,肯德瑞斯便質問道:“好了,你為什么要對我撒謊?”
哈特曼太太道:“我……我不明白你在說什么。”
“得了!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三萬三千元。這起搶劫案在報紙和電視上有很多報道,可是我去銀行調查時才了解到,你從來沒有在那里開戶。他們見到你時,比如前天,你是去兌現社會福利金支票的。你為什么要撒謊呢?”
這個受傷的女人攤開手,又并攏在一起,隨后又攤開,一副無助的樣子。“我不想讓那兩個賊就這樣跑掉。我……我要讓他們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價。”
肯德瑞斯仍不想就這樣放過她。“可是,你沒有必要撒謊。你是知道的,我們同樣會努力工作,會盡力想法子找回你的社會福利金。在我們看來,它與那筆數額巨大的錢同等重要。”
哈特曼太太沒有立即回答,這使得肯德瑞斯有時間回味他剛說過的話,領悟那是多么不近情理。起初他們認為三萬三千元被人搶走,便派了4名偵探調查這個案子,記者們也在跟蹤報道他們的行動。現在呢?只有他一個人還是正式受命調查此案的警官,而且調查只會延續到他回到辦公室里,將報告歸入“未破案”卷宗之中那一刻。至少,良知尚能使他感到慚愧。
哈特曼太太說:“哦,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相信警察會盡力而為的,不論那筆錢是多是少。”聽到這番話,肯德瑞斯不免覺得她有點兒言不由衷。這個被人痛打了一頓的老婦人表現得很能理解他,甚至比自己對她的同情更貼切,這益發令他覺得很難為情。
他想就此打住,不再往下說。“好吧,我們就把這件事忘掉吧。”他朝門口走去,一邊說:“若是有什么進展,我會通知你的。”說完,他便走出病房。
那個年輕的志愿者回到病房里,拿起肯德瑞斯剛才進來時她放下的報紙,在床邊坐下。
“要我再給你念一段嗎?”她問。
哈特曼太太說:“好啊,請讀讀殺人案的那一段。”
姑娘抗議道:“可是我已經讀過4遍了。”
“我知道,不過請你再讀一遍。”
姑娘清清喉嚨讀起來:“昨晚10點左右,警察調查了第七大道895號一套公寓里發生的騷亂。他們發現兩個人死在廳里的地板上,死因是持刀械斗。這兩個人是威廉·懷特和杰西·博爾特,他們合住在這套公寓里。鄰居們說,今天這兩個人幾乎整天都在爭吵、斗毆,指責對方騙走了一筆數目不詳的錢。最終兩人動了刀子,結果兩人都被對方殺死。他們都有長期坐牢的記錄。警方還在繼續調查此案。”
哈特曼太太張開青腫的嘴巴笑了。她柔聲道:“請再讀一遍。”
(寒塘鶴影摘自《視野》2010年第17期,李曉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