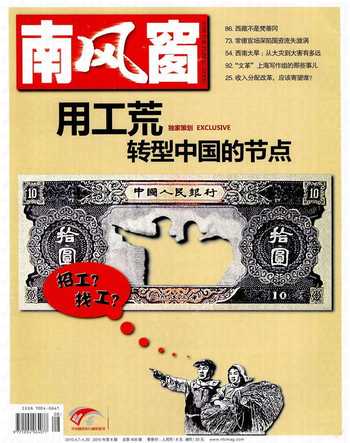山西煤老板的轉型煩惱
廖海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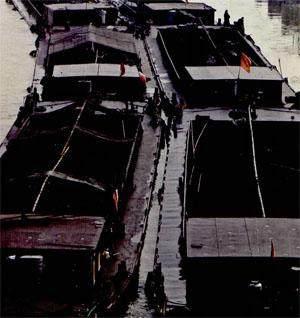
煤老板趙一山決定進軍農業,一方面是因為熟悉,一方面出于“國家扶持農業的力度將持續加大”和“農產品價格將上漲”的預期。這兩個預期不能說錯,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趙一山的身上體現。
2010年3月28日,位于月壇南街的國家發改委大樓沉浸在陰雨綿綿之中。
傳達室里人頭攢動,僅有的幾條凳子早已經被人占滿,人們三三兩兩的低頭耳語,不少人身后還拖著行李。來自山西的胡潤貴站在門口的角落里,焦急地不時掏出手機來看。按照規定,外來人員要進入發改委大樓,必須得到里面人的首肯,并到傳達室交驗證件,方可獲得進門的通行條。為了等待來自“里面人”的指令,胡潤貴已經足足等了一個小時。
5分鐘面試
終于,從傳達室的窗口傳來一個女聲:“山西的胡潤貴是哪位?”胡潤貴趕緊沖過去:“我就是!”傳達室的大媽連眼皮都沒抬,“身份證帶了沒有?”
這種冷淡讓胡感覺有些小小的不適應。他曾經任山西某縣主管農業的副縣長,現在是一家大企業的總裁,在當地也算叫得響的人物。但在這位門房大媽面前,似乎脾氣也沒有了。
不過,當接過門房大媽遞過來通行條時,他還是長長松了一口氣。要知道有很多老板在發改委門口轉悠了半年,請客送禮無數,上當無數,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跟這些人比起來,他已經算幸運的了。
胡潤貴登上6樓,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最西段的農經司年度計劃處。門是半開著的,不大的辦公室內擺了5張辦公桌,顯得擁擠甚至有些凌亂。但這個看似簡陋的辦公室,卻掌管著全中國年度農業投資計劃的審批大權。
接見他的是年輕的處長,溫和親切,滿面笑容。胡潤貴連忙將材料遞過去,充滿期望地看著對方。誰知迎接他的卻是兜頭一瓢冷水:“你們來得不巧,年度計劃今天剛剛發下去了”。處長微笑著說。
沒等胡潤貴反應過來,處長又接著說:“再說,你們個人企業應該先報到省里,再到國家發改委備案的,直接找我們沒意義啊!”
“我們擔心的是省里通過了,結果國家發改委通不過,等于白忙活,所以先到您這里來了解情況,也好有個底。另外我們還擔心,如果先報到省里,省里會不會往上報呢?”
“你投資這么大,省里如果沒有配套資金,肯定也不會往上報的。”
胡潤貴顯得有些失望。但他自然不甘空手而回,短暫的沉默之后,他問道:“不管怎么樣,關鍵您看看這個項目有沒有審批的可能?”
處長把材料擺在桌上翻了翻,不禁啞然失笑:“你把這么多不同的項目打包上來,哪一個司都不敢批啊!你拿回去好好改改。”
會見就此結束。胡潤貴抬腕看表,整個過程沒超過5分鐘。
煤老板的煩惱
胡潤貴垂頭喪氣地打車來到位于王府井的東方君悅酒店,在那里,公司董事長趙一山正在等他的好消息。
生于1961年的趙一山農村出身,曾是山西省古交市的一個煤老板,中等身材的他,腆著個大肚子,一襲金黃色的唐裝,右手戴著一顆新買的祖母綠戒指,跟記者握手時,他“啊”了一聲——被戒指硌痛了:
趙一山的第一座煤礦正式開采是在1994年,彼時,一噸煤價值17塊錢,隨后一路猛漲,最高時漲到1000多元一噸。業務最紅火的時候,他一天的收益超過百萬。從2003年起,古交小煤窯的轉手價格被節節炒高,趙一山又出手購入了3個煤礦,轉讓費用過億。然而,在經歷本輪“國進民退”之后,趙一山日進斗金的故事被劃上了休止符,他的煤礦被悉數收編了。
“每個礦國家只賠了900萬,實在是太虧了。”他摸了摸額頭,把臉轉向一邊。
但日子還要繼續。農村出身的他決定轉向他熟悉的行業——農業。其實要說熟悉,也僅僅限于會種地而已。
去年,他和一個自稱留美博士的人合作建設純種安格斯牛培育基地,基地還沒建起來,那人就卷款潛逃,至今杳無蹤跡。
趙一山現在最大的項目是有機肥廠已經投資了8000萬。此外,他的計劃書上還包括5萬只規模的養豬場、2000畝生態林、7000平方米的連棟智能溫室等,總投資超過10億。
他計劃把這一攬子項目打包成一個大項目向發改委申報,從而獲得國家的大力支持。文化不高、對政策了解有限的他,為了方便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不惜重金把曾任副縣長的胡潤貴請過來當總裁。按照他的設想,隨著公司轉型發展,不僅可以解決大量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在給農民增收創造條件的同時,還可以發展當地的農業旅游資源。
煤老板趙一山天真地以為,有了這么多好處,國家發改委沒理由不批。但胡潤貴的匯報讓他徹底斷了念想。
“鬧了半天原來我們是一廂情愿啊!”他不無懊惱,把戒指摘下在桌上猛敲幾下。
“看來只有把項目分拆了,但這樣的話,國家發改委最多給你200萬的專項資金,地方配套大概指望不上了”。胡潤貴說。
“那就沒意思了,毛毛雨,還要給他們做賬……”趙一山撇撇嘴,有些不屑地說。
趙一山當初決定進軍農業,一方面是因為熟悉,另一方面出于“國家扶持農業的力度將持續加大”和“農產品價格將上漲”的預期。這兩個預期不能說錯,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趙一山的身上體現。
“幸虧當初沒有一頭扎進去,不然就進退兩難了”。他悻悻地說。
碰了壁的趙一山打算轉向另一個領域。他2008年在廣西東興和河北邢臺買了兩塊地,打算開發房地產,但出于對樓市泡沫的憂慮一直沒有動工。現在農業的項目眼看是要黃了,而房價又節節高升,進入樓市就成了他唯一的選擇。
轉身之難
趙一山是山西煤老板轉型發展的一個樣本。
經過本輪國進民退,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礦將只保留1000座。這意味著,山西數千名煤老板將從煤炭產業退出,進入新的投資和產業領域。據業內人士估計,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約有3000億元的資金,而國內投資渠道狹窄,煤老板的巨額資金將投向何方亟須政策引導。
據山西省煤炭工業協會一位官員介紹,煤老板轉型在山西已經是普遍的現象,但成功的并不多。“煤炭太容易讓人暴富了,利潤太高,操作難度又不大,大家都在找項目,但還能有哪一個行業能像開煤礦這樣賺錢呢?”
“小煤礦利潤大,但屬于粗放式管理,高科技和服務業,既要求精細管理,更有技術門檻;人才、管理技術跟不上顯然具有很大經營風險。”山西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周明定表示。
上述煤炭工業協會人士稱,山西省小型煤炭企業主大多數只有初中文化水平,這幾年各地加大了對他們的教育培訓力度,也限于煤炭業的政策法規和安全生產知識。
“這些土生土長的煤老板再重新選擇一個產業來創業很難,受本身素質能力所限、產業轉型所需市場環境不成熟等因素,容易因為輕率冒進而失敗。”
對多數出身農村的煤老板來說,選擇農業和養殖業是自然而然的事。據了解,目前山西省共有610個煤焦鐵企業創辦和轉產農產品加工業,形成投資總額68億元,其中投資上億元的企業有23家。但農業受自然和市場風險雙重影響大、周期長、利潤薄,這對習慣了日進斗金的煤老板們來說不啻是一種考驗。
同時,民營企業投資受到的制約和瓶頸很多,也是“煤老板”轉型困難的重要原因。土地、資金、人才、管理、技術、信息缺一不可,這些要素的取得,對于國有企業可能容易一些;但對于民營企業來說,獲取成本依然很高。
山西省農業產業化領導組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一些轉型企業盡管在社會上形成一定影響,但考察中發現大都還在建設中,沒有形成生產能力。”山西省農業廳廳長孫連珠亦承認,山西省進行農產品加工業的龍頭企業規模小、布局散,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帶動能力還不夠強。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潘云指出,在一些煤老板轉型成功的同時,還有不少煤老板的重新投資帶有盲目性,建議政府采取措施,運用金融、產業政策的“杠桿”給予更多的引導和支持。使其走上有利于全省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來。
對整個山西省來說,煤老板的回歸關乎當地經濟結構調整大計。2009年8月19日,山西省政府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做大做強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的意見》,提出實施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513”工程。11月10日,山西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513”工程啟動,作為配套,省財政等部門拿出大約3億元用于扶持龍頭企業發展。省級交通部門、水利部門、金融部門也有相關的優惠配套措施。
但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煤老板投資到農業上來,以及投資后能否實現良性發展,這一切尚待時間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