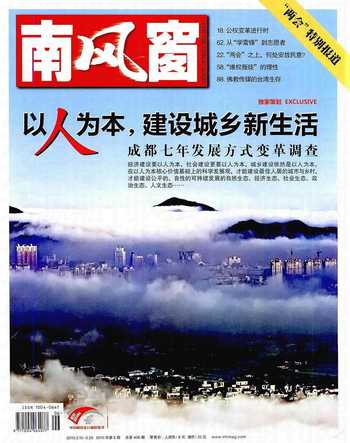“維權叛徒”的理性:龍泉征地糾紛全記錄
石 破
龍泉征地案中,地方政府的進步表現在終于知道站在農民的立場考慮問題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與農民打交道了。而農民代表在類似聽證會的場合往往不知所措,不習慣與政府進行理性的討價還價。事實表明,政府越替農民考慮得多一些,直接沖突就少一些、不穩定因素就少一些。
“我們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浙江龍泉農民張麗峰反復念叨著這兩句話,他快被這個念頭給弄魔怔了。
8年前,張麗峰是龍淵一村的農民維權領袖,帶領83戶被征地村民與龍泉市政府、浙江省政府打官司,驚動國務院下來裁決書,責令浙江省政府改正征地程序中的錯誤。但,政府到底還是把地征到手了。因應著村民們的不滿意,政府的征地補償條件一再優惠,然則不滿的村民仍舊不滿,上告的村民還在上告,只是張麗峰已然出局。
“我們是輸了吧?……還是贏了?”張麗峰喃喃地問。
錦旗感謝國務院
龍淵一村的征地糾紛事件源于2002年。龍泉市要建設“麗水地區西部中心城市”,唯一的辦法是城區向東拓展,市政府計劃征地2000多畝,包括龍淵街道一村土地15.4228公頃。
與農村的大多數征地糾紛一樣:政府貼出征地公告;農民對補償標準不滿;政府找農民談判,在征地工作組累計6000人次的“說服”壓力下一村14個生產小組中有11個簽字領了征地補償款,只有一、三、四這3個組的83戶農民仍不答應。隨后是2004年3月11日,政府組織大批人馬強行征地,農民以血肉之驅誓死抵抗。龍泉市副市長曹新民說:“政府考慮穩定問題,撤回了,隨即完善法律程序。”
2005年1月,市里拿到了省政府的征地批文:“龍淵一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制土地,用途為城東安置區,性質屬未利用地,同意龍泉市政府征地。”5月中下旬,市政府發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及征地補償方案公告,張麗峰等村民立即提出召開聽證會的申請。6月12日,市政府召開征地聽證會。會上的爭議焦點并非征地補償問題,而是龍淵一村15.4228公頃土地到底是耕地還是荒地(未利用地)?雙方爭持不下。
7月7日,張麗鋒等村民向浙江省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仲裁。11月14日,省政府出具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征地批文,但針對審理中發現的問題,向當地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發出法律意見書,責令對征地過程中有關問題進行糾正和完善,并切實做好當地農民工作,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事情就從這時起,開始變得不同——一、張麗峰等農民決定聘請律師打官司,經人介紹,他們認識了北京律師張星水。二、張麗峰等人和張星水經過商議,決定上訴到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這是一件絕對新穎的事情。香港媒體后來報道說:“……村民們都已打定輸數,因為就連他們的律師也說,從未聽說過國務院會推翻省政府的決定。”
但,2007年2月1日,國務院做出最終裁決,推翻和修改浙江省政府的兩項行政裁決,認為涉案的土地,的確是村民所說的耕地,并非未利用地。國務院并指龍泉市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未將土地現狀的調查結果事先交農民確認,程序上有瑕疵,責令浙江省政府完善批準收地手續。這是1999年《行政復議法》通過以來,第一起國務院推翻和修改省級政府行政裁決的例子,
2007年3月,張麗峰拿到了國務院的裁決書,立即張貼到村里。北京律師張星水第三次來到龍泉,大家一起微笑,村民們老老實實地覺得開心。“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我們共同來慶祝比較圓滿的勝利……”張星水跟村民們說。他估計全國有5000萬農民面臨與龍淵一村類似的收地糾紛,但只有張麗峰他們得到了國務院的支持,是幸運兒。
一切都值得贊美。張麗峰一下做了5面錦旗,感謝國務院、感謝律師及為他們牽線搭橋、奔走呼吁的學者、記者。村民們在寬敞的房子里舉杯慶賀,屋子里充滿了喜氣,久違的歡樂蘇醒起來,似乎什么都變了。張麗峰樂觀地跟記者說:“國務院裁決書下來之后,政府不再提起我們的土地征收一事,我們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繼續耕種了!”他還興沖沖地在網上“為被非法征地的農民兄弟支招”。
事實證明,張麗峰樂過了頭。
為什么不談?
國務院的裁決書成為龍泉征地糾紛案的分水嶺,龍泉市政府充分意識到了征地問題的復雜性。從2005年起開始分管土地工作的龍泉市副市長曹新民對記者說:“國務院裁決對我們的觸動,一是使我們認識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二是認識到化解征地矛盾的手段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市政府有人私下跟張麗峰講,當初龍泉市政府就是按占用耕地的標準補錢給農民的,但占用耕地開發要繳開墾費,為規避這筆費用,政府才上報成了荒地。國務院裁決書亦認定:“龍泉市人民政府對征收土地按照耕地而不是未利用地的標準進行了補償,同時給予10%的留地安置,并采取多種途徑安置申請人,補償安置措施合法。”
因此,在政府重新完善征地的法律手續之前,農民們只是贏得了一刻喘息的機會。國務院行政復議司副司長方軍跟張麗峰等農民說:“政府的地是一定要征的,你們要考慮清楚。我們責令地方政府完善手續,荒地改耕地,但完善手續對政府很簡單。你們要抓緊時間與政府談判。”
但農民覺得有人幫了,腰桿子硬了,不屑于跟政府談判。雨散云收后,村民內部也開始分裂,原來的團結如水汽一般升化。為打這場官司,張麗峰等人花了十幾萬元,原本說好村民每一畝地出200元作為官司費,但有人不愿出了:“官司也不是你們打下來的。”有人覺得沒拿到實在的好處。還有人說:“中央與下面(地方政府)是一伙的,等荒地錢補上去,中央就又站到下面政府一邊了。”
當初,龍淵一村農民去省里申請行政復議時,省里讓農民與市政府談判,農民堅決不肯,堅持要種地。官司打到國務院后,行政復議司副司長方軍兩次下來調查,也讓農民談判,并建議村民向政府提三個條件:一是征地補償價格適當提高,二是在龍泉市區范圍內優先挑選位置作為農民建房留地,三是村民蓋房時審批優惠。
“……但為首的村民不肯談,我想出面談,又被看成是叛徒。沒辦法,繼續告吧。2005年12月我們告到國務院,2007年3月拿到裁決書,國務院拖了一年半才裁決。”張麗峰說。
長久的對抗之后,局面重歸平靜,但張麗峰等農民的心蕩來蕩去。終于,巨大的陰影卷過,雷雨的日子開始了。
2007年8月,龍泉市政府又貼出兩份公告,省里的批文下了“荒地改耕地”,還是要征。市政府派人做張麗峰的工作:“不要再告了,能談就談。”張麗峰暗想:“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我也沒法再告了,難道要我去上訪?上訪又有什么用?”
政府再次組織聽證會,張麗峰等村民代表都去了。回來后,村民小組開會,有人建議跟政府談判,但村民提出的條件過高,
會上未形成統一意見。
2007年9月15日,政府組織千人隊伍來龍淵一村強拆,搞掉了七八十個菜大棚。有百十名村民前去反抗,警察抓走幾個鬧得厲害的婦女,關幾天又放了“政府組織第二次強拆,比第一次阻力小些。”曹副市長說,“根本原則,土地是國有的,我們有征用土地用于城市發展的權力。城鎮化建設的目的是進一步聚集人口,不在城區征地,難道要市民都搬到山溝里去住?也不現實。”
“千人拆遷”第二天,3名新華社記者來龍泉采訪,一到征地現場就被市政府請去了。市政府說:征地經國務院裁決,所有手續已完善,程序合法。記者無功而返。
政府強拆后,農民們法律維權的路已走到頭了。他們去省里信訪,省信訪局的人挺客氣,當著村民面給龍泉市政府打電話:“你們要好好解決!”結果一點作用也沒有。村民們的心“半晌涼初透”。他們去浙江省政府申請第二次行政復議。不久,省政府寄來書面答復:你們申請復議的事項,已經國務院法制辦最終裁決,我們不再受理。村民不甘心,又一次告到國務院法制辦行政復議司。行政復議司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張麗峰,也說他們不能再受理了。張麗峰:“我跟那幾位骨干村民講,他們不信,懷疑我被政府收買一自己又往行政復議司寄了一份申請,結果人家打電話來,說我已經對張麗峰講得很清楚了,你們為什么還要寄?”
這件事傷了張麗峰的心。“我帶著村民打這么多年官司,沒拿過政府一分錢,他們為這點小事懷疑我……律師也跟我說:張麗峰,集體的事情最難辦。我當了20年律師,最怕接集體的案子。”
張麗峰認為,2007年9月15日被強制征地后,村民已然失敗了,應該從失敗中求小勝,提過高要求不現實,能談多少是多少。“想想我們以前怎么這么笨?都告到國家最高機關了,在過去這就算是到皇帝跟前了,連他都讓你談,你為什么還不談?”
龍淵一村的一、三、四3個小組,很多村民都沒領政府的征地補償費,現在一看地已被政府強征,領吧。只有28戶村民仍沒簽字領錢,但有些也準備領了。張麗峰比較尷尬。雖然他被村民孤立,不贊成繼續跟政府對抗,卻也沒好意思去簽字領錢。
“這時候龍淵的大部分村民已默認現狀,沒辦法。”張麗峰說:“簽協議前沒跟政府談判,等到政府把手續弄合法了,你還能怎樣?現在政府要強制執行了,農民說‘沖,殺他們幾個!真到時候沒一個敢沖的,沖了你就是妨礙公務、聚眾攻擊政府機關、擾亂社會秩序。”
在當前形勢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較真,最不怕你胡攪蠻纏,最喜歡你跟他武斗。但農民認為政府就是強盜,是賊。我讓他們跟政府談,他們當我是叛徒。”
政府似乎越來越知道該怎么辦。據村民們說,龍淵一村的征地,政府原規劃是一個叫“城東花園”的商品房開發區(政府否認),2008年,政府修改了規劃,將這里作為龍泉市人民醫院的新址,由政府投資2.1億元,規劃將其建成浙、閩、贛邊界中心醫院,這是政府加大公共建設項目投入,帶動龍淵一村地段升值的項目之一。龍淵街道辦書記李先頂說:“農民留地如果全是居民區,升值空間不大,現在龍泉市中心小學、幼兒園、龍泉一中都建在一村旁邊,還規劃在這里建兩座公園。此外,市里還將一村附近的北沙路規劃為城市道路,投入700多萬強化水電路,改善一村的生活設施。”
李先頂介紹:龍淵一村的地被征后,10%的土地劃撥給村里,作為后續經濟發展用地,搞二、三產,原則上只能有7%用于住房困難農民的住宅用地,但市政府應一村村民要求,全部給農民用于建住宅。市區一般地段每植地基的出讓價為20萬元,一村留地在學校、醫院帶動下,每植留地價值平均在30萬左右,在龍泉是最高的。
張麗峰也說:“現在一村的留地位置算是最佳的了,左前方是醫院,右前方是小學。學校三四千名學生,去年9月1日蓋好,學生已經搬進去了。”
李先頂說:“一村農民抵制征地,擔心政府報復,審批留地建房時會卡他們。今年1月14日,市政府出臺了會議紀要,專門為一村農民蓋房開辟審批綠色通道。農民留地建房原規劃蓋4~5層,現在可加到5~6層,加這一層不得了,整個村又是幾千萬元的事!市政府明確態度:不能因為一村反對過政府征地,就說政府與農民誰輸誰贏的問題,應該是‘共贏……8年過來了,不能無休止地折騰下去了。”
農民的綠洲
2010年1月30日早晨,天陰雨濕。龍泉市區東盡頭,躺著荒寂的農田。這原本是一片膏腴之地,地里的菜棚已拆,拉起了圍墻。幾個老農圍著記者議論。他們的農田將在嶄新的城市里永遠消失。
龍淵一村的農民維權隊伍里,本有幾個年輕人,但他們在本地做生意,經物價、工商等部門“勸說”退出了。張麗峰也做小生意,他將生意停了。政府拿他沒辦法,但跟他繼續維權的骨干都是些五六十歲的老農,他們種了幾十年地,除種地外不會干別的,地被拿走他們更恐慌。張麗峰退出后,這些老農去北京、去省里上訪,給國土資源部、省市國土資源局寫信,向紀委反映情況,甚至給溫家寶總理寫信告狀,都是一個理由:我們不簽字政府就把地收了,是違法的;我們靠土地生活,沒了土地,我們沒法活,政府應該管。
經歷了早期的成功與挫敗后,在失望和絕望包裹的沙漠中間,上訪成了農民唯一追逐的綠洲。去北京上訪可不同于向國務院申請行政復議,農民們向著一個陌生的方向前進,越過一崗又是一崗。他們的笨拙被人賞玩;希望好似秋天的樹葉,不斷搖落。
“我們去了中紀委、國務院信訪局。官員說普通話,我聽不懂……”一個叫管新年的農民說。那你們去反映什么問題呢?“我們沒簽字,政府強征我們的地就是違法的。”但是政府有合法的征地手續呀,“我們沒簽字就不合法,征我們的地得我們同意。”但是村里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呀,村民組織法規定,不是100%村民簽字才合法,只要大多數村民同意就有效。“他們同意是他們的事。我們種了50多年地了,一年能掙5萬來元。地征了,我們沒活路了!”管新年的語氣中,悲愴伴隨著狂熱。
記者提到政府在開發醫院等公共設施項目,農民們不屑地說:“蓋醫院對我村沒有多少利,又不是杭州的大醫院,一天能有幾個人看病?”
一村4名上訪農民在北京呆了一周,被警車送了回來。管新年說,這一趟他們每人自掏腰包2000元,總共花了近萬塊錢。
“叛徒”張麗峰
張麗峰打官司出名后,到他這里來取經的農民很多,但真想學他的很少。這些農民很固執,從內心認為自己的選擇是對的,還打算走與政府對抗到底的就這令張麗峰很無奈。
“我給農民辦成那么多事,村里沒有一個人說我好。”張麗峰說,“國務院裁決下來后,沒有一個村民跑到我家說‘你辛苦了!我
們跟政府打幾年官司,現在地價漲了,村民也沾了光,但沒人感謝我。農民建房審批費從4萬多減到3萬,但老百姓要看現錢,你現在給他100元,比承諾將來給他1萬元還值錢。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原來個人最低要繳7500元,60歲后每月領80元。我們告到國務院后,現在個人只繳500元,60歲后每年給400元。你活到70歲,就等于拿回本錢了。”
2009年12月,上海記者翟明磊、浙江奉化維權農民張召良來龍泉,跟村民分析形勢。張麗峰說:“張召良、翟明磊都勸我們談判,形勢對我們不利。有些一心想告的人也轉過彎了。也怪我們自己,這么多次的談判機會都錯失了。政府一直想談,但村民意見不一致。”
張召良,浙江奉化市農民,因質疑家鄉長汀村的征地批復,提請浙江省政府行政復議,遭拒絕后,將其告上法庭。2006年4月,省高院判其勝訴。張召良成為中國第一個運用法律手段告贏省政府的失地農民。
張麗峰說:“張召良是一直要求政府跟他談,政府不談。我們是政府要求談,我們不跟政府談。”
2010年1月29日,聽說張麗峰來到溫州,附近的瑞安市陶山鎮霞林村幾個農民也來溫州看他。
1998年和2006年底,瑞安市政府先后兩次征收霞林村土地130多畝,出讓給兩家公司。村民們認為政府征地未征求全體村民意見,補償過低,抵制強征。接著,瑞安農民向張麗峰學習,也向國務院提起了行政復議申請,但這次國務院卻維持了地方政府的決議,因為政府的征地程序是完善的。張麗峰惋惜地說:“他們丟掉了政府完善手續前的機會,等到政府把所有手續完善,再申請行政復議已然晚了。”
但瑞安農民不甘心失掉土地,搭寮守護,在田里睡了3年,與政府僵持,那100畝地撂荒至今。瑞安農民的“領頭大哥”林存漢,50來歲,身材高大。談話中,他從身上掏出一伸縮式鐵棍,唰地一下,從鞘里甩出一尺多長的棍頭。林存漢說,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十幾人闖入他家,將他愛人痛打一頓,手臂打骨折了。那天他不在家。現在不管走到哪兒,林存漢都帶武器防身。
張麗峰說:“他們來找我,我都是千叮嚀,萬囑咐:維權首先要保護好自己,千萬不要和政府搞暴力,要理性維權、非暴力維權。在當前形勢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較真,最不怕你胡攪蠻纏,最喜歡你跟他武斗。但農民認為政府就是強盜,是賊。我讓他們跟政府談,他們當我是叛徒。唉,農民都是倔脾氣,只知進攻,不知撤退,也沒有一個可以適當讓步的目標。等搞到沒有土地了,想跟政府談判,手里沒籌碼了……”
2010年1月30日上午,龍淵街道辦黨委書記李先頂,帶記者登上市區附近一座山,鳥瞰龍泉市區。6萬人口的龍泉市區,四面皆山,三面環水,可用的土地已征得差不多了。市區14個城中村,僅剩1000多畝尚未開發,包括龍淵一村的600多畝。
李先頂說:“農民都愿意被征地,只是對補償標準不滿意,農民有意見,我們通過各種方式說服。過去缺乏溝通,應該學會協商妥協,每—方都要做出必要的讓步,農民權益才能得到維護,不能完全是斗爭的方式。”
李先頂承認,一村農民打官司后,政府的征地難度大了,但他說:“一村的村民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用這個武器捍衛權益,我認為從法律角度看是一種進步。”
20lO年1月30日中午,張麗峰的舅舅聽說有記者到龍泉,馬上趕過來見面。他現在是龍淵一村繼續為征地問題上訪的骨干人員之一,之前他們去過北京,也去過省、市信訪局、國土資源管理局等部門上訪。
“我們到北京后,先去中紀委。中紀委寫條子讓去國務院信訪局。有人跟蹤我們到信訪局門口,警察把我們抓到車上,送回來了……上次去的時間不對,烏魯木齊事件正好發生。如果政府沒有明確的答復,我們還要上北京。”
農民上訪的具體要求是什么呢?張舅回答:“我們去北京問‘沒飯吃怎么辦?因為我們還沒簽字,他們就把地賣掉了,現在我們是小康,地賣掉了,生活水平馬上掉下來了……以后我們沒飯吃就要找政府!”記者手記
失地農民可憐嗎?答案是:是的。農民是土地的命根子,但這命根子卻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代表國家將它拿走,因此農民自然產生的反應就是:你拿走了我的命根子,就得給我一條新活路。征地不是簡單地把農民正在耕種的地拿走,再給一些補償的問題,要考慮到農民對土地的眷戀、失地后的恐慌,予以細心的安撫、妥善的補償安置,不然就極易導致突發性事件發生。
農民不僅要勇于維護權益,還應善于在社會本身的結構內找到保護自己的方法,學會在理性的指引下與政府談判,討價還價,而不是抱著要么全敗、要么全勝的心態。農民受限于自己的習慣,不屑于也不懂得與政府換位思考,以獲得對征地問題的全局性、復雜性的認識。實事求是地說,農民中懂法的不多,更多的農民習慣性地認為,政府征地就是對農民利益的暴力掠奪,應該“以暴易暴”,堅決捍衛自己的權益。而媒體對農民抗爭行為的簡單喝彩,也往往會掩蓋真正的問題,并使農民迷失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和時機。
龍泉征地糾紛案中有趣的一點,是農民在維權中引入了精英力量,精英與農民同步運作,相互配合,終于換來了一紙國務院最終裁決書。這對農民確然是一個勝利,不管政府承認不承認。媒體對國務院裁決的過度解讀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即令是國務院法制辦,此后也未出臺過第二起對省級政府決定做出更正的裁決。然而,過度解讀也容易引起人們的盲目樂觀,而忽視問題的復雜性。
龍泉征地案中,政府的進步表現在終于知道站在農民的立場考慮問題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與農民打交道了,在拆遷、修路、建醫院之前,多次召開聽證會,聽取村民代表的意見,并認真對待這些意見。而農民代表在這樣的場合往往不知所措,不習慣與政府進行理性的討價還價,難以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事實袁明,政府越替農民考慮得多一些,直接沖突就少一些、不穩定因素就少一些。
在本案中,精英的力量是理性參與的。如果在全國的農民征地維權案中,多一些精英的介入(真正親身參與,而不是站在一旁批評議論),案子的解決會更容易些。說服農民走理性維權之路,并不容易。就像龍泉農民能贏得國務院一紙裁決具有偶然性一樣,要成為像張麗峰這樣的理性維權農民,也不容易,
張麗峰的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農民維權的官司難打,主要是錢不好湊。農民為打官司,要付出巨大代價,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們未找到合適的道路而瞎摸亂撞所付的代價。沉重的代價是否值得'精英們應否為他們參謀一條合理、簡捷、便宜的道路?本案律師張星水也說,農民維權隸的官司不好代理,如果不是出于公益心,他不會接這個案子。農民花了巨大的代價瞎打瞎撞,地方政府往往要花同樣的、甚至更大的代價去“維穩”。這種兩敗俱傷的、導致社會空轉的結局對誰有好處?
當今形勢下,在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錯綜復雜的時期,把紛爭直接化、簡單化為對抗性矛盾是愚蠢的,應該提倡協商、妥協、談判,而不要把有關利益方拖進“戰爭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