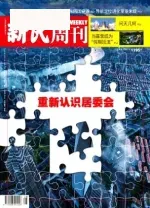“香港之子”陳志云
林奕華
表面上對一個人不感興趣所以不覺得要去認識他,其實,更有可能是不想認識自己,才相信似曾相識的人是完全陌路。
走進“文化、社會、藝術”課的教室,我問同學們:“大家對上星期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陳志云事件有什么想法?”面前約有三十人,看上去的確也是三十張臉孔,但感覺卻是“如墮死海”:一片死寂。我再鼓勵性地多問一次,終于有聲音從角落響起:“我沒有關注他的新聞。”“為什么?”“沒有時間。”我只好再把網撒回大海:“這里都沒有人對他有絲毫興趣嗎?”不搖頭也不吭聲的大多數中冒出一個少數分子:“我覺得他的人很假。”
很假,所以對陳志云沒有“興趣”。聽起來一錘定音的這位(女)同學好像是去市場購物,拈起一尾魚放下來:“不新鮮”,把一件外套拿上手又沒有買:“太貴了”。──能夠馬上作出判斷,得出結果,因為“主觀”幫她決定一切。說“陳志云很假”,所以“對他沒興趣”,然后不用細想、反思、認識,甚至解構“他”作為過去十多天全港所有報章雜志頭條人物──也就是被媒體集體利用來賣錢、套現──的意義,難道真可以被這樣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完全打發?
很假──是只有陳志云“很假”嗎?我看著眼前的這位女生,促狹地反問她:“你覺得自己‘假嗎?”斬釘截鐵地:“不!”“那你為什么每天都化了妝才來上課?”這一次可能因為問題中的主角不是別人,她倒是用了幾秒來轉動腦筋:“不化妝就沒有精神。”聽了,我再反問她:“你接受自己因為某些需要而不是拿出最自然一面見人,故此不認同別人說你是‘假。偏偏你又在仍未了解別人有哪些需要前,便認定‘他‘化妝便是‘假?同時否定了‘他和你之間可能潛藏著千絲萬縷的共同點?”
上述便是典型香港式的觀點與角度:表面上對一個人不感興趣所以不覺得要去認識他,其實,更有可能是不想認識自己,才相信似曾相識的人是完全陌路。都怪落難在香港人面前的陳志云已今非昔比,此刻人人要與之劃清界線,卻不代表他曾經不被很多人羨慕——連陳先生都曾有此慨嘆:“出生、念書、求職、轉工,由名校到最高學府,政府高官到大機構行政主管,一路走來都沒有怎么經歷挫折”(大意)——青云路便是志云路,可見他是多少香港家長心目中的“男兒典范”,堪稱“香港之子”。
然后,不知是無心插柳還是基于兩位都姓陳而惺惺相惜,“香港之子”在他的個人記者會上引述了“臺灣之子”的一句名言幫自己解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一夜之間全城瘋狂投入移橙換櫈的文字游戲:“六嬸七不了,七嬸六不了”、“彎的直不了,直的彎不了”之類不勝枚舉。社會上有此反響,證明陳志云仍然標志成功人士應有效應:引發大眾效法的個人魅(魔)力。有趣的是,此陳理當明白引述彼陳的名言將給自己帶來“詭辯”而不是“清白”的聯想,但他竟然不以為忤——光是這一點便已值得談論不知多少個茶余飯后,但是我面前這位修讀“文化、藝術、社會”科目的學生卻告訴我,陳志云對她來說并無研究價值,因為他“假”。
猶如她真不知道構成一個社會的“和諧”,“(虛)假”是很被需要重視的學問之一——包括窮一個人的心思與精力躋身進入名叫大學的窄門把它無微不至地活到老,學到老。以香港的主流學府為例,更多時候是為了幫助學生適應社會而設立名目繁多的“化妝”活動,例如廣邀名人分享穿衣、禮儀、談吐等等的心得。疑涉貪案的陳先生,在他那令全港嘩然的個人記招舉行過后不到二十四小時,已人在香港大學,留下一張有數十師生在他背后、身旁,豎起大拇指的“相挺”大合照。與其說陳志云備受尊崇是因為對社會有過多少貢獻,不如說“貢獻”就是,他令人相信一帆風順不是夢,是真實。
因此,我有理由懷疑那位說對“陳志云不感興趣”的同學不是看透了社會的“虛偽”,卻是“一帆風順”給她制造了太多的壓力和焦慮,讓她一聽陳志云三字便變成了不認耶穌的使徒彼得,是為了逃避不想面對的自己的“自我否認”。《穿Prada的惡魔》早已把個中道理說得很清楚:“你覺得這些東西都與你無關?打個比方,你從衣柜選了這件臃腫的毛衣,你以為只是想告訴全世界你關心的不是身上穿的是什么?但想想真可笑……你居然覺得它讓你與時裝業劃清界線,但實際上呢,它正是由這間房里的人(時裝雜志編輯,包括你在內)替你挑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