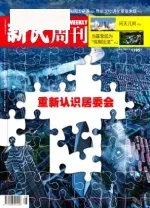“國進民退”與“讓步心態”
丁學良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依靠的是一種特權,而不是它應有、并且有憲法保證的權利。政府可以給你一個特權,也可以拿回來。
大陸正在發生“國進民退”現象,有必要把這個話題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中來解讀一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1年的歷史中,“國進民退”不是第一次發生,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遠一點,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國進民退”也不是中國才有的現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對所有制問題進行過好幾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核心是,1949年之后,執政黨要不要繼續保持40年代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承諾。那個承諾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與民爭利”。也即除了極少數的產業由國家控制之外,其他絕大部分產業的利潤,應該留給民間,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概念。1949年之后,中共很多高級干部認為,有必要保持這個承諾,以便使中國的經濟得到比較平衡的發展,最終能夠藏富于民。
可惜的是,這個政策最后被一步步拋棄掉了,由此形成的計劃和國有經濟體制,直到1979年才發生轉向。去年中國剛剛慶祝了改革開放30周年,須知,31年之前,人們討論的問題就是“國進民退”的問題。1979年,人們覺得,當年的“國進民退”太激烈,措施太強制性,造成的傷害太大,然后才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次“國退民進”,也就是讓民營企業一步步地恢復,給它們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空間。
還沒有人把這兩年的“國進民退”等同于50年代的“國進民退”,但我們要警惕這種狀況。在中國有一種思維認為,給民營企業更多的空間是一種讓步政策,是臨時性的,是照顧性。權力把市場看作自己的禁臠,民間沒有權利插手,只有在中國形勢艱難,經濟不好的時候,才允許民營企業存在發展。一旦形勢好轉,政府手里的錢多了,官員手里的錢多了,原先讓三步的,變成讓兩步,甚至只讓一步了。
這種心態很危險,可是在中國老是出頭,因為它的歷史太久遠了。有人說: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只有那些有政治權力的人,才有發大財、發橫財的機會。看到中國的官僚就能夠明白這一點。財富積累的源泉不是商業上的交換所得,而是來自對老百姓的剝奪,以及老百姓為了買通官府而支付的賄賂。因為官府擁有隨意予奪的權利。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間,物質上的、個人的創造發明,新型的收入和事業,經常處于一種不保險的狀態,隨時可能遭到統治階級及其官僚們的任意處置。統治階級及其官僚要么攫取和壟斷發財的機會,使私有經濟的資本形成斷了來源,要么用傳統的觀念組織經濟創新,唯恐創新會擾亂社會的安定。因為缺乏政治上和程序上的可預測性,中國傳統政治中,政府權力的專斷是非常顯眼的。朝廷和地方官員朝令夕改,好惡無常。在這種體制下,個別的人也可能發財,只要他精明地審時度勢,利用特殊關系。特權一旦到手,就有無限的機會。但顯而易見,這種環境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很難發展起來和正常運作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企業必須為著大眾市場的需要而組織勞工進行生產和銷售,必須依靠對事態的預測,必須能夠指望法制持續和客觀公正,必須指望政府合理的和可以預料地運作。
這段話是馬克斯·韋伯在整整一個世紀以前說的。這幾年我們老是在討論,政府給民營經濟的邊界劃在那里,是收還是放,這是很難預測的一件事。因為有這種不可預測性,導致中國企業家的短期行為。人們常常從道德上譴責中國的企業家只知道拉關系、坑蒙拐騙,不愿意從事創新和持續地創造財富,其實這種行為方式有比道德更深的制度性原因。換一種體制環境,中國的企業家完全可以轉向創新和持續創造財富的企業家精神。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依靠的是一種特權,而不是它應有、并且有憲法保證的權利。政府可以給你一個特權,也可以拿回來。在幾千年來的官僚政治傳統和61年來的“讓步心態”的影響下,政府掌握著予取予奪的權利,可以自由決定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這就是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