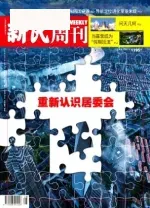五糧液之爭的背后
陳冰

五糧液古窖案會成為一個標志性案件,在民法理論和行政法理論上也會成為一個充分展示的活的案例。仔細解剖下去,就會知道在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公有化歷程中,民權是如何被逐步蠶食的。
北京,40度,烈日當頭,她在前往正義網的路上。
上海,37.4度,雷雨大作,他在去往法院的途中。
她叫尹孝功,一位身體瘦弱、年已古稀的四川老太;他叫陳有西,一位精力旺盛、神采奕奕的大律師。他們的生活本無交集,但是眼下,他們被緊緊地拴在了一起——為了16口明代酒窖的所有權,更為平民百姓的私有產權保護。
奔走、呼號、吶喊,他們深知這是一場大象與螞蟻的較量——一方是財大氣粗的上市公司,一方是年入兩三萬的工薪之家;一方是義正詞嚴、手握公權力的政府,一方是人微言輕、無依無靠的小老百姓。已有人“善意”地暗示,干脆將此“國寶”獻給國家,彰顯尹家一貫的為國家做貢獻的優良傳統。
但是——她說,“在官司打完之前,我不能生病”,“哪怕是賣掉房子我也要將官司進行到底”。
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一級律師陳有西認為:“五糧液古窖案除了在公理和公義之爭上會成為一個標志性案件,在民法理論和行政法理論上也會成為一個充分展示的活的案例。仔細解剖下去,就會知道在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公有化歷程中,民權是如何被逐步蠶食的。”
厘清被混淆的概念
記者:“租賃”、“經租”、“征用”、“征收”這四個法律術語在五糧液一案中反復出現,并且糾合在一起。我們需要梳理一下。
陳有西:經租,在民法理論上是不會喪失所有權的。是委托國家租給他人使用,同時收回一部分租金。“經租”怎么會變成“征用”、“征收”,不還,喪失所有權,自己租出去的東西怎么會成為別人的,國家的?這體現了我們國家沒有法制的年代,對民權的一種漠視和肆意剝奪。
這種不講理的剝奪,也被合法化了。最高法院按照國家當年有關部委的精神,出了剝奪繼承權的解釋。也就是說,租出去的東西,所有權到你死了為止,下一代沒有份,歸國家所有。
在那個“一大二公”沒有法制的年代,以租代征,以租代沒收,被最高法院以答復解釋的方式“合法”化了。雖然最高法院現在廢止了這個違反基本法律常識的解釋,但是,40多年這樣“租”走的物產太多了,對歷史老賬已經無法再翻,否則法院忙不過來了。因此,廢止司法解釋以后,“租變成征”已經不再允許,歷史上已經“租”走的已經沒有辦法了。
這對尹家是個陷阱。如果強調“經租”變“征用”的違法性,要推翻最高法院這個解釋,無異于雞蛋碰石頭。被告們會以“歷史政策如此,法不責眾”而讓尹家輸了官司。但是本案中,我們已經充分注意了這個問題。我們不會同最高法院的解釋去搏斗,挑戰其效力,同既成事實去搏斗。我們只是從事實上證明,尹家酒窖根本沒有進行國家“經租”。
如果真有“經租”,宜賓地方政府就撈到了稻草。他們請的一些“法律專家”“集體研究”后搬出這一條,目的就在這里。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最高法院早已經廢止該解釋,相對于現在的行政行為,已經無效。他們更不知道,這一條根本不適用于尹家的酒窖。
因為酒窖從來沒有“經租”給國家過。而是直接租給了國營二十四廠,這是企業同個人的關系,沒有到國家那里“經”過。從來沒有辦過“經租”手續,沒有任何證據。而且酒窖不是房產,當時政策可以列入“經租”的只是房產,不是土地和酒窖。酒窖的租賃關系沒有到國家手中經手。一直是尹家個人直接和二十四廠企業之間的民間租用行為。
另外,沒有公開的還有一個更令人驚愕的內幕:酒窖上方的尹家租出去的房產,是如何喪失所有權的,如何成了五糧液公司名下的。如果公開會更令人發指。尹孝功早就打過“舊宅保衛戰”,不讓他們拆掉從小長大的故宅,不同意、不承認這個尹家租給國家的房產,國家不“賣”回給他們尹家,而強行“代賣”給五糧液公司。但是她斗不過強大的公權。這是尹家的早年的一場保衛戰,他們要向國家買回被租走的房子,地方政府不同意,讓五糧液硬拆了老宅。尹家根本沒有同意。一千多平方米房產就是這樣從尹家手中被奪走了。這個官司現在還沒有打。就這樣,尹家失去了酒窖上空的房產,只留下了18.17平方米。多少不平事,是假公權名義以行。現在地方政府想故伎重演,想進一步拿走酒窖。
記者:我們知道國家相關法律早就確定了對私有財產保護的原則。但私產的保護還是舉步維艱,唐福珍式的悲劇一再上演。在和公權力的博弈中,弱小的百姓總是敗下陣來。
陳有西:50年代初,我們開始消滅私產搞集體化,農村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把土地和生產資料“自愿”收歸集體,后來就搞人民公社、立法規定土地公有,“退社不自由”了,農民失去了土改得到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城里則進行“一化三改造”,“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搞社會主義工業化。除了生活資料,無論城鄉,土地房產生產資料大多數收歸國有和集體所有了。這種國家征收行為,幾乎是無償的。國家免費獲得了公民的土地和私有財產。
后來“文革”、割資本主義尾巴、打擊投機倒把,國家用打擊犯罪的手段,專政的手段,將公民的私產幾乎全部收歸國有和集體所有了。憲法規定了“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文革”后落實政策,發還查抄財產,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就這樣“公有”了。
但是,尹家的房地產、酒窖不同。每一個政治運動中,尹家的房產和酒窖一直沒有被征收和剝奪。因此才會到2009年底一直享有出租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他們的權利一直延續到了中國依法治國時代,有了民法、有了物權法的時代。這樣,他們的財產權已經不能用當年的政策治國的方式來解決,只能依現有的民法和物權法來解決了。但是宜賓政府和五糧液公司的觀念,還停留在依政策治國的時代。
記者: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尹家證明16口酒窖是自己的證據是否充分?
陳有西:非常扎實充分。“一化三改造”從來沒有剝奪過他們的權利,當地政府也是一直承認的。尹家還有歷次處理租賃問題的宜賓領導的證言;是一種很特殊的一直擁有私產的權利。
尹家在中國沒有實施土地證制度時,一直擁有無可爭議的地權,因為酒窖就挖在地上,有600年了。后來我國開始實行土地可以發證,政府違法刁難不給他發,用左的政治運動的觀念限制尹家的正當要求。但是仍然一直承認他的地權和租賃權。
一直到了改革開放時代,這時我國已經建設了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但為了擴大五糧液的生產經營規模,地方政府把房產通過行政權強行“以租代征”后又違法轉賣給五糧液公司,這是典型的“民產國有化”、“用政府手段進行企業行為”違法事件,導致房權和地權割裂。但是政府對600年酒窖的權利一直沒有沒收和購買過。
激醒“睡美人”
記者:我對尹家能否取得法院公正的審判心存疑慮。你們直接選擇到四川省高級法院提出起訴,是否也有這個考慮?
陳有西:我們還是要相信法律,相信法院。一個正常的社會,沒有其他的路。當然小環境也要靠律師智慧去創造。我們在起訴時發了一個致四川省高院立案庭的函。在函上我寫明了:“我們清楚,兩案都不是非由高院審理不可,貴院可能往下交。如果一定要由中院一審,也請將本案指定到宜賓市以外的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在這份函中,我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五糧液公司系宜賓市舉足輕重的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占有當地財政收入相當大比例,其股份公司董事長和集團總裁是原宜賓市的副市長。市國資占有五糧液56.07%的股份。在宜賓司法機關中有很大影響力。對于以市政府和五糧液公司為被告的案件,當地司法機關以回避為宜,以保障兩案能夠客觀超脫地審理。
另外,尹家的五糧液600年16口明代古窖的所有權之爭,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糾結在一起,屬于有全國性影響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涉及建國60多年的政策、法律界線,影響到五糧液股份公司的核心無形資產的真假,涉及尹氏家族600多年的歷史私有財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涉及尹家的祖先歷史和長遠利益。它將體現我國物權法實施后公私財產的司法保護狀況,應當由省高級法院一審管轄審理。
記者:你講到了《物權法》的實施,看上去似乎并不樂觀。
陳有西:我給你講個荷蘭的例子。
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簽署后的25年中,它只是個“睡美人”,在歐洲無聲無息。荷蘭法官不了解,議會也不當回事,認為荷蘭國內法同人權公約沒有沖突。但20世紀70年代,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
公民人權意識提高了;荷蘭一些大學的博士生開始寫論文研究歐洲人權公約,律師從中發現了很多有用的東西。特別從刑事訴訟的程序上,先發現了荷蘭法院判決中的不合歐洲人權公約的問題。
律師向歐洲人權法院的起訴案,判決荷蘭國家法院不符合人權公約而推翻判決的案例接連發生,這就引起了法官的注意,開始研究本國判決的問題。法官學習歐洲人權公約成了必修課,也引起了議會的注意,審視自己的國內立法是否需要重新對照修改。現在大學法學院把人權課作為必修課進行教育。作為司法部,在國家當被告時,要去應訴。在本國判決被推翻時,要在國內貫徹人權法院的判決:一要對本案進行糾正和國家賠償;二是要對法律規范進行修改。
由此可見,在喚醒法律這個“睡美人”的過程中,律師和學者起了很大的作用。眼下,我認為,尹家的官司就是一劑喚醒《物權法》“睡美人”的強心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