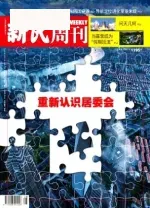建國大業美國版
王曉漁
一提到美國的建國大業,我們總是想起萊克星頓清脆的槍聲。但是美國之特色,不在于“槍桿子里出政權”,而是“筆桿子里出政權”(或者說“嘴皮子里出政權”)。1775年,萊克星頓打響獨立戰爭第一槍;1776年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通過《獨立宣言》,成為開國十三州;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八年抗戰”宣告結束。
戰爭結束,海晏河清的景象卻沒有立即出現。《獨立宣言》宣告十三州獨立于英國之外,但十三州各自為政,還是緊密團結在中央政權周圍,成為新的問題。《邦聯條例》決定設立邦聯國會,可是邦聯國會的權力遭到重重限制,沒有軍隊,不能征稅,十三州保持相對獨立。
獨立自主的美國,一度比在大不列顛統治之下還要混亂。1787年,在通過《獨立宣言》的舊址召開了制憲會議,最初準備修訂《邦聯條例》,后來發現僅僅修訂《邦聯條例》已經是杯水車薪,開始起草憲法。一邊擴大中央政府的權力,一邊以三權分立避免過度的中央集權,構建一個聯邦制、總統制的共和國。1789年,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也就是說,美國宣告獨立之后長達十三年的時間里,沒有總統。
沒有1787年的制憲會議,就沒有美利堅合眾國的大國崛起。如今看來,制憲會議是勝利的大會,奠定了美利堅合眾國長治久安的基石,但當時看去,制憲會議絕不是團結的大會,圍繞建國大業中的種種棘手問題,代表們從5月爭論到9月。在《如彗星劃過夜空》和《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里,林達和易中天向中國讀者普及了制憲會議的過程。
如果說制憲會議是“嘴皮子里出政權”,制憲會議之后報紙上對聯邦制的激烈爭論,則可以稱作“筆桿子里出政權”。制憲會議發起人之一的麥迪遜在百忙之中記下會議過程,結集為《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在報紙上力挺聯邦制的文章,結集為《聯邦論》(又名《聯邦黨人文集》)——尹宣先生先后翻譯了這兩本書,前者2003年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先后被林達和易中天在寫作時參考,后者剛剛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借用我們熟悉的框架,《聯邦論》主要討論美國應該統一還是分裂,但是統一/分裂的框架不足以描述雙方的分歧。如果認為聯邦論者堅持統一、反對分裂,反聯邦論者堅持分裂、反對統一,就把雙方的觀點極端化、簡單化了。聯邦論者主張建立一個擁有一定權力的聯邦政府,反聯邦論者更為強調各州的獨立性,但是前者并不否認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后者也不否認需要存在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專制國家。經常放大無政府狀態下的混亂,為自己的暴力統治尋求合法性,這種宣傳特別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同,“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反聯邦論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他們對于一個無所不能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政府會以行善為南謀求最大權力,一旦獲得不加限制的權力,作惡的可能性遠遠超出行善。反聯邦論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并不反對政府的存在,只是對無所不能的政府表示恐懼。在一個穩定得幾乎停滯的國家,公民可能像動物一樣,只有生存權,沒有其他公民權,暴力維護的太平盛世,不見得比亂世更好。所以,聯邦論者不僅要正面論述建立聯邦政府的必要性,還要向對方辯友說明聯邦政府如何與中央集權劃清界限。雙方擁有一定的共識,既要避免一個獨裁君主式的中央政府,又要避免一盤散沙式的無政府狀態。
聯邦論者和反聯邦論者不是在“太平犬”和“亂世人”里二選一,不是以“亂世人”的命運恐嚇公眾安于“太平犬”的生活。雖然他們的具體觀點存在巨大分歧,但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建立一種制度,這種制度不僅可以保障國家富強,更重要的是,它保障公民權利不被國家以公共利益為名隨意侵犯。
英美政治體制常被并稱為“英美模式”,可是從《聯邦論》來看,美國的建國大業不是一邊山寨、一邊排外,而是堅持本國國情和學習他國模式并存。雖然英美剛剛交戰,但以此為由徹底否定英國憲政的觀點,幾乎看不到。歷史也足以說明,如果因此否定憲政,那不是跟敵國過不去,而是跟自己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