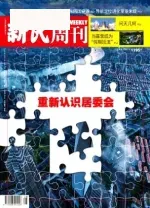科幻的世界地圖
宋明煒
《星球大戰》是流行的科幻,但同時也是最保守的科幻——一切都納入自我復制的話語之中。
1948年,美國雜志《神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的主編坎貝爾有感于主流文學界對“科幻”的歧視,發表驚人之語:科幻不是主流文學的分支,而應該反過來,主流文學才是科幻的分支,因為科幻處理的是一切時間與空間中的事件。這聳人聽聞的說法,隱含著科幻的真正生機——它本來就包羅萬象,氣吞一切,要跨越所有的界限,包括自我構筑的邊界。科幻是從古老的怪誕、冒險故事發展出來的寫作類型,到此時第一次誕生了自我意識,把整個世界當作自身的鏡像。
科幻的經典敘述(以凡爾納、威爾斯為代表),其實早在不自覺中打開了一張可以無限生長的神奇的世界地圖。這地圖上繪滿帝國擴張的足跡——從地理版圖的延展,到想象時空的無限開放。對后殖民理論家來說,經典科幻是帝國的寫作方式;就像凡爾納小說里,上天入地的主人公背后有著法國殖民者的身影,而威爾斯式的星際大戰觸動的是帝國子民的神經。20世紀后半期家喻戶曉的美國科幻故事“星球大戰”(Star Wars)與“星際迷航”(Star Trek),把所有帝國式的文化邏輯都一鍋燴了:宏大歷史,正義倫理,擴土開疆的冒險精神,堅不可摧的身體,以及微妙之中對異類的恐懼、同情——乃至歸化。這兩部作品稍有不同,但前者體現里根時代的美國神話,顯然更加引人入勝,生命力經久不衰。如此現代帝國的想象愈演愈烈,直到最近的《阿凡達》,其實仍在重復這一經典敘述。
有趣的是,這個世界之所以令人著迷,原本在于它看起來危機重重,充滿異類。未被標記的海面上或許存在魔獸島,飛出太陽系的歷險可能帶來危險的異種,探索引向自身時則暴露出我們的陌生面孔。科幻的世界地圖,無論在物理還是精神的意義上,永遠是描繪“異地”“異形”的所在。或者說,這個地圖展示的,不是已知世界的圖景,而是延伸向未知的路徑。
當坎貝爾宣布科幻是一切文學的總體時,這個想象的定義不僅面向已知,而且包括了一切面向未知的寫作。盡管在邏輯上,或許所有的未知可能僅僅是已知的變形,所有未來都是過去的倒影,但最關鍵——也是最神奇的,是與之遭遇時的姿態。帝國的視野中,未知是被征服的疆域,如凡爾納筆下的鸚鵡螺號潛水艇,或《星際奇航》里的企業號航天飛船,把未知的經驗帶入地圖之中,其實已經將其化為知識,轉換成日常的景觀。比如,你有沒有感到《阿凡達》里的一切神奇都似曾相識呢?
但面對未知,還有另一種姿態。
克拉克的《與拉瑪有約》代表我心目中最精彩的科幻想象。這部小說寫的是在22世紀有一個未知天體飛進太陽系,宇航員發現其為人造物體,而且可以進入其中。克拉克的敘述充滿技術細節,帶有繪圖員的精準細膩。這個被命名為拉瑪的物體內部是一個空洞,里面有完整的世界,甚至如紐約城一般的高大建筑,卻沒有生命的痕跡。拉瑪“人”不知道在多少時間以前,已經在跨越星系的航行中湮滅了,或者他們的存在根本無法為地球人觀測到。地球派出的宇航員,只能短暫地對拉瑪進行勘查,而拉瑪平靜地承受了勘查,沒有任何波瀾。人類看著它掠過行星的軌道,飛向太陽,再繼續飛出太陽系,消失在大麥哲倫星系的方向。
最給人以啟發的科幻,是在充分描繪“世界”地圖的同時,展現出未知的無限魅力。它承認“差異”有無法被歸化的層面,而“認同”的政治在面向宇宙(或者比宇宙尺度小得多的意象)時,需保留對“異地”“異形”的敬畏。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地圖不是星球大戰上演的舞臺,而是反觀自身的鏡像。《星球大戰》是流行的科幻,但同時也是最保守的科幻——一切都納入自我復制的話語之中。與之相比,克拉克的《與拉瑪有約》描寫了一次真正的與世界相遇的過程。
正如當代優秀的科幻小說家劉慈欣,在讀完克拉克的小說后,“出門仰望夜空,突然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腳下的大地變成了無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純幾何平面,在這無限廣闊的二維平面上,在壯麗的星空下,就站著我一個人,孤獨地面對著這人類頭腦無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從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個樣子了,那感覺像離開了池塘看到了大海。”
與世界的相遇,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