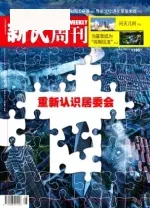葉小綱:十年磨劍為《詠.別》
何映宇



如果是十年前我寫這部戲,不會是現在這樣。
歌詠言,詩言志。
《詠·別》,既是歌劇,又是一首詠嘆愛情的哀婉詩篇。
一種超越了性別的大愛,在音符交織中綻放出別樣的光彩。那是有關愛欲、尊嚴、幻滅與犧牲的故事,又仿佛是東西方跨越時空的對話,京劇與歌劇,恰似火星撞地球般的碰撞中,剎那絢爛,霸王和虞姬,獲得了新生。
出生于上海的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葉小綱的第一部歌劇《詠·別》10月17日亮相上海大劇院。雖有電影《霸王別姬》和《蝴蝶君》在前,但講述同性之戀的歌劇,在世界歌劇史上恐怕還是首例。是什么讓葉小綱義無反顧地寫下《詠·別》,開風氣之先?
10月12日,星期二,下午3點,記者來到上海歌劇院的排練廳,一身黑衣的葉小綱靜靜坐著,看上去早已胸有成竹,他說:“到了我的歌劇時間。”
葉小綱與譚盾、瞿小松、郭文景并稱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四大才子”,這是個怎樣的音樂家呢?很平易,總是微笑著,但說話的字里行間,卻并不總是好好先生。該說什么,該批評什么,他并不避諱。“可以公開說,沒什么。”他斬釘截鐵地說。
他相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養成了愛音樂,也愛讀書和思考的習慣,他每天聽40分鐘音樂,讀一個多小時書籍(卻很少看音樂書),兩天查一下卓越網,雷打不動,坊間紅火的書,門兒清。這讓他永遠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反思自己,也反思中國音樂存在的諸多問題。
這樣一個愛思考的葉小綱為自己的努力贏得了掌聲與鮮花,他的現代音樂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譽。這么多年來,他寫過交響樂《長城》、《大地之歌》、《最后的樂園》,大型舞劇《紅雪》、《深圳故事》,室內樂《九亂》和《林泉》,為電影《人約黃昏》和《半生緣》配樂,但歌劇他還是第一次。他說:“盡管這是我的第一部歌劇,但是我等待了很久,也準備了很久。三四年前北京國際音樂節就開始醞釀這部歌劇,最后余隆給了我這個委約,北京國際音樂節在發展中國音樂文化方面是很有創意的。我不想寫什么現代歌劇,對指定題材或者先鋒派歌劇也沒什么興趣。我一直在等待這樣一部歌劇來圓我的歌劇夢,自《詠·別》之后,我才開始我的歌劇起航之旅。”
看得出來,這是一部沉淀了葉小綱多年心血的作品,好像他也頗為看重這次創作。他似乎在一直等待,等待著《詠·別》的劇本放在他的桌案前,等待著一支筆在這樣的劇本上寫下音符。如今,終于將音樂寫就之后,葉小綱的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他知道,這不是他和歌劇的“永別”,只是一個開始,也許,也是中國歌劇的新起點。
電影配樂是為歌劇做準備
《新民周刊》:我聽說您在寫本書,叫《苦海無邊》,寫完了沒有?
葉小綱:那本書我還在寫。我寫我們家的家史,從我姑媽開始寫。我姑媽是葉璐茜,趙丹的第一任夫人,當年和藍蘋在六和塔結婚的六個人之一。我們的家族事情比較多。我父親又是音樂家,后來又參加革命,如實寫下來,還需要等等吧。
《新民周刊》:您是音樂世家,您父親葉純之是不是對您后來成為作曲家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葉小綱:我父親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音樂世家給我的教育比較全面,背后的文化支撐點也比較多,我能夠投身于音樂事業當然與我的家庭是密不可分的。
我從小就愛看書、聽音樂、看戲,我父親是個很有素養、精神追求很高的人,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這個人看上去較軟弱,但內心還算堅強,沒有倒下來。“文革”中,我父親受到迫害,中學畢業后我被下放農場,后來在工廠里當了6年鉗工,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放棄音樂。沒有放棄的結果就是恢復高考我馬上就考取了中央音樂學院,又出去留學,在國外覺得應該回到國內的時候就回來了。回國之后,一直在打拼吧,可以說遍體鱗傷,呵呵。要不是有毅力,真堅持不下來。
《新民周刊》:進了中央音樂學院之后,您得了作曲系“四大才子”的頭銜,這個頭銜是怎么得來的?
葉小綱:當時大概是我們幾個比較紅吧,結果成了一種說法。這是歷史的機緣。前面是十年動亂,沒有出人,我們的思想和作品都比較新銳,手法上不見得比現在的年輕人好,現在的年輕人機會比我們多。但我們還在那兒呆著,好像也沒有什么后來人上來。
《新民周刊》:您創作了大量的交響樂作品,其中的《長城》是不是您和上海歌劇院院長張國勇先生的第一次合作?
葉小綱:是我們的第一次合作。當時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但我覺得他是特別耿直的一個人,拿藝術當生命。所以我對他這次指揮《詠·別》很放心。張國勇也一直覺得要再指揮一次,他覺得指揮一次不過癮,終于有了《詠·別》這樣的作品可以讓他過過癮。
當時請我寫《長城》的部門希望我寫個主旋律,像《黃河》那樣的作品。我想,《黃河》有抗戰的背景,那《長城》怎么寫?我依據自己的感悟,想到了文化長城:從嘉峪關一直寫到山海關。用音樂來表現長城的蜿蜒萬里:甘肅是甘肅風韻,陜西有秦腔調,然后山西晉味,再是河北蒼茫,到了秦皇島是冀北的民歌素材,我寫了個文化長城。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審查的時候,他們很失望,說:怎么不是《黃河》那樣呢?他們又聽了北京的幾位“專家”意見,結果就沒去北京“晉京演出”。當地官員和北京“專家”都拿這個作品當政績工程,想要有當時那幾首很紅的歌曲的政治效果。我沒有聽他們的意見,堅持了自己的藝術見解。今天那些官員都已不知去向,而我的《長城》卻成了個人氣質鮮明的藝術作品,已被世界著名的音樂出版機構拿去推廣和出版,進入世界文化市場,我的藝術判斷還是對的。以前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我看現在,嚴重的問題不光在于“教育干部”,也包括要“教育專家”。有時“專家”更壞事。主管官員不懂藝術規律沒問題,人家不是干這行的,只要負責把握方向或掌控全局,我特別理解;但那些就知道拍馬屁的“專家”,往往壞了我們中國太多的事,千萬不能信。
我還希望和張國勇在北京現代音樂節上再合作一次,比如再搞一個歌劇。有個題材講人的本質,把人性看得很透,很有意思。另外一個很想做的是《牡丹亭》,陰間與陽間的對話很吸引我。如果做《牡丹亭》,我就直接用湯顯祖的原本,那樣誰也揪不出劇本的毛病。當代劇本,常有各種部門橫挑鼻子豎挑眼,但湯顯祖的劇本誰敢說它有問題?誰都沒那么傻,那可是老祖宗的經典,是“文化遺產”,“申遺”都來不及呢,說它有問題就是自己“沒文化”了。
《新民周刊》:您也是中國電影音樂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為多部著名的影視劇寫了音樂,比如陳逸飛的《人約黃昏》。當時陳逸飛是怎么找您來為《人約黃昏》配樂的呢?
葉小綱:影視音樂方面我是寫了很多,大概有30多部吧,還得過中國兩個最重要的電影音樂獎。黃蜀芹的《上海滄桑》、陳逸飛的《人約黃昏》、許鞍華的《半生緣》都是我寫的音樂,最近還把《玉觀音》的配樂重新整理出版了。《人約黃昏》很簡單,陳逸飛當時對我說:“小綱,你來呀。”我就去了。我認識他多年,是淡如水的君子交往。我去美國第一頓飯就是陳逸飛請的我,第二頓請我的是小提琴家徐惟聆。陳逸飛是藝術上比較淡定的人,沒像某些大牌導演那樣不懂還在裝懂。陳逸飛放手讓我作曲,一點干涉都沒有,這就給了我創作的空間,結果就成了。就像領導部門要是老干涉藝術家就出不了好作品一樣,導演對作曲家干涉過多也肯定不行,導演如果能代替作曲家創作電影音樂的話,那就不需要作曲家了。
《新民周刊》:《半生緣》呢?許鞍華會不會干涉你的創作?
葉小綱:《半生緣》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提名。許鞍華也不干涉我的音樂,所以里面有很現代的音樂,也有很傳統的音樂,都為電影服務。能做到這一點,可以這么說,是幾十年積累的結果。
為電影作曲的好處是什么?電影刻畫人,電影配樂同樣如此。沒有寫過電影配樂的作曲家寫歌劇,也許沒那么多配器經驗。我寫了30多部電影和電視劇的音樂,每一部戲都不一樣,沒有一個人物是相同的,沒有一個時代是相同的。電影里的故事,沒準是一百年前的事,沒準是一百年后的事,這讓自己獲得了經驗。我寫過廣西很窮的地方,也寫過陳逸飛這種小資情調的電影,這都是一個個感悟的過程。時間、人物、地域、環境甚至氣候都給我很多感慨,而電影音樂對人物內心的刻畫的經驗正是歌劇所需要的,可以說,我寫了那么多電影音樂、室內劇和交響樂,都為這部戲做了很好的準備。
《新民周刊》:您現在也是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王健之前接受采訪時對中國國內的音樂教育提出了比較尖銳的批評,比如,他認為現在國內的音樂學院學生只知道得獎,為了得獎拼命努力,放棄了音樂的根本,您是否同意他的觀點?
葉小綱:重視得獎是體制原因。我當年成名也是因為得獎。我現在認為得獎根本就不重要,王健就沒得過什么獎,但是他很棒。中國人得獎是敲門磚,因為文化起點相對比較低,得獎的至少說明你還不錯,很差的肯定得不了獎。現在中國整體音樂水平不高,所以得獎變得很重要。如果大家水平都很高,像王健一樣,誰還稀罕什么獎?
中國音樂教育當然問題不少,重要的是缺少人格培養和文化底蘊的熏陶。追求升學率、就業率,高品位文化缺失。我們說改革開放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前十五年是補課,是恢復,高等教育起到一個非常好的作用。等到后十五年,由于市場化大潮,慢慢低俗化、庸俗化,甚至惡俗化,這是管理不善造成的。我們文化工作者應該做什么?我一直堅信,如果思想上不領先,藝術不會成功。當然還要看機遇。如果這部歌劇不請我寫,就永遠不會有現在的“葉氏”旋律了,呵呵。
藝術至上
《新民周刊》:對于《詠·別》這部歌劇而言,同性戀是不可回避的話題,您用這樣一個題材來寫一部歌劇,是為同性戀正名,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葉小綱:同性戀是客觀存在,不用刻意回避。《詠·別》中的男主角是一個得不到同性之愛的劇作家唐麒聲,最后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我沒有嚴格查證,好像這是世界歌劇史上第一部明火執仗涉及同性戀的歌劇,將男男之愛像李安的《斷背山》那樣正面展現在歌劇舞臺上。但我處理的辦法是將劇中的愛超越性別,感情交織超越性別。社會現在對同性戀的看法和態度,還停留在“能不能合法婚姻啊,是不是傷風敗俗啊”等階段,較淺,沒能從高層面來看待這種現象。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人類的大愛。《詠·別》中的劇作家唐麒聲追求的,既是愛情,也是一種理想。歌劇真正要表現的,是一種高尚的情操,是一首孤獨靈魂的挽歌。如果劇本將唐麒聲寫成一名女性,也會是很有魅力的一男兩女“三角戀愛”故事。現在寫成兩男一女更多是因為聲樂魅力所致,你知道男高音永遠是歌劇舞臺的主角,全世界有那么多男高音前赴后繼地涌向歌劇舞臺,因為觀眾無法拒絕男高音在歌劇舞臺上的魅力,而霸王這個角色只能是個男中音,舞臺上實在是需要一個男高音。其實就是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三角戀愛,也是兩男一女的戲要好看,更有戲劇性。要是兩女一男,往往社會性要差些,“范兒”小了。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偉大女性,但男性的心胸是不是更寬廣些?要不然統治世界的怎么還是男性居多?哈哈。
現在這部戲沒有讓人覺得不舒服,完全是精神上的英雄相惜。這種精神大愛其實是人類永恒的追求,男主人公最后的死,就像中國古人的高潔之士為世俗所不容,猶如《詠·別》結語所唱的:“每當塵世將你遺忘,你在高處沉默不語。”所以主人公放棄生命,永別這個世界是必然的。有高尚理想的人往往與世俗格格不入,任何時代都差不多,盡管歌劇背景在20世紀20年代,但放在今天其實也如此。故事背后,往往是更多表現事件的歷史環境。
《新民周刊》:歌劇里的四個主角,都有所指,分別是追求物欲和感官欲、追求功利、追求道德、追求審美的四個不同層次人物,為什么這樣設置人物?
葉小綱:四個人物,有追求感官物質的,有追求審美的,每個人都不一樣。比如唐先生,他的那種寧折勿彎的精神,其實也是很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就像張伯駒先生。出身高貴,很有文化,又喜歡追求美,在審美中享受自己的人生。如果他不能在審美上達到他對美的追求,那他就放棄自己生命,他不是凡俗之人。普通人的生活邏輯是:“好死不如賴活”。當然,這種世界觀,也有深層次的內涵在里面。
劇本的文字之外,我更多的是用音樂來表現這四個人物。目前劇本的思想脈絡還比較模糊,但是我用不同的音樂,讓聽者感受這四個人物的差別:激烈的、沖突的、忐忑不安的、酸的、甜的,都在音樂中自然而然地呈現,彌補戲文上的不足。
《新民周刊》:對幾位主演還滿意嗎?
葉小綱:石倚潔(飾演唐麒聲)很突出。他現在居住在奧地利維也納,但卻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浦東張江人,我們這部歌劇最大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國男高音,這次他取得了很大突破和進步,不容易。不能說他外形條件有多好,但聲音真漂亮,演唱水平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抒情男高音中最高的。本來,北京的張英席,一米八五的個頭,又高又帥,明星一樣的帥,演這部戲的形象條件更合適,但是上帝就是這么公平,不把所有的好事都給一個人。要是我拍電影啊,就用張英席演,用石倚潔的聲音。就像以前京劇《海港》中,高志揚的表演和演唱用了兩個演員。
當時藝術總監余隆很發愁,不想用男演員來演,他認為中國的男高音太難找了,想用女中音來反串,就像《玫瑰騎士》那樣,女扮男裝,女性演這類角色,觀眾更容易接受。但是我和編劇堅持要用男演員,因為我們心里怎么都不認同女的在那兒演男的。
《新民周刊》:這是您的第一部歌劇,之后還準備寫第二、第三部歌劇嗎?
葉小綱:歌劇像毒藥一樣,瓦格納寫了歌劇之后就再也不寫別的了。我覺得我也快了。我覺得真正的藝術品還是要體現創造者的獨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真正能在歷史上留下來的經典作品,需要藝術至上。《紅樓夢》講不講政治?多少年前,中國那么多文化大家,梁啟超、章太炎、魯迅、周作人、李叔同、齊白石、張恨水、林語堂、朱自清、茅盾、巴金、郁達夫、陳寅恪、聞一多、張愛玲……他們都是有獨立人格的文化大家。如果說近幾十年來文化墮落,沒這么多大師,恐怕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思考一下原因吧。
接下來我有幾個計劃。有一部偏現代主義的歌劇,還有中國的古典題材。《尼伯龍根的指環》可以連演4個晚上,昆劇《牡丹亭》可以連演3個晚上,我都考慮過了,不愁沒有投資,我第一部歌劇出來以后,心里有點底。《詠·別》相對比較正,所以我想下一部戲我可以相對前衛一點。音樂、舞美、意識都可以超前一點,當然,也希望能與上海多多合作。
骨子里的民族性
《新民周刊》:您喜歡瓦格納的歌劇?
葉小綱:我非常喜歡。我是瓦格納迷。但我只聽,不看。馬克思主義有三大來源,我也有三個精神來源:中國古典音樂、德國古典音樂和美國當代音樂技術。瓦格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資源,主要是他的強者意識。但我沒有怎么受德國現代音樂的影響,德國當代樂派能耐心聽下去的不多。美國是一個比較講究傳統意義美感的國家,我也比較喜歡傳統意義美感的藝術作品。
《詠·別》這部戲中體現了很多中國古典美學的精神追求。品質高潔不容于社會,這還是很中國化的美學思想。我還在歌劇中加了一些世俗的眾生相,表現這個社會其實哪個時代都一樣。比如女教官唱“我當年怎么樣”,旁邊一個人就接著諷刺她:“你當年可不怎么樣。”還有最后,我借劇中人口說“死什么?好死不如賴活”。這種中國人的世俗一面,也是我加進去的,原來劇本里都沒有。我覺得還不過癮,如果有機會,我會把第四幕中的眾生相寫得更徹底,針針見血,像魯迅那樣來描繪中國人的人性。歌劇是個production的藝術,一部歌劇,不同的制作可以產生不同的版本。這一次,他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很不容易。
《新民周刊》:《尼伯龍根的指環》在上海演出時您去看了嗎?
葉小綱:我沒有看。我不怎么喜歡現代派版本的《指環》。瓦格納的作品,永遠是臺上不如臺下,他的音樂太牛逼了,音樂一出來,總覺得臺上體現不夠好,跟音樂不是一個級別,總有這樣的問題。不要迷信經典作品新制作,好的也是少數。
《新民周刊》:《詠·別》也是將京劇與西洋音樂相結合的一次嘗試,可是除了一些念白之外,我并沒有看到多少京劇演員的演唱,京劇在這里只是一個故事框架的需要嗎?
葉小綱:《詠·別》里的京劇元素很多,但是都變成西洋管弦樂了。這是靠積累,我從小聽樣板戲,傳統京劇也聽過不少,京劇音樂對我來說是種血液里的東西。
歌劇里許多旋律都來自京劇,熟悉京劇的聽眾一聽就會知道。我的前奏、過門全是京劇。歌劇演員方面,男的武生,化用的是京劇中的奚派(奚嘯伯),女的則是李慧芳的調子,但都不是很有名的唱腔。我不想用很有名的,因為太出名的話,一聽就知道從哪兒來的,也不好。除了一些念白是直接搬用京劇,其他的音樂部分,都沒有直接挪用京劇,否則那就不是歌劇了。
京劇演員不能在歌劇中直接演唱,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京劇演員的識譜習慣和西洋音樂的方式不一樣。他們和交響樂隊合作要克服很多問題。他們演出時不看指揮,只聽京胡和司鼓。這是兩種藝術形式不同的傳統和表現方式造成的問題,我把這個問題回避掉了。但我保留了部分念白,讓它和歌劇形成一種對話和緊張關系。比較長的念白出現在第四幕,京劇念白念一句,歌劇演員唱一句,在形式上很有革命性。
《新民周刊》:您之前創作過一部昆曲歌舞劇《貴妃東渡》,將昆曲與交響樂結合,寫這樣一部作品是否也為今天寫《詠·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葉小綱:所以這些之前的努力都幫了我的忙。京昆是一家,昆曲是京劇的祖宗,所以《詠·別》里也有昆曲的調調,比如《詠·別》男一號的主旋律就來自昆曲。這也是積累的結果,如果是十年前我寫這部戲,不會是現在這樣。
《新民周刊》:做這樣一部歌劇,是為了使其成為東西方對話的一種表現,還是說骨子里其實還是民族性的考慮更多?
葉小綱:我覺得骨子里還是民族性的,只是用了一種西方的模式。當時余隆對我說,西方觀眾會對中國的京劇感興趣,但是如果用中國京劇演員來唱歌劇,那就不是歌劇了,所以我們需要在其中找到一種平衡。我要求我的演員咬字比較靠前,比較像中國的民族歌劇,但是發聲方法都是美聲的,不用話筒而大劇院的最后一排,觀眾都能聽見。
中國的歌劇成功不容易,不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一是主創者的定位不準確,二是創作者的才能尚不足以駕馭一部歌劇,第三,合適的演員不多。一部歌劇要成功,這幾個方面,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出現大的問題,所以說創作一部歌劇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新民周刊》:那么對中國歌劇的現狀,您還是以不滿意居多?葉小綱:中國歌劇的現狀,首先還不夠繁榮是肯定的。歌劇畢竟是種外來的藝術模式,過去的五六十年里,中國歌劇一直在做各種各樣的嘗試,比如中國歌劇起步之初的《白毛女》、《江姐》、《洪湖赤衛隊》,它們沒有采用西方歌劇的模式,等于兩個系統在交戰。歌劇作為一種西方舶來品,你必須符合它的演出模式或創作規律。中國的民族歌劇做了很多嘗試。你說它們成功嗎?很成功,老百姓很喜歡。成功之處在于它的旋律和語言的結合特別好——中文寫歌劇是很難的。當然,中國的民族歌劇受意識形態影響很大,它是強勢推行的,但為今天我們寫《詠·別》這樣的歌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中國民族歌劇不是世界通用模式,無法走向世界,這種唱法西方人不會,就像西方人不會京劇一樣,因為你走了一條非西方的道路。
而《詠·別》可以走向世界,我們用的是通用模式,就像電腦里的二進制,你能用,我也能用。世界上任何一個女高音只要學中文發音,就能唱《詠·別》了。我們完全是用西方模式的歌劇,來講一個中國故事。這也是我做這個歌劇的初衷,中國文化,要用世界上大多數人能用的、看得懂、聽得懂的、弄得明白的系統來實現,這樣可以讓世界更多地更好地了解中國。
《新民周刊》:正因為歌劇在中國的時間非常短,大多數觀眾還沒有形成觀看歌劇的習慣,您覺得《詠·別》這部歌劇是否能得到普通觀眾的認可?
葉小綱:我沒有走實驗歌劇的路線,相信它的受眾面不會窄。
《新民周刊》:《詠·別》是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閉幕節目,您自己也是北京現代音樂節的創辦人,怎么創辦這個音樂節的?
葉小綱:我很感謝余隆給我這次機會,做中國原創的大歌劇,是他的理想。具體操作,需要極強的行政能力和管理魄力,我要向他學習。至于現代音樂節,原來的想法很樸素,就是覺得外國有中國也要有,我在維也納時看到有維也納現代音樂節,我就想,來個北京現代音樂節吧。一晃至今也已經8年了,在這個音樂節上,我們推出了許多新作品,但還沒有制作過歌劇,所以我想在北京現代音樂節上做一部。
《新民周刊》:選擇了在上海大劇院首演,您對上海的文化產業是否關注?對它們怎么評價?
葉小綱:上海曾經是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但是最近幾十年衰落了。但我認為,近年來上海并沒有出現什么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非常有影響的作品,上海的高端文化非常缺位。上海的資金很雄厚,卻做了一些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請外國人寫上海,讓人覺得是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