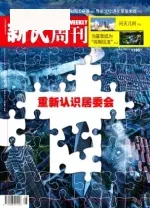中國歌劇的記憶宮殿
何映宇



中國歌劇有輝煌,有風雨,也有沉寂和停滯,從“有中國特色”歌劇為民眾的喜聞樂見,到歐美經典歌劇紛紛登陸中國,自閉與開放,革命與和諧,中國歌劇的變遷,也是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詠·別》吹響了中國歌劇前進的號角。倘若它成為中國歌劇的里程碑,它也一定是踏在先驅者的肩膀上。誠如葉小綱本人所言:“這些前人的努力,為《詠·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回首中國歌劇的發展歷程,自《白毛女》橫空出世以來,已經走過了65個春秋。其中,有輝煌,有風雨,也有沉寂和停滯,從“有中國特色”歌劇為民眾的喜聞樂見,到歐美經典歌劇紛紛登陸中國,自閉與開放,革命與和諧,中國歌劇的變遷,也是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槍斃黃世仁
在沉寂了32年之后,2009年年底重新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的歌劇《白毛女》是中國第一部民族“新歌劇”。時間退回到1944年5月。一天,延安大學校長兼延安大學魯迅文藝學院院長周揚收到了晉察冀邊區的林漫(本名李滿天)寫來的一封信。他展開一看,信中提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說河北阜平一帶的山洞里,有一個長滿白毛的仙姑,能除惡揚善。這本是一個民間傳說,多少有點荒誕不經,但是政治敏感的周揚馬上嗅到了其中的革命意味,一個大膽的計劃油然而生:不再是神神鬼鬼的傳奇,變身為一個“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新歌劇,是否可行?
說干就干。
第一稿由“西戰團”的編輯邵子南寫成。基本上用了舊戲的形式,唱腔是秦腔似的。試排時,周揚來看,看完之后,他并不滿意,他指示說:“要注重思想內容。另外,我們在藝術形式上,不要洋八股,但是我們也不能要封建八股。”
于是,劇本執筆人由邵子南變成了后來寫過“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的賀敬之。這是個燙手山芋,賀敬之二稿寫完后,再次試演,結果觀眾仍不滿意,這回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階級斗爭上。最后,幾經討論,在歌劇的最后,加了一場群眾斗爭大會的情節,以滿足貧下中農對地主惡霸的滿腔仇恨,不過,也沒有設計槍斃黃世仁,只是人民群眾把他押走了。
《白毛女》是歌劇,可是五個作曲者,沒有一個懂歌劇。結果寫出的歌劇可想而知——四不像,這可急壞了當時負責《白毛女》創作組的張庚同志。他想這可怎么辦?作曲者寫了一個多月,寫了一首又一首,可是他就是覺得不對。他一琢磨,之前的思路可能有問題。他們所面對的主要觀眾,不是西洋音樂愛好者,而是接受教育不多的農民。應該要創作出一種新的民族風格!想到這,他把作曲找來,統一思想,然后要求他們先把《白毛女》首段的《北風吹》給寫出來。
思路對了,創作仍然舉步維艱。五個作曲,創作三天,幾十首小樣,張庚仍不滿意。
有一天,作曲之一的張魯突然有了靈感,以民歌“小白菜”作基調不行嗎?他試著寫了幾句,喜兒滿心歡喜的情緒似乎也在他的心里迅速地開花結果。“北風那個吹啊,雪花那個飄啊”,張魯一揮而就,然后,興奮的他小跑著奔進張庚的辦公室,唱給他聽。也許是張魯的演唱水平一般,張庚并沒有張魯那么興奮,他只是冷靜地聽著。聽完,他把旁邊的小王叫來:“小王,你來唱唱這段。”小王的歌喉非張魯可比,一唱,張庚一聽,馬上拍板:“就是它了!”
這位小王,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王昆。
1945年4月28日,在黨的“七大”召開期間,《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會堂舉行首演,獲得極大成功。全國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首長,幾乎悉數到場,規格之高,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都是罕見的。當演到黃世仁對喜兒施暴時,有幾個女同志已經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李富春回過頭去,勸解她們:“同志們吶,你們這是干什么?這是演戲啊!”但語調很沉痛。
黃世仁徹底激怒了勞苦大眾,演出完畢后,對于原劇中黃世仁給押走的結局,大家伙們都覺得不過癮。大家七嘴八舌,都覺得,對這樣的大惡霸,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于是,賀敬之回憶,演出完畢之后,中央書記處的評價有三條:“第一,這個戲是很及時的;第二,藝術上也是成功的;第三,黃世仁這樣的惡霸地主應該槍斃。”
從此,惡霸黃世仁在劇末由逮捕,變成了槍斃。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我叫羊鳴,這個名字很怪,牛羊的羊,一個口加一個鳥的鳴。”作曲家羊鳴在自己的自述文章中這樣幽默地介紹自己。
這是他的筆名,不是真名。他原名楊明,用羊鳴而不用楊明,他自己給出的理由是:“這個名字很有詩意,再有對我也是一個鞭策。”不管是羊鳴還是楊明,不是音樂界的行內人聽著多少有些陌生,但要提起歌劇《江姐》的選段《紅梅贊》,相信上一點年紀的中國聽眾一定耳熟能詳。
這也是羊鳴這一生中自己覺得“最值得驕傲的作品”。
這部名噪一時的歌劇是怎么來的呢?還得從一頓飯局說起。
1959年,在北京空軍政治部文工團任職的羊鳴與劇作家、詞作家閻肅以及作曲家姜春陽一起合作,寫出了小歌劇《江四姐》,得了一筆稿費,幾個人相約去東來順撮一頓。
幾杯茅臺酒入肚,話匣子就打開了,有人提議:“我們寫個大一點的劇本吧。”寫什么呢?大家思來想去莫衷一是,這時候,閻肅提議:“《紅巖》中的江姐是個非常感動人的形象,不如就寫一個《江姐》!”
江姐,這位在反動派的渣滓洞集中營中不屈不撓的女戰士,因為小說《紅巖》而家喻戶曉,有著很好的群眾基礎,也令創作者激情澎湃。
閻肅一個月就寫出了劇本,負責作曲的羊鳴、姜春陽和金砂前往重慶渣滓洞、白公館、華瑩山等舊址,一個個拜訪江姐生前的戰友,吸收川劇的音樂元素,兩三個月就寫出了初稿。
可是,當他們信心滿滿地將劇本交到文工團領導手中時,迎頭澆來的卻是一盆冷水。領導給出的意見一邊倒:完全否定。理由是“生搬硬套川劇”,要求他們的藝術創作要“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
羊鳴等人商量了一下,還是需要再深入民間,只是這一次,目的地不再是四川,而是江南,江南的杭劇、滬劇、越劇和婺劇為一部充滿革命意味的歌劇注入了柔美的情調。
這樣寫出的歌劇是有溫度的,也是有美感的,歌劇《江姐》朗朗上口的詞和曲令人一聽難忘。“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1964年9月,歌劇《江姐》在北京首演,立即轟動京城,也傳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10月12日夜,有個干事突然跑來向文工團報告:“毛主席明天要來看演出,地點定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
大家伙兒既緊張,又興奮。第二天,毛主席、周總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江姐》的演出。毛主席看得非常認真,觀看過程中幾次帶頭鼓掌。他看到江姐被捕就板起了臉,顯得非常生氣;看到幾個大特務的丑態,毛主席則會心一笑。
演出完畢,毛主席上臺與演員一一握手,說:“看了你們的歌劇,劇本改寫得不錯嘛。”一句話,演員們懸著的心就算落了地。
毛主席寫過這樣的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江姐們為了新中國的誕生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而中國民族歌劇也將在革命敘事中展開它的發展歷程:《洪湖赤衛隊》、《劉胡蘭》、《黨的女兒》……歌劇藝術之外,也打上了意識形態的濃濃印記,它們帶來了中國民族歌劇的春天,也為日后中國歌劇遇到的困難,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歌劇是個冒險的行當
一個政治嚴肅時代的終結意味著中國民族歌劇由盛轉衰。
意識形態不再能左右中國歌劇的創作,不僅沒有使中國歌劇走向一個新的高峰,似乎反而讓大家變得迷惘。但隨著國門的打開,真正優秀的西方歌劇,也一部部地登陸中國,登陸上海。
歌劇雖是陽春白雪,卻也是身價的保障,上海大劇院藝術總監錢世錦先生還記得:“建上海大劇院的時候,市領導覺得,大劇院應該就是演歌劇、交響樂這樣的高雅藝術為主的劇場,所以我當時花了比較大的力氣在策劃歌劇演出方面,這是和大劇院的身份、格調相符的。”
上海大劇院第一個演出就是歌劇《阿伊達》。有藝術上的考慮,但主要還是覺得大劇院開幕,有意大利的經典歌劇那是水準的象征:“開羅歌劇院的落成委托威爾第寫了這個歌劇,而且又是蘇伊士運河開航,兩大盛事成就了這部歌劇。后來形成了一種慣例,好像劇院落成都要以《阿伊達》來開幕,《阿伊達》也很考驗一個劇院的能力、水準和格調。我們覺得也要表示一下我們大劇院也是能夠和世界一流劇院相媲美的,于是我就向意大利方面提出想演這部歌劇。”
改革開放,富裕了,精神上也要成為貴族,但歌劇終究曲高和寡,日后音樂劇——而不是歌劇——成為大劇院的票房頂梁柱已經說明了問題。
不要說中國人,就是在西方,寫歌劇也是個冒險的行當。比才的《卡門》在他生前并不被人們看好,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贏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這對比才來說顯然是太遲了。莫扎特的天才誰都無法否認,不過他的命運就實在有些讓人看不懂了。寫《魔笛》的時候,莫扎特已病入膏肓。在此之前,他寫的歌劇《阿斯卡尼歐在阿爾巴》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米蘭的費迪南大公也是贊不絕口。不過費迪南的母親瑪麗亞·特麗莎可不這么看,他寫了封信給他的兒子,稱莫扎特是一位“像乞丐一樣到處求乞的人”。
羅曼·羅蘭是貝多芬的鐵桿樂迷,卻對歌劇界的天皇巨星瓦格納冷言冷語。文人相輕的毛病似乎在歌劇界也很通行。肖斯塔科維奇這樣來評價普羅科夫耶夫:“普羅科夫耶夫笨得像只鵝,從來愛吵架。”而普羅科夫耶夫也反唇相譏,他看完肖斯塔科維奇的《麥克白夫人》后,從他的嘴里只輕蔑地迸出了兩個字:“可笑”,這令肖斯塔科維奇火冒三丈。
西方歌劇界的紛紛擾擾似乎還沒有影響中國,國內歌劇界基本上還是和諧為主,上海大劇院對中國本土歌劇就一直支持有加。《雷雨》、《詩人李白》、《木蘭詩篇》、《西施》……都曾在上海大劇院上演。但錢世錦也承認,時代在變化,人們的欣賞口味也在變化:“歌劇一般也就演個一場兩場,而音樂劇卻能久演不衰,這是因為現代人的口味已經有所變化,音樂劇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些貼近現代生活的作品。歌劇是農業社會的產物,而音樂劇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是城市的產物。商業社會的發達促成了音樂劇的發達。”
80年代之后,中國歌劇創作的絕對數量并不少。《馬可·波羅》(王世光曲)、《安重根》(劉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孫武》(崔新曲)、《張騫》、《蒼原》(徐占海等曲)、《鷹》(劉錫金曲),但是總體而言,成功的不多,沒有再現《白毛女》、《江姐》時期的輝煌。
唱歌劇的李白和《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詠·別》之前,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郭文景和著名男高音田浩江的《詩人李白》就曾在上海大劇院上演,并且在國內外引起了不俗的反響。
李白拿腔拿調地唱歌劇?李白的仙風道骨到了胖胖的田浩江這里總讓人有一點異國情調的感覺,想想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導演林兆華聲稱他對歌劇不怎么懂。他坦言:“歌劇我也不怎么在行,我也不怎么看,也不懂作曲。”在不懂曲調的前提下你怎么來編排戲劇?不僅觀眾心中充滿了疑問,就是主演田浩江一開始也有點摸不著頭腦:“開始幾天的排練,我不是很能理解他要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他似乎是不要東西。他對我說,不要演,尤其是不要像西方歌劇一樣演。那么對我來說,其實最難的就是不演。這花了我很長時間來領悟他所要的東西。”
神奇的是,只沒過幾天,田浩江就說自己逐漸適應了林兆華的導演思路,而且合作變得特別愉快。“不怎么在行”的導演導出來的歌劇會成功嗎?林兆華給出的答案理直氣壯:“我只能說我要找到一個感覺,我感覺對了就對了。”
林兆華讓田浩江開了竅,今年,田浩江走出林兆華的歌劇迷宮,又步入“進念·二十面體”胡恩威的記憶宮殿。
榮念曾嫁接實驗與戲曲的手法到了“進念·二十面體”的另一位大將胡恩威手中又有了新的可能——那就是10月1日在香港上演的七幕歌劇《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這是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代表作,而利瑪竇又是東西方交流最重要的先驅之一。導演胡恩威說:“在舞臺重建歷史現場,這是一種對于宗教和社會發展的探討。”
心寬體胖的田浩江來演高鼻深目的利瑪竇似乎比他演李白更合適一些,他對利瑪竇的理解也很特別,他說:“今天我們需要利瑪竇這樣的人,因為他的信念是和平。”
就像榮念曾改編的《夜奔》利用大量的多媒體,將古今中外熔于一爐一樣,胡恩威的歌劇也將音樂、歌唱、舞蹈、偶戲組成一個錯綜迷亂的“記憶宮殿”。在歌劇中,利瑪竇來到中國,向中國人傳授一種“記憶宮殿”的記憶法,據說這是13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發明的一種有助倫理道德的記憶法,具體說來就是把要記憶的事物賦予一個形象,并分派到一個場所,儲存起來。玄奧?有那么點兒,看完歌劇,我們記住利瑪竇了嗎?記住史景遷了嗎?還是,記住了胡恩威和他奇幻莫測的歌劇實驗?
和《詠·別》一樣,這些歌劇,都以西洋唱法來演繹,不再是民族唱法的天下。這是中國歌劇與世界接軌的一次次嘗試,也為中國民族歌劇唱響了挽歌。回顧歷史,多少讓人有些唏噓感慨,和過去永別了,才會翻開中國歌劇一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