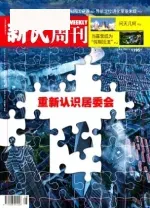城市“中產”:從“偽幸福”到“真幸福”
應琛


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數的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幸福是什么?
在古代,“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一直被視為人生四大福;后來便是“富貴是福,多子是福,團圓是福,長壽是福”;再往后“平淡是福,貧窮是福,吃虧是福,孤獨是福”……而在中國民間,有這樣的拆字和解釋:“幸”的上面是土,下面是錢;“福”的左邊是衣,右邊是田。于是“幸福”與“有房有錢,豐衣足食”畫上了等號。
正所謂“幸福”是千人千事,所悟不同。
近日,由一保險公司聯合媒體共同制作的一份《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正式發布,根據調查結果,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數的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這次調查的取樣是:全國10個城市7萬余名20歲至40歲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的人群,也就是所謂的城市中產階層。于是關于中產階層的種種話題再次被提起:什么樣的生活才算是中產階層的幸福生活?
記者了解到,多數一線城市的中產家庭之所以幸福感指數低下,是由于家庭經濟壓力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價負擔,加上工作競爭激烈、交通擁擠、子女教育成本高等等。由此看來,有著一定財富和理想事業等表面風光的中國中產階層,他們的生活卻被房奴、車奴、孩奴、卡奴等“奴時代”的層層枷鎖捆縛著,生活富足的“幸福”難以彌補他們內心的缺失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究竟中國的中產階層的幸福在哪里?
中產欲出逃
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已達到23%左右,但其實,其中的不少人只是“貌似中產”,他們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人在2005年之前在某一線城市中買了一套房子,那么到今天,從升值后的資產來看就可算是中產階層了。但實際上,他是欠了債的。現在許多人的按揭都很高,通常要拿出收入的50%~60%來償還按揭,這邊還債,那邊要相應地壓縮其他消費,生活品質并不高。所以只能說他們是“貌似中產”。當然,從政治學角度講,只有這個國家的中產階層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會結構才合理,但我們現在還達不到這個標準。
馬建偉和董鶯夫婦二人便是其中的一員。他倆在上海安家4年了,有車有房有很好的職業,家庭年收入在15萬元左右,獨缺上海戶口。就在最近,拼搏在這座競爭異常激烈的移民城市讓這對夫婦感到壓力。
“在上海錢是賺不完的,有那么多標桿人物在這里,很多大學同學已經自己創業小有成就。”馬建偉說,然而沉重的房貸、未來有了孩子之后的求學經費以及父輩養老問題讓他們覺得難以松懈,“在別人看來,我們夫妻倆生活在大城市,似乎什么都有了,卻不知道我們承擔著怎樣的壓力,有時覺得透不過氣來”。
妻子董鶯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們2007年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層,目前還欠銀行近80萬元。她給記者算了每月的支出,養車大概在2000元左右,房貸每個月5000元,再加上平時日常開銷大概4000元,如果請客吃飯聚會一次動輒千元左右。“我們還是想盡早將房貸還完,這樣算下來每個月結余真的不多。”
加上2008年中,董鶯遭遇了公司裁員,接著幾個月連換了兩三家公司都不是很滿意,也使得家庭收入一度減少了許多。好在這些天,她找到了一份較理想的新工作。
“目前來看,新工作還算不錯,收入也與之前差不多。但如果是在紹興,通過家里的關系,我們夫妻倆都能找到比現在更好的工作,生活上也能輕松許多。”工作上的波折讓董鶯萌生了回家鄉發展的念頭。他們的憂慮除了現實問題,還有將來的長遠負擔。由于他們所買的房子不是重點小學的學區房,將來有了孩子,讀小學可能還涉及一筆高昂的擇校費。此外,馬建偉來自農村家庭,父母的醫保都比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筆用于將來抵御疾病風險的錢也需要存下來。
“公公年紀大了,有高血壓。婆婆身體也比較弱,最怕的就是他們生病。”董鶯說,“我們商量后,決定再用一年的時間拼搏一下,如果還不能改變現狀,我們就決定離開這兒,回家鄉發展。”
逃離的總是“外地人”
上世紀90年代后,美國就出現城市白領遷移的現象。當時的背景是美國郊區化浪潮高漲。除了城市本身問題的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從人口流動的特征來看,唯有高學歷者、高收入者、具有專業技術特長者的流動性最強。
這種現象隨著美國資源的均衡發展而從未間斷。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學家肯尼思·M.約翰森博士的研究,從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間,共有160萬人口從美國大都市遷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們遷居的理由大多是因為小城市治安穩定、交通方便、房價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氣中休閑娛樂。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婦都認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長。
“他們已經厭倦了時尚潮流和物質虛榮,美國人重新發現,家庭生活的樂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價值。他們發現,原來生活需要野外燒烤的閑情逸致,需要家庭團聚的幸福。”約翰森博士說。
英國《經濟學人》的調查也顯示,中國一線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鐘用在上班路上,這個數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擁擠是重要原因。過去讓大都市的人們常常夸耀的城市標簽——地鐵,如今變成了擁擠的代言詞。二三線城市的交通狀況則完全不同。步行10分鐘上下班是一種常態。據一項調查顯示:在一線城市,75%的人晚上6點至8點吃晚飯,而二三線城市,70%的人則是5點至7點晚餐。
顯然,中國大都市白領階層的被迫逃離與美國白領的遷居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國,戶籍問題形成了很大的障礙。在一線城市工作,如果你沒有當地戶籍,讀書、就業、購房、養老、醫療等等問題都很難解決。
小馬夫婦回到紹興,不但能夠解決上述問題,生活品質明顯優于上海。對他們來說,還有更多的發展機會。過去在一線城市布局的企業和知名品牌,開始向二三線市場進軍,這些企業需要在一線城市有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偽幸福”的思考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大都市,都是白領們曾經熱衷的城市。按理說,能成為經濟最為發達四個地區的中產階層,是很多人的夢想和追求。雖然,在這些一線城市不一定能實現每個人的夢想追求,但這確實是傳說中的“百舸爭流”之地,能在逼仄的城市空間中擠出自己的一份生存空間,自然會有些“盡顯英雄本色”的豪邁。
現實卻是,這些城市成了“不夠幸福”和“偽幸福”的地方,那些在大都市工作過幾年的中產們不堪“三座大山”的壓力而萌生退意,著實打擊了相當一批人的奮斗信心。
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隨著二三線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過大、競爭激烈,2007年以后逐漸出現城市白領向宜居的二三線城市“被流動”的現象。甚至農民工對大都市也失去了興趣,近幾年連續出現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領逃離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17.9%增長到2008年的46%,增長了28.1個百分點。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水平超過50%,標志著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轉型,就會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期加速階段。
而這次的“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更佐證了上述現象。調查報告顯示,南京、成都、福州、重慶的幸福指數分列前4位,而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數最低,與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價飆升則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從住房變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為了負擔房貸,夫妻雙方必須獲得更高的報酬或用更多時間加班。缺少了溝通的家庭生活變得程序化,家成為臨時住所。然而,健康、情商、財商、家庭責任以及社會環境,被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是影響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關聯,缺一不可。
“事實上,這和發達國家的白領轉移有著很大不同,這是一種被迫的轉移,我們處在工業化中期,這個階段白領離開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產市場畸形上升,以及物價的昂貴,給這個階層很大的擠壓,中產階層的品質得不到保證。另外,由于高校的擴張,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擠壓了原本屬于有工作經驗白領的部分空間而讓他們感到競爭激烈壓力過大,他們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競爭較少、幸福感較明顯的城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張翼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表示。
可話又說回來,打擊歸打擊,這遠遠比在“被時代”里“被幸福”真切得多、真實得多。還記得去年的“2009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評選結果嗎?2009年12月26日這份榜單最終出爐之時,許多網民直呼“被幸福”的那種場景還歷歷在目。當時,網民們紛紛質問,請列舉出真正讓我們感覺幸福的物價與理由?房價這一重大問題先放在一邊,就是普通的水電氣價格也是“逢聽證便漲價”。更不用說,那些“蝸居”于城市的“蟻族”和“犀利哥”了。
所以,雖然一句“偽幸福”切到了公眾的痛處,卻遠遠要比“溫水煮青蛙”里那些自以為洗熱水澡的人幸福得多。這或許就是傳說中的“痛并快樂著”。可以說,從“被幸福”到“偽幸福”,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雖然距離“真幸福”還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有提出“偽幸福”的心態在,幸福就不會變成一句空話。
“偽幸福”的提法里沒有粉飾與美化,更沒有所謂的官員政績,有的只是切實的公眾感覺與公共利益。將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列為最低,其實是一種對于高房價的宣戰,更是對低房價里幸福感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