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細菌”來襲
黃祺 吳曉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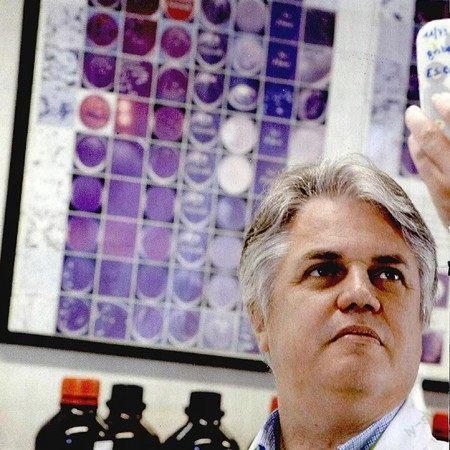
甲型H1N1大流感剛剛隱退,“超級細菌”NDM-1卻立馬殺到,人們還未來得及好好安撫長期緊繃的神經,如今又在各種關于“超級細菌”的傳言中不知所措。
“超級細菌”是什么
13日,比利時傳出一起NDM-1細菌死亡病例,這也是這種病菌引起的首個致死案例。另據英國媒體報道,英國已出現至少50宗NDM-1細菌感染病例,5人感染后死亡,但尚未證實。
在最近的一周里,NDM-1細菌的名字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媒體上,就算那些本來不甚關心科學和醫療信息的報紙、廣播,也加入到對“超級細菌”的報道中。當消息傳到中國,經歷了SARS、禽流感、甲流的中國民眾,對此更加敏感。
上海復旦大學華山醫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王明貴,被好幾家媒體追問類似的問題:感染這種細菌是不是無藥可救?它會不會成為新發的傳染病?感染這種細菌的幾率有多少?王明貴給出的答案是,目前中國還沒有NDM-1細菌感染的相關報道,他正準備對細菌感染病人的菌株樣本進行篩查,明確國內是否存在NDM-1細菌的感染。但是,沒必要那么緊張,細菌耐藥在我國早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一次,不過是又發現了一個新耐藥型的細菌。
本輪報道發端于8月出版的《柳葉刀——感染病》雜志。在這本最權威的醫學期刊上,刊登了一篇有31位作者的論文,題目為《印度、巴基斯坦、英國出現新型抗生素耐藥機制:一項分子、生物及流行病學研究》(《Emergenceof a new antibiotic resistancemechanisminIndia,Pakistan,andtheUK:amolecular,biological,andepidemiologicalstudy》)。
文章中提到,來自英國卡迪夫大學、英國健康保護署和印度馬德拉斯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印度金奈市確診了44名感染NDM-1細菌的患者,在印度哈利那亞邦確診了26名,英國37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域還有73例。攜帶NDM-1基因的細菌,能夠對包括廣譜抗生素碳青霉烯類在內的幾乎所有的抗生素產生耐藥性,所以被叫做“超級細菌”。
論文被英國大眾媒體報道后,立刻成為全民關注的新聞事件。英國《衛報》11日報道,論文的通訊作者英國卡迪夫大學醫學教授蒂姆·沃爾什的研究表明,這種病菌可以通過飲用水等途徑傳染,表現癥狀為腸道感染,死亡率很高。
除了替加環素和多粘菌素,幾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對它無效。而在目前有效的兩種抗生素中,多黏菌素是有50年歷史的老藥,它對腎臟損害嚴重,很多國家已經停止使用。沃爾什同時也表示,很快這些細菌就有可能對這兩種抗生素產生抗藥性。同時,也有科學家指出,可能10年內都不會有對NDM-1有效的新型抗生素出現,勤洗手能有效阻止其傳播。
事實上,最早對NDM-1的報道,是2009年《抗微生物藥物及化療》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這個研究也是由蒂姆·沃爾什主持的。文章講到一名印度裔的瑞典人,曾經到新德里旅行,并在那里接受過住院治療。他被檢查出感染了攜帶NDM-1基因的細菌,而這種細菌具有廣泛的耐藥性。
目前已發現NDM-1基因存在于一些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腸桿菌等菌株中,但研究者同時還發現,該基因可以通過基因水平轉移從一個菌株轉移到另一個同菌屬或不同菌屬的細菌。這種DNA質粒能在細菌中自由復制和移動,從而使這種細菌擁有傳播和變異的驚人潛能。
耐藥菌有多危險
如果感染NDM-1細菌,是不是等于無藥可救?
王明貴教授認為,理論上的確如此。“在目前的研究報告中,攜帶NDM-1基因的細菌,對替加環素和多黏菌素的敏感度稍微高一些外,對其他我們臨床上常用的抗菌藥物,比如青霉素、頭孢菌素類抗生素等,幾乎都不敏感。也就是說,一旦感染NDM-1細菌,目前臨床在用的抗生素都不能控制。”由于國內沒有替加環素和多黏菌素這兩種抗生素,如果感染發生在中國,幾乎就是無藥可救。
“準確地說,只要是廣泛耐藥的細菌,都可以叫做超級細菌,NDM-1細菌只是它們中的一種。”曾經被戴上“超級細菌”高帽的,有MRSA(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VRE(耐萬古霉素腸球菌)、泛耐藥鮑曼不動桿菌。“耐藥菌造成的死亡,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醫院內發生。”王明貴介紹說。MRSA一度在美國蔓延,政府調查預計每年有9萬多人嚴重感染這一細菌,每年因MRSA感染的死亡病例甚至超過感染HIV病毒(艾滋病)。
NDM-1細菌的出現讓噩夢重溫,對此仍心有余悸的人們被卷入新一輪的“超級細菌”寒流。英國《衛報》健康欄目編輯莎拉·波士利的擔憂頗深。她認為“超級細菌”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傳播可能預示著抗生素時代的終結,醫生將難以治療受到耐藥細菌感染的患者。
但在王明貴看來,公眾沒有必要對NDM-1細菌感到恐懼,即便它是一種超級耐藥的細菌,也不一定是最危險的耐藥菌,因為在醫學界,細菌耐藥是個老問題,耐藥細菌廣泛存在。
“這次NDM-1細菌受到關注的原因有三個。第一,發現NDM-1基因的這種細菌,本來屬于耐藥情況不是很嚴重的一個細菌種類,在它身上出現如此嚴重的耐藥性,引起了醫學界及科學家的特別關注。第二,目前研究表明這個耐藥菌從南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傳播至歐洲和美國等國家,說明耐藥菌已經在跨洲際播散,可能會造成大范圍的影響。第三,歐洲一直是抗生素管理比較嚴格的地區,細菌耐藥的情況比其他地區要好,所以歐洲出現這類超級細菌感染,公眾會更加緊張。”王明貴說。
他認為,公眾不用恐慌,首先,目前的報道認為,NDM-1細菌的傳播的主要途徑,很可能是直接接觸,中國人到印度去接受醫療服務的情況極少;另外,高度耐藥菌往往繁殖緩慢,耐藥菌的傳染能力并不是非常強。“而且,此類耐藥菌的傳播絕大多數發生在醫院內,特別是免疫力低下的老弱患者和腫瘤患者等,有可能遇到這個問題,正常免疫力的健康人群,一般不會感染此類耐藥菌。”
事實上,值得擔心的耐藥菌,還有很多。王明貴教授很早就開始關注鮑曼不動桿菌耐藥的問題,這個細菌近年來感染發生率明顯上升,可引起肺炎、腦膜炎等各類嚴重感染,住院重癥患者受感染的情況更為常見。這種細菌的耐藥情況,在全世界都很嚴重,對治療革蘭陰性桿菌的“王牌”藥物碳青霉烯類的耐藥率達到50%。鮑曼不動桿菌可能不如如今的NDM-1細菌有名,但它的危害更勝于NDM-1細菌。
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負責人馬丁·J.布萊澤表示:“這些對抗生素具有耐藥性的細菌無疑是帶有危害性的,但DNM-1比MRSA更令人擔憂嗎?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過早。”
從英美等國的官方公告來看,他們并未過高估計NDM-1的殺傷力,但根據他們的部署和態度,也絕沒有輕敵。CDC反復重申防止這些高度耐藥生物傳播的重要性;英國衛生部正與HPA(英國健康保護署)聯手監測超級細菌的傳播并著手研發新抗生素;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正與世界衛生組織和有關衛生機構跟進此次事件,并與醫院的實驗室聯系,制定加強監測這種細菌的安排;印度醫療機構也正全力研究這種細菌,并試圖弄清其傳染機制。
都是印度惹的禍?
NDM-1看上去是個十分深奧的代號,其實,ND只不過是“新德里”的英文縮寫,它的中文名翻譯過來是“新德里金屬β內酰胺酶-1”。目前被調查的感染病例,多與患者赴印度旅行或者住院治療有關。《柳葉刀》上的論文中就提到:“英國確診的很多感染NDM-1細菌的病人,都曾在最近幾年到印度或巴基斯坦旅游過,或者曾與這些國家有過聯系。”
據報道,美國至少3宗病例;澳大利亞發現3宗。這些病人多曾往南亞旅行或去印度整容。而印度本土也錄得逾百宗,巴基斯坦、加拿大、法國、荷蘭和孟加拉國均見感染病例,全球感染人數已有170例。
香港衛生署早在去年10月,就從一名男病人的尿液樣本中化驗出帶有NDM-1的大腸桿菌,經治療后痊愈。該男子66歲,印度裔。
對于患者的這種類似經歷,有西方媒體不依不饒,反復提到去印度“醫療旅游”的危害。《紐約時報》記者唐納德·麥克尼爾于11日的報道中提出,通過“醫療旅游”赴印度接受整容、矯形甚至器官移植等手術越來越普遍,雖然那里的有經驗的醫師和一流的醫院的價格比西方國家便宜很多,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CDC(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6月24日在官網上發布公告,提醒醫生關注在印度或巴基斯坦接受過醫學治療的患者。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病理學及實驗醫學系的約翰·皮陶特在雜志評論中,公開建議密切關注有過印度“醫療旅游”歷史的病人,經篩查后才讓他們回家。
王明貴教授介紹,就像天文學界常常用發現者的姓名為新星命名一樣,細菌耐藥基因的名字有時候是按發現地的地名來命名的。不過,對于新發現耐藥細菌的名字以及相關的評論,印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印度衛生部于12日發表聲明,對英國雜志刊登報告將超級細菌的源頭指向印度表示不滿,并強烈抗議英國政府的相關警告以及將新發現的超級細菌以印度首都新德里命名。印度衛生部部長阿扎德指出,研究團隊里的印度學者庫馬拉薩米已向媒體澄清,登在《柳葉刀》上的報告最終版本由英國人操刀,有些觀點是他也不知道的,所以阿扎德強調事件有可疑。
印度衛生部醫藥研究局局長卡杜什也在同一天表示,一些西方傳媒把一種不明病因的傳染病與印度聯系在一起是完全錯誤的,一些西方醫學家在沒有搞清事實真相便武斷地認定某種新出現的病癥起源于印度是不負責任的。這種病例同時出現于幾個國家,也可能是西方游客從其他地方把細菌帶入了印度。
印度醫學界也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有專家認為具耐藥性的細菌并不新奇,不明白為什么要針對某一地區。更有專家懷疑報告是宣傳戰,具有政治動機,意圖打擊印度紅火的醫療旅游業。曾有媒體報道,印度旅游業高居世界第二,僅次于泰國。其“第一世界的服務,第三世界的價格”越來越受到英美等西方國家的青睞。
后抗生素時代
細菌耐藥已然成為現代醫學進程中一個巨大的障礙。耐藥菌的不斷出現,甚至讓醫藥企業感到悲觀,進而放棄新抗生素的研發,轉向其他藥物。“有一段時間,幾家最知名的國際藥物企業,放棄抗生素研發。因為一種新抗生素的研發,投資可能10億美元,耗時10年,而在它問世僅僅兩三年后,就會出現耐藥的情況。”王明貴說,在醫藥公司看來,因為耐藥菌的大量涌現,研發抗生素不如其他藥物投資回報好。
在細菌、病毒、真菌等引發人類疾病的病原體中,細菌是最早被“征服”的一種微生物。人類利用抗菌藥控制細菌,曾經被視為文明進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要回到起點,當耐藥菌不斷出現以后,抗生素顯得捉襟見肘,細菌感染重新成為不容輕視的嚴重疾病。“超級細菌”種類越來越多,有人發明了“后抗生素時代”這樣的名詞,一種聳人聽聞的描述是,在這個時代,移植外科手術將幾乎不可能;切除闌尾將再次成為危險的手術;肺炎將重新成為老年人的“朋友”;淋病很難治療;肺結核將無可救藥。
當然,也有人表示樂觀。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抗生素耐藥性的專家亞歷山大·J.卡倫表示:10年前,紐約各大醫院,都曾是感染耐碳青霉烯類抗生素細菌患者的集中地,這些擁有不同變異性的細菌非常麻煩,但最終并未發展成公共健康事件。言下之意,就算目前“超級細菌”呈蔓延的趨勢,但像曾經出現過的一些耐藥性細菌一樣,并不會發展到失控的地步。
中國的細菌耐藥情況,比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嚴重。王明貴教授告訴記者,MRSA在中國對甲氧西林的耐藥率,高達50%-60%,在歐洲許多國家低于20%。
中國的抗生素濫用,一直是廣被詬病的問題,2004年衛生部發布《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后,情況有所改善,但極端耐藥菌的耐藥率還是在快速增長。
王明貴介紹,一個有中國十余家大型醫院參與的細菌耐藥性監測顯示,鮑曼不動桿菌的泛耐藥率,2007年是2.8%,2008年是11%,2009年達到17%。肺炎克雷伯菌的泛耐藥率,2007年0.3%,2008年0.6%,到2009年達到1.8%,“泛耐藥”指的是細菌對目前臨床應用的所有抗生素耐藥。兩種細菌泛耐藥率的迅速上升,不能不讓人感到擔憂。
抗生素在中國被濫用,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王明貴講到一個常見的現象,兒科門急診,發燒的孩子家長總是焦急萬分,一些家長會要求醫生開抗生素。王明貴說,小兒發燒多是由病毒引起,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只有少數病兒一開始是病毒感染,之后可能繼發細菌感染。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往往會給患兒使用抗生素。醫患誠信的缺失和醫院管理的缺陷,助長了抗生素的濫用,也讓中國成為細菌耐藥的重災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