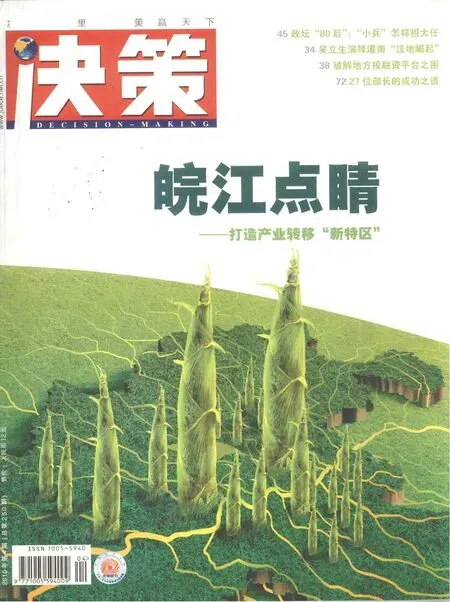湖州考核之變
■顧 春
核心爭議在于GDP指標的取消。有人質疑:“拿掉了GDP,還考核什么?”這樣的疑問,一定程度上也是湖州市決策層的爭論焦點。
3 月12日,在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任職培訓班上,長興縣委書記劉國富作了經驗介紹,長興縣強縣與富民互促互進良性發展的經驗,引起了學員的極大興趣。
是什么讓長興的做法如此受關注?
讓我們把時間推回到2003年,當年12月11日,一個被稱為“不要發展”的會議曾在湖州長興縣掀起一陣轟動。該縣領導在會上宣布,從當年12月20日開始到第二年3月,全縣187家耐火材料企業全部列入整治或整改對象,200多只煙囪限期拆除、改造。
“急功近利的發展到底給長興帶來什么?”時任縣長劉國富經過反思以后,認定長興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那么切入口在哪里?
“拿掉了GDP,還考核什么?”
這樣的反思不僅存在于長興縣,而是遍布整個湖州區。其時,湖州正面臨發展中的種種尷尬:礦山開采曾經是當地的一大產業,開山甚至破壞了“西塞山前白鷺飛”的西塞山;長興的蓄電池產業造成污染,被媒體曝光;太湖藍藻暴發,環湖城市之一的湖州也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樣的尷尬在很大程度上與單一的、以GDP為核心的干部考核體系有關。現實生活中,GDP成了“一俊遮百丑”的唯一指標。為此,湖州把轉變干部考核模式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口。
正是在2003年底,湖州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一份《關于完善縣區年度綜合考核工作的意見》。決定從2004年起,湖州干部考核取消GDP指標,強化對經濟綜合實力增強、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考核,并改變以內部考核、上級對下級考核為主的做法,將考核過程和結果向社會公開。
此舉在當時被稱之為“石破天驚的改革舉動”。
核心爭議在于GDP指標的取消。有人質疑:“拿掉了GDP,還考核什么?”這樣的疑問,一定程度上也是湖州市決策層的爭論焦點。
然而,力主改革的市委主要領導堅持認為,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一些地方把“發展才是硬道理”錯誤地理解為“增長率才是硬道理”、“GDP增長才是硬道理”。
內蒙古河套灌區位于巴彥淖爾市境內,總灌溉面積57.4×104hm2,有總干渠1條,干渠13條,分干渠48條,各級灌排渠道6.4萬km。該區屬典型溫帶大陸性氣候,夏季高溫干旱、冬季嚴寒少雪,年降雨量100~250 mm,蒸發量2 400 mm,主要種植向日葵、玉米、小麥等作物 [8-10]。根據監測,河套灌區2010—2016年單個面積大于3.33 hm2的淖爾數量平均為401個,水面面積平均101.27×102hm2。淖爾多處于低洼地,湖渠交錯,周邊耕地資源豐富。
“當時的現實擺著,我覺得必須進行環境治理,否則要出大問題。但如果沒有淡化GDP考核的決定,沒有制度上的保證,這個決心還是難下。有了制度保證,再大的阻力,我們還是做下去了。”劉國富說。
新《意見》的關鍵,正是在實踐中淡化GDP的分量,避免“數字出干部”的弊端。“我們無法做到完全不提GDP,因為到目前為止,這還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這一定不是干部考核的唯一標準。”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說。
有人如此評價:薄薄4頁紙的《意見》,標志著湖州成為全國干部政績考核改革的先行者和試驗田。
改變考核內容
6年來,湖州基層干部要面對的,就是一個迥異于GDP核心的考核體系。
截至2009年,湖州市三縣兩區綜合考核體系,主要包括了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社會民生、執政能力四大類16項指標。而社會民生類更是細分為居民收入、創業就業、城鄉建設、社會保障、社會事業、平安湖州6項指標。
6年來,湖州市嘗試建立起“分類考核”的辦法,改變“長跑和游泳一起比賽”的弊端,讓不具備發展工業條件的鄉鎮徹底擺脫GDP考核約束。
以湖州市安吉縣為例。該縣下屬15個鄉鎮被分為三類,一類有工業園區基礎的鄉鎮,考核工業經濟;二類有工業功能區又有自然保護區的鄉鎮,雙考核;三類是山區鄉鎮,只考核生態保護和新農村建設。
報福鎮屬于第三類。鎮黨委書記顧建強說:“考核就是我們工作的指揮棒。按原有辦法考核GDP,我們這樣的山區鄉鎮怎么干都不行,工作哪來積極性?搞了分類考核,工業發達的鄉鎮有事干,山區鄉鎮也有事干。”
統計顯示,湖州已連續5年農民收入增幅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有20個國家環境優美鄉鎮、38個省級生態鄉鎮、148個市級生態村,是浙江唯一下屬縣全部獲得省級以上生態縣稱號的地級市。
考核方式之變
改變的不僅僅是考核內容。
為改革慣常考核體系中“不換屆不考察、不提拔不考察”的弊端,湖州強化了“經常性考核”辦法:班子考核有綜合考核、好班子考核、班子回頭看;干部個人有任前量化考核、屆中綜合考核、屆末綜合考核,再結合平時的民主生活會,每年的述職述廉、年度工作總結會,把一個籠統的“總印象分”分解為多項考核之和。
為使考核盡量全面,避免人為干擾,湖州市在考核中增加“民意調查”項目,讓群眾參評。“小鄉鎮通常有幾十人參加考評,多的有幾百人呢。”安吉縣組織部長李曉良介紹說。
在湖州市,除了嚴格的考察程序外,還有“兩圈”考察。
所謂“兩圈”,指的是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品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三個方面。從生活作風、公眾形象、社會公德等15項具體指標,按好、較好、一般、較差4個等次進行測評。
考察時,先在干部所居住社區張貼考察預告,向樓道鄰居和知情群眾發放測評表,組織部門深入街道社區,向社區干部、左鄰右里調查走訪,全面了解八小時外的生活。至今已有73批、1892人次接受“兩圈”考察,發現問題被談話誡勉的干部78人,暫緩使用5人,取消任職資格4人。
“只看在單位的表現,范圍小,不全面。萬一‘帶病提拔’,組織部門壓力也很大。考察‘兩圈’,其實是讓群眾幫助監督干部,這樣不但心里有底,而且群眾很滿意。”湖州市組織部部長高玲慧說。
速度和民生協調發展
采訪中,幾乎每個官員都不諱言,雖然不考核GDP,但仍然求發展,而且照樣講速度。
從《意見》出臺至今,湖州市的GDP、財政收入、工業增長速度都仍保持著平穩較快的發展。這樣的成績,讓人覺得難能可貴。
“不惟GDP,不是不講發展經濟。經濟收入是民生的保障。沒有發展,最終就沒有足夠的財力投入民生,老百姓還是不滿意。”孫文友說。
不過,孫文友也坦承,“在發展之初,確實需要付出速度的代價。”
2004年,考核指標轉變后,湖州市長興縣曾痛下決心,整治礦山、水泥窯。結果是10億不到的財政,當年就少了2個億。
被整治的企業不理解,256個耐火窯爐企業主聯名寫信質問劉國富:“不要發展要什么?哪有你這樣的縣長?”
“如果只看速度,有很多機會我們錯失了。但如果錢是多的,水是臟的,空氣是污染的,壽命是短的,老百姓不需要這樣的發展。我們要探求的,就是又要速度,又要和諧的科學發展。”孫文友說。
協調發展也需探索前行。安吉一度遇到了左右矛盾的困惑:提出抓工業的口號,結果引進粗放項目后,付出了很大的環境成本;緊急剎車后,轉向放棄工業搞環境保護,幾年下來,又發現財政不足,就不能保證公共事業投入、城鄉統籌投入,新矛盾照樣尖銳……
直到2006年后,安吉確定一套新的發展思路:15個鄉鎮,確定其中具備條件的四五個鄉鎮發展工業,其余全部退出工業保護生態;堅持發展與生態環境相融合的產業,高規格配套園區建設,集約發展。現在確定的三類考核評價,不看經濟總量,看最后結果。這個結果,體現在具體指標之下,也被稱作“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