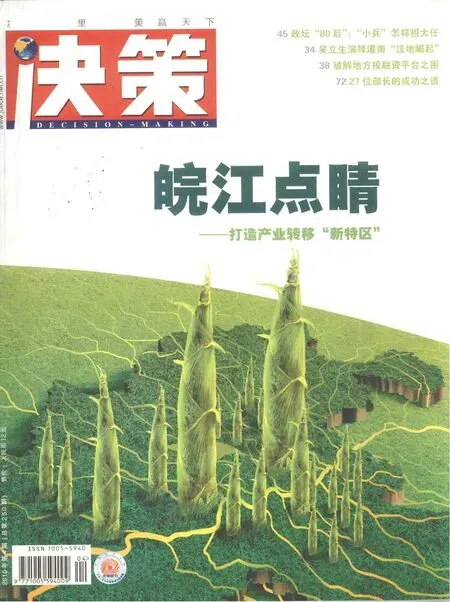解讀杜集
■本刊記者 楊 敏
杜集的基層轉型,是從拆掉一堵墻開始的。顧文感慨地說,如果中國的基層組織都能把圍墻拆掉,那才是真正的和諧。關鍵是,我們有沒有拆掉圍墻的勇氣和底氣。
陽春三月,記者來到淮北市杜集區劉樓村的時候,安徽山河礦業裝備有限公司建設工地上,兩棟六聯跨廠房已經拔地而起。占地6.3萬平方米,足有九個標準足球場那么大,山河的“大氣派”在皖北地區極為罕見。
“這還只是一期工程,山河項目規劃占地1500畝,計劃總投資20億元,全部投產后可實現年銷售收入35億,將增加就業崗位5000個……”,杜集經濟開發區的工作人員一口氣報出了一大串數據。這些數據,將真切地改寫這片土地的歷史。
10年前的春天,這里是綠油油的麥地;兩年前的春天,這里是連片的果園。可以說,劉樓變遷,是杜集這個城郊型農業區艱難轉型的一個縮影,隨著山河智能,這家中國裝備制造業最具成長性的上市公司的入駐,標志著熬過漫長的嚴冬,杜集的“工業化春天”終于到來了。
思維轉型:逼出來的一條路
淮北是一座因煤而興的城市,1958年,國家大規模開發建設的閘河煤田,就坐落在杜集區境內。
50多年間,杜集地下9對國有大中型煤礦、7對地方小煤礦,累計產煤4億噸,完成利稅30多億元。從體制上說,杜集拿不到一分錢,卻擺脫不了“資源型陷阱”的魔咒。20萬畝的土地塌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讓杜集發展道路荊棘叢生。
“如果按照低于人均3分地的標準計算失地農民的話,杜集10多萬農業人口中,現在還有4萬屬于失地農民。”區長張信鵬坦言,原來93個村莊,有84個存在塌陷土地,涉及搬遷的村莊占全區自然村落的80%。不停塌陷的土地對全區的水利工程、道路、水系等基礎設施的破壞也不容小視。
越來越多的農民無地可種,越來越多的村莊等著搬遷。不僅如此,“搖搖晃晃”的區級財政也讓杜集區各級干部在發展經濟問題上有心無力。杜集曾經“窮”到什么程度?據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郝圣領回憶,2000年他剛擔任副區長時,杜集的經濟發展是比較困難的。“區鎮兩級的機關公務員工資連續4個月都發不上,當時全區5個鄉鎮長每月25、26號,就開始想辦法去礦上借錢”。
地里長不出“金豆子”,吃飯財政更不能保發展。杜集下一步往哪去?
轉折發生在2002年,這一年時任杜集區委書記的王大軍去山東青島市北區掛職鍛煉,膠東半島各區縣工業經濟發展高歌猛進,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掛職一結束,他第一次提出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產業化的“三化”戰略。
對一個城郊型農業區來說,“工業化”戰略所帶來的觀念沖擊是不言而喻的。農業的基礎地位還要不要保留?郝圣領對當時發生在區長辦公會上的一次爭論記憶猶新,“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第一個問題到底是講農業還是講工業,大家意見就不統一。結果還是農業放在第一條講,200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才將工業化提到第一條。要說杜集發展工業真正沒有雜音,那要到2005年。”
思維轉型,的確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對當時的杜集干部來說,抓農業可謂諳熟于心,當時,杜集農業結構調整工作在全省連續十年處于先進位次,城郊型農業和“菜籃子工程”,是杜集經濟發展最大的亮點。農業區也要搞工業?一些干部覺得心里沒底也在情理之中。
不論先干。只有等大家看到工業化的希望,才能真正統一認識、轉變觀念。
發展工業沒有載體不行,2004年底,杜集區委、區政府決定在高岳鎮建設滂汪工業園。當時,全區有幾家零打碎敲的小型煤機配件企業,要讓這些企業進駐工業園,也不是一件易事。第一家入駐工業園的企業叫弘武液壓,當時廠子的老板守著八九間平房做廠房,區里領導苦口婆心去做工作,終于把她請進園區。經過5年發展,弘武液壓的規模與當年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從一個作坊式的小廠發展到年產值8000萬的規模企業。
2004年底到2005年上半年,像弘武液壓那樣被“勸”進園的小型煤機企業一共4、5家。區委書記顧文說起開發區創業時的艱難感慨頗多,“當時開發區沒幾家企業,大家看不到希望,區里也實在沒有錢再投入進去了,但我們還是挺過來了,可見堅持、堅守、堅韌多么重要。”
2006年9月,杜集經濟開發區升格為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籌備)。這個建成區面積只有5平方公里,雖然還是“籌備”,卻讓杜集人看到了“工業化”的希望。企業再小,聚集程度一高,就能形成園區特色,不久“小丁當”引來了大企業。
短短5年時間,杜集經濟開發區入駐企業82家,規模以上機械制造企業54家。“山河智能、三一重工、安徽機電、浙江中煤、無錫盛達……”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張長根隨口說出的這些企業,都是國內裝備制造業中數得著的明星。
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實質是一個主導產業再造的過程。具體到杜集區,最明晰最有潛力并初現端倪的就是煤機產業。那么,杜集又是怎樣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實現產業集聚的呢?
產業轉型: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做什么?怎么做?一直是杜集產業轉型過程最核心的兩大命題。
在顧文看來,一個地區的產業定位要緊緊抓住兩個關鍵點,一是要有產業基礎,二是要符合發展方向。
淮北是全國十大煤炭基地之一,地處淮海經濟區腹地,方圓300公里范圍內有19家礦業集團,230多家煤礦企業,礦山設備需求量在300億至500億,具有廣闊的市場優勢。加上上世紀80年代杜集大辦鄉鎮企業,產生了一批工礦配件企業和熟練技術工人,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

而從發展方向上來看,機械制造業一直有國民經濟的“裝備部”之稱,它的發達和先進程度,既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標志,也是工業化進程中最不可或缺的支柱產業。杜集培育煤機產業,可以說在國家的裝備制造業發展趨勢和能源發展戰略兩者之間找到了結合點。
有選擇就有痛苦。杜集煤機產業的培育過程,一直貫穿著“舍”與“得”的辯證法。2006年前后,建成不久的杜集開發區,大多數只是些“小丁當”,上億的投資項目對杜集來說都是極大的誘惑。顧文在接受《決策》記者采訪時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我記得很清楚,是一個周末,聽說一個3個億的項目有投資意向,我就一早上路去迎接這位客商”。一見面,顧文得知這是一個藥品中間體的精細化工項目,就連忙擺手說,不符合我們的產業定位,不能要不能要。“我的話太直截了當了,對方很不愉快”。雖然一口回絕了這個項目,顧文坦言,心里還是很舍不得,她說,“但是堅守產業定位,打造特色園區這個初衷不能變,特色就是生產力”。
投資上億的項目,被杜集婉言謝絕的不止這一家,張信鵬至今還記得,在一家大型玻璃生產廠家的去留問題上,杜集的決策者也曾經歷過類似的抉擇。
有舍就有得。
2007年,淮北第二次煤機會期間,湖南山河智能公司代表在杜集開發區呆了5分鐘,就決定在這里投資。“跟其他地區比,我們的優勢就是園區的特色,產業集聚程度高,配套條件好,這是山河智能和其他裝備制造業龍頭企業最看重的一點。”張信鵬告訴《決策》,2006年,杜集全區規模以上工業只有23家,但是2009年底,已經增加到119家。或許,這就是特色園區的魅力。
一個地區如何培育自己的特色產業?如何堅持自己的產業定位?對一個地方來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易。
顧文將杜集產業轉型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強制性定位,堅守我們的產業方向不動搖。二是針對性招商,那個時候大家是撿到籃子里都是菜,我們的做法是符合杜集產業定位的菜,才往籃子里面挖。第三是限制性入園,規定投資強度,規定項目投資時限,強調土地的集約化使用。”
如果說杜集經濟開發區是支撐其工業經濟起飛的“一體”,那礦山集紡織工業園、段園工業集中區就是“兩翼”。主業突出、集聚程度高,是杜集“一體兩翼”園區經濟最大的特點。以礦山集為例,既有具有塊狀經濟特點的58戶家庭織布企業,也有啟鑫工貿這樣投資上億,十萬紗錠的精紡規模企業。礦山集街道辦事處主任劉峰告訴《決策》:“2010年底,紡織工業園精紡產業可以做到40萬紗錠,產值也將突破4個億。對于一個鄉鎮級工業園來說,紡織這一塊我們就是全省做得最大的了。”
而2009年4月,規劃面積達到43平方公里的段園工業集中區,也因毗鄰徐州的獨特區位優勢,在精密鑄造、商貿物流等產業的培育上發揮出后發優勢,“不久的將來,段園將成為杜集工業新的增長極”。
基層轉型:從拆掉一堵墻開始
杜集轉型,似乎發生在不經意間。
從幾家工礦配件企業小打小鬧,到引進10家投資過億的大企業、大項目,杜集用了5年;從2006年捉襟見肘的4400萬地方財政收入,到實現“錢袋子”翻三番過億,杜集用了3年時間;從全區23家規模以上企業,到2009年底的119家,杜集也只用了3年時間。
任何一個區域,在其工業化道路上,會有鮮花和掌聲,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陣痛。對于杜集來說,土地塌陷仍在繼續,村莊搬遷工作不是一日之功;開發區建設土地征遷帶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隨時都有可能將杜集的主政者推向“火山口”。
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從來都是一體兩面,不可能孤立求解,更不容偏廢一方。區政協主席歐陽林芝,這位杜集轉型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回頭看這幾年,杜集這一路著實不容易”。采煤塌陷的壓力、征地壓力、轉型壓力,都在倒逼著杜集在社會治理上尋找新的突破口。
2007年,杜集區小村并大村,在調研過程中,區委書記顧文發現,85%的群眾上訪都是采煤塌陷村莊搬遷引起的。“這其中,90%的上訪是因為我們的干部工作沒有做到位,政策沒宣傳到位、沒執行到位,矛盾沒化解到位”。走了許多村之后,她發現凡是村級黨組織凝聚力強的地方,百姓上訪就很少。
社會治理,特別是信訪工作,以前過多地強調鄉鎮和區一級的作用,然而,有了村一級“隔熱層”,鄉區兩級都無法準確感知民間冷暖和百姓訴求。社會治理必須沉到底層,而基層突破尤須以村為主,為民服務在村、矛盾化解在村。
然而,從實際情況看,村一級又恐難當大任。傳統的“官本位”思想,讓村干部都把自己當成了村官,圍墻一拉,門鎖一掛,村部儼然成了“衙門”,哪里還是給百姓辦事的地方?
拆掉圍墻,建開放式村部,讓村干部能為百姓辦事,并能辦得成事。區里將建設開放式村部的試點任務交給了高岳鎮雙樓村。
2008年2月的一天,雙樓村新建村部大樓外,很多人見證了這一時刻。拆除圍墻的時候,村民帶著不解的眼光,村干部帶著不舍的眼光,他們都在觀望,這一“儀式化”的動作后面還會有哪些實質性的舉措。
很快,每一個村部的公共活動空間,都安裝了一組健身器材,十幾米高的廣場燈亮了,村部有了黨員活動室、圖書閱覽室、為民服務代理室、文體活動室、計生服務室,連警務室都沉到了村一級。
沒有了圍墻的村部,門不上鎖,百姓自由進出,村部成了人場,村干部感覺有凝聚力了,老百姓覺得有歸屬感了。記者在仁莊村和雙樓村與村民座談,大家普遍反映為民服務代理室真正能給百姓辦事。據雙樓村民王淮北回憶,他最近一次來村部辦事,是辦身份證。“我就帶了幾張照片到村部,村干部幫忙填好一張表就行,證件辦好,還有人送上門”。辦身份證、辦土地流轉有代理服務,甚至連信訪、上訪也能代理服務。
村部不僅成了為民服務中心,也是村民娛樂中心。春節期間,每一個村部都組織了迎春活動,拔河、球賽、文藝演出,村民說,“幾輩子也沒見這么熱鬧過”。
杜集的基層轉型,是從拆掉一堵墻開始的。顧文感慨地說,如果中國最基層的政府都能把圍墻打掉,那才是真正的和諧。關鍵是,我們有沒有打掉圍墻的勇氣和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