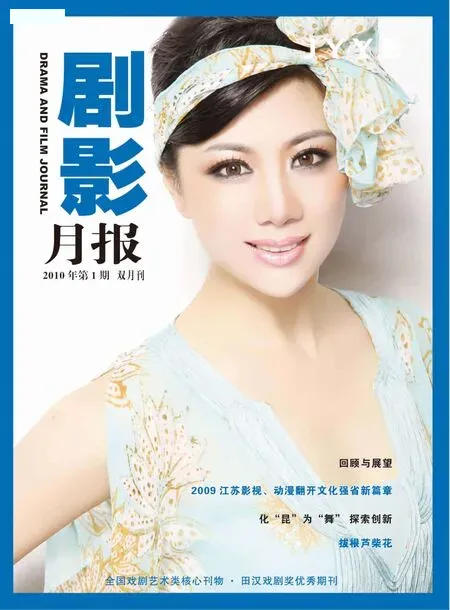試論《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中民族調式的運用與發展
■許揚寧
許常惠(1929-2001),臺灣彰化人,是臺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在推動現代音樂創作方面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之一。在創作上,他強調中西結合,并致力于創作具有現代風格的中國音樂。在具體實踐中,大量采用民族調式是其創作中的主要特點之一,因此,本文分析其第一首采用民族調式的作品,通過對這首作品的研究,試圖掌握許常惠早期的調式處理技法特點,同時也為他中期以后的作品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1958年創作于巴黎,歌詞取自詩人陳小翠為女兒所寫的抒情詩,編制為長笛、女高音與鋼琴三重奏。這首被許常惠認為是其創作起點的作品。全曲共37小節,3/4拍,bE大調調號記譜,由鋼琴左手的華彩音型開始,伴隨著右手的五聲性旋律,一小節后長笛以be2-f2-b1的音型進入,作為引子的呈示(譜例一)。
譜例一:《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1-4小節

在鋼琴的華彩音型上,特別強調六度加半音裝飾:作品開始處是一連串填充于C與bA之間的半音音型,持續四拍后向上大二度模進進行展開,這里作曲家刻意將音型組與拍號錯位,產生重心游離的效果。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第8小節,盡管曾在第5小節改變了一次旋律進行方向,但織體與音程結構基本不變。
鋼琴右手特別強調純四度的關系,第一個和弦是很明顯的,而第二個和弦則是ba大三和弦與以bb為根音的純四度疊置三和弦疊加而成,它直接陳述全曲的和弦結構并具有三、四度疊置以及附加音的特性,偏離功能和聲的規范。在引子的陳述過程中,華彩音型不斷出現bA持續音,鋼琴右手在第5至第6小節停在ba1這個變徵音上,以中國調式體系而言不會在此停留。同時,左手分別在第4與第8小節反復強調bd以離開調性,加上長笛一開始的陳述雖是從bE調的主音開始,但卻立即用三全音以模糊調性,這些都暗示了調式是建立在bA宮系統上,并非根據作曲家定的調號使用bE宮系統,如此就能解釋歌曲中作曲家運用的諸多變音現象。
第9小節是引子的總結部分,這里確立了bA宮系統:鋼琴的華彩音型轉變為bA宮系統五聲音階下行,織體也改用鄰近音級相互交替,最后停在f小三和弦上,長笛則補充了三小節,于第12小節結束在f羽上。女高音在第10小節,以重疊方式從ba1進入,陳述第一個樂句。
女高音進入后反復強調小三加大二度,是典型的五聲性旋律,分為兩個樂節,3+4前長后短的非方整性結構,樂句停在第16小節的f2,羽調式。鋼琴在12小節以純四度疊置的柱式和弦結構進入,輔以f大三和弦以及省略三音的c大七和弦,相當于f羽調式的主與屬七和弦,具有較強的和聲動力。17到24小節為第二樂句,長笛強調c2-be2小三度,女高音主題采用第一樂句的移位加節奏減值,與第一樂句構成平行關系。本樂句出現的變化音除了19小節女高音、22小節長笛以及女高音bg外均可視為和弦外音,這音被放置在重要而明顯的位置上成為調式轉換,由f五聲羽調式轉換為f七聲燕樂羽調式,是燕樂的閏音。鋼琴織體改為流動性較強的琶音,并自18小節起左手加入主屬持續音至整個樂段結束,使得調式轉變的過程中雖出現許多變化音,仍為羽調式色彩。
25到37小節為第二樂段,女高音主題根據第一樂句進行音程擴充以及節奏減值發展而來,這里僅將原主題中的ba1改成了c2。第一樂句情緒激動,速度加快超過一倍,經過一個小節長笛的短小引子后女高音在第26小節進入,以第一樂段兩個樂句的骨架為主體,濃縮結合而成。32小節女高音轉換為清樂音階,仍是bA宮系統,f七聲清樂羽調式。接下來交由鋼琴補充一小節轉換情緒,35小節進入第二樂句,速度還原。
鋼琴聲部在第二樂段中延續引子的音型,但節奏放大了一倍。右手采用引子素材,以純四度疊置弦連續展開,形成一個由c1開始,上行進行到f3,再折返至F的峰形旋律,只有在29小節三連音的過程中有一個經過式的減五度以及35小節F與臨時變化音還原B形成的三全音,其余的緊張度一直保持不變;左手部分也是根據引子中的華彩音型展開的:25小節保持小六度加半音填充,26到30小節則是利用小二度裝飾bA宮系統前三音級,成為bA-bB-C-bA的一連串展開(譜例二),減五到純五交替出現,形成全曲中最強的緊張度。
長笛聲部從25小節進入,以五聲性旋律進行半音裝飾。自27小節起,聲部中開始出現bg的等音#f,調式從f燕樂七聲羽調式逐漸過度到由其它聲部確立的清樂羽調式。
譜例二:《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25-27小節

這個樂句結束的部分長笛與其它聲部的關系很特殊:33小節通過長笛的不協和音使樂句延續了一個小節。
35到37小節為最后一個樂句,這短短三小節的樂句相當于是全曲的尾聲。
首先,女高音其實是前樂段第二樂句最后部分的倒影,再補充一個純四度上行,結束在bb1商調式,是第一樂句第一樂節主干音的集合;長笛是闖入終止,運用半音對f進行裝飾,最后下行純四度停在c1上;鋼琴由一個附加純四度的f小三和弦開始,加入了雅樂變徵音以避免過多的平行八度所產生單調感,同時,運用一次增八度碰撞改變和弦內部的緊張度,但并未確立新調性,仍為f羽調式。全曲最后結束在以c為根音的純四度疊置三音和弦。
整部作品的創作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旋律寫作采用傳統聲樂的寫作原則,歌唱性強,即使采用大跳也只是出現在旋律內部結構中,并作合理的解決。
2.變音體系全都能運用和弦外音進行解釋。
3.和聲的運用仍采用功能和聲中,屬音對主音的偏離與回歸以建立調性。
4.本作品采用大量的四度疊置和弦、平行進行以及專為調式設置和聲等現象,受到德彪西印象派手法的影響。
5.結構是一個復樂段結構,屬于古典曲式,即使是其長大的引子,陳述方式嚴格遵照引子型陳述方式的模式寫作。
6.在節奏方面,除了引子中鋼琴聲部出現少許的重音與節拍交錯之外,仍保持均分律動的模式。
7.采用中國七聲調式進行創作,運用保持同宮系統的調式交替手法,使全曲并無單調感。
綜上所述,許常惠在本作品的嘗試主要是在調式運用方面,這是為后面的創作所進行的準備,四年后所創作的《葬花吟》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這首作品是他至今為止最常被演出的作品,編制是女高音獨唱與女聲四部合唱,另外加上引磬與木魚兩件打擊樂器。全曲共131小節,8/4拍、中慢板。
開始由引磬獨奏一小節引入,合唱聲部自第2小節起進入,聲部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各聲部均采用同音反復、節奏固定的旋律形態,四個聲部疊置在一起,形成一片音流,作為背景;第二,和弦結構保持在純四度疊置的五聲性和弦。
女高音獨唱自第3小節進入,a羽五聲調式。與《八月》最主要的相似處在于運用民族調式過程中,強調了的變宮以及獨立運用閏音,這些都體現出根源于《八月》的調式轉換模式。此外,本作品仍繼續在調式方面進行嘗試:首先,全曲調式保持在羽調式,基本沒變化;其次,采用五度循環圈的次序向上轉調:從a羽調式開始共轉了十二個調,最后回到a羽調式上;最后,不同宮調疊置。如此一來,雖然整首作品均采用五聲音階,但并不會產生單調感。
許常惠對于民族調式方面的實驗并不只限于這兩首作品,其它還有一系列嘗試。那么,為什么他要堅持采用民族調式?1999年許常惠在香港《第六屆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上所提交的論文中提到了他由于能使用多種語言進行思考,直接影響到音樂創作,音樂母語一直是個問題。而為他提供解決辦法的首先是德彪西著名的歌劇 《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其次是巴托克《小宇宙》。他從前者吸取到音韻結合必須考慮語言的聲韻問題,后者則提供他民歌以及調式的運用。此外,在對德彪西的研究中總結了五聲音階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性,這都加深了許常惠采用民族調式的想法。最后,王光祈《中國音樂史》自序中的一翻話,更是使許常惠堅持研究民族調式的重要原因,正如同他在日記中所摘引的:“…由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以引起 ‘民族自覺’之心……。”
黑格爾在談論人創造藝術的原因時說道:“人通過實踐的活動來達到為自己(認識自己)…目的在于……在事物的形狀中他欣賞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現實。”作品必須表現出人的特質,是人化了的結果,而當作品表現出這個結果并被人察覺時,它將被欣賞。至于民族是由人群組成的具有特殊性的群體,根據它所創作的作品就需要體現其特質才能成為民族的作品,這正是許常惠堅持創作具現代性風格的中國作品的原因之一,民族調式便是他的其中一個切入點,《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正是他實現這個目的的起點。正如他在留法時期的日記中所提及,這首作品標志著其創作技術、風格與內涵轉變的轉折點,通過這部作品,他尋找到未來創作的方向。
邱坤良 昨自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
許常惠 巴黎樂志[M]臺北:百科文化公司,1982
簡巧珍許常惠先生臺灣當代音樂的貢獻—兼析其早期作品兩部[J]中國音樂,2001,(1):49-52
許常惠 我的作曲道路[C]見:劉靖之、李明主編 中國新音樂史論集—表達方式、表達能力、美學基礎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125-131
許常惠 杜布西研究[M]臺北:百科文化公司,1983
[德]黑格爾 美學第一卷[M]朱光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