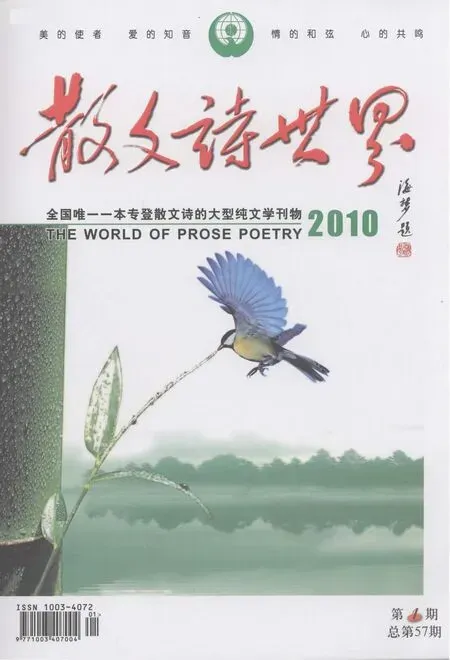稻草人站在荒野的中央
深圳 張型鋒

稻草人站在鐮刀留下的傷口上,豐收后的土地一臉疤痕。冰冷的風從比遙遠更遙遠的地方吹來,稻草人忍不住一聲聲咳嗽。他咳出的血絲像一條條蚯蚓,從他碎裂的心臟爬出,經過了干癟的喉管,在光裸的土地上蠕動,游行,爬走。
一聲聲的咳嗽,讓他的胸膛響起雷聲的轟鳴,他的思念像閃電一樣劈開夜空。她在哪里熟睡,夢見白云一樣飄過村莊的羊群;她又會在什么時候醒來,在清晨的薄霧里,頭戴一頂竹篾斗笠,踩過一片輕軟的草地,露水打濕了她自己編做的草鞋?
稻草人站在荒野的中央,他的眼睛是昏黃的燈盞,像在風中搖曳的昏黃燭光。稻草人一聲低沉的嘆息,熄滅了滿天跳動的星火。萬籟俱寂,連自詡“為土地而歌”的四腳蟋蟀,都悄悄藏起了草葉的豎琴。稻草人關閉了耳膜,他聽不到哪怕是一粒芝麻大小的聲音。
漆黑的夜,是一塊化不開的墨。
沒有火把,更沒有燈籠,稻草人伸展著僵直的胳膊,他一動不動。他的姿勢從很久以前那個杜鵑開花的早晨,到很久以前那個螢火蟲追趕流星的夜晚,一直沒有改變。這中間又有多少個霧氣氤氳的早晨,又有多少個星光燦爛的夜晚,稻草人說不清楚。他似乎還站在青草萌發的春天的邊緣,卻已經送走了夏天之后葉落枝黃的秋天。稻草人佇立在冬的門口,在打了無數個噴嚏之后,遭遇了一場來自西伯利亞的徹骨風寒。
更大的風寒來自他的內心,稻草人站在時間的夾縫里,他無法抱緊雙肩,卻一陣又一陣顫抖。他苦苦守候著一個人的愛情。這個人是他自己,他的愛情是獨角戲。
稻草人射出思念的箭,他的箭穿行在絕望的真空里,他愛的人無法察覺。
她不知道他的冷暖。她不知道他光著的雙腳,踩著冰涼,稻草人沒有一雙紅布繡花的鞋子;她不知道他裸著的肩膀,落滿寒霜,稻草人沒有一身雙層夾棉的冬襖。
他終究掙脫不了思念的蛛網,在夢的背面,在月光的陰暗處,稻草人又一次在記憶里尋找她的歌聲。她的歌聲飽滿得像高粱火紅的穗子,粘著一朵朵野菊花的濃濃的香,飄過了三月的小河,飄過了八月的山岡。
野菊花的香味讓他陶醉,讓他沉浸在回憶里不能自拔。稻草人站在十一月的天空下,他的周圍是幾千里的孤寂和荒涼。田野金黃的地毯,早已被那些忙碌的身影卷入糧倉,這個過程快得讓人難以置信。仿佛一群饑餓的山羊,在嘴唇閉合的一瞬間,啃光了一片無邊的草原。青嫩的草,金黃的稻穗,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喊一聲疼痛,便離開了它們的母親,離開了它們因過度悲泣而聾啞的母親。土地上只有嗚咽的風,天空中只有流浪的云。
一只只飛鳥在沉悶的傍晚收緊了翅膀,它們恐懼于一場暴風雪的來臨。
稻草人慢慢老了,他的銀發一根根脫落,像一個牙齒松動皺紋深陷的老人。他的身體里再也沒有潮漲潮落,再也沒有奔涌的河流。血脈的航道久已干涸,稻草人無力挽留他的青春。他的手掌握不住正午的陽光,他的雙眼看不見夜晚的星辰。
稻草人站在荒野的中央,周身充滿了渾濁的霉味。他聽到了皮膚爆裂的聲音,他身體的長城就要坍塌。一片掌形的枯葉終將把他覆蓋,一朵六瓣的雪花終將把他埋葬。沒有葬禮,沒有人在風塵中向他祭拜。稻草人只能用淚水來淹沒自己。
滿世界血紅的淚滴,是他一生不堪承受的思念;滿世界血紅的淚滴,是他一生未得啟齒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