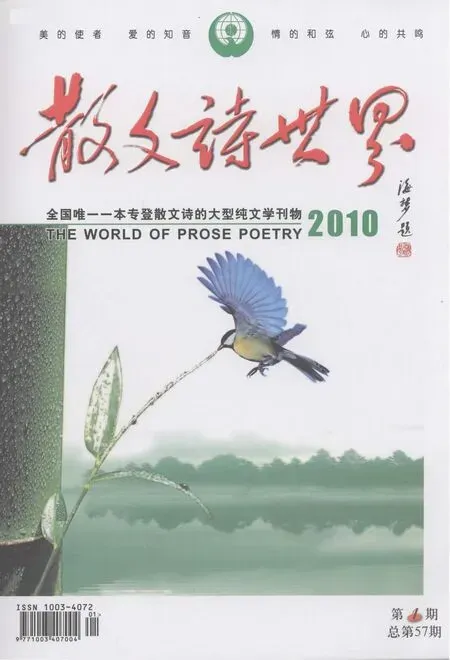風從故鄉吹過(六章)
貴州 胡 潔

古西堡
風從唐朝都城長安吹過去,吹過元朝城垛的豁口,吹過改土歸流的大明江山……
古西堡,一首石頭上爬滿青苔的頌歌,一闋蠻荒邊鄙的斷章,捧在掌上我熱淚成行。
風四季拍打著透明的翅膀,飛了那么久,那么遠,又回來喚醒這荒寂中沉睡的土地。
站在古西堡,我無數次遙望,后面是堅硬的大山,前面是柔軟的大河,掛在山腰的幾截古驛道,是來去與生死的圖騰。
回望棲居的家園,我多想做一任土司。但,不要衙門,衙門會擋住仰望大地的眼睛;不要衙門,衙門會捂住傾聽民謠的耳朵;不要衙門,衙門最容易誤解歷史的良知。
我不要權杖,不要威嚴,只想把千年的歷史牽回來,拴在粗壯的梧桐樹上。
沙家屯
烽火遠了,硝煙散了。
垣墻倒了,野草枯了。
銹跡斑斑的刀刃,千瘡百孔的彈痕,我們腳踏手摸的,是刀槍與象形文字刻畫的歷史。
雷聲動天,鐵蹄四起,土司最遠的疆土在哪里?
云過山梁,火棘紅透,我們最后的防線在哪里?
大山啊,請告訴我,我攀爬的姿勢,是否像只尋找歷史的螞蟻?我不愿退下的神態,是否像個執拗堅守的兵卒?
沙家屯,這個永無退路的關口——每一捧泥巴都是墳土,每一塊石頭都是墓碑,每一寸高度都是生與死的距離。
落日蒼涼,暮靄沉沉,夜露四起,我們退出的,是歲月與風雨放逐的天地。
歸來吧,早已化作齏粉的青石,我愿你心懷綠草、樹陰、山花和頌詞。歸來吧,遠去的白馬,我愿你馱著花朵、蜂蝶、蜜糖和幸福。
一切了無聲息,只有馬場大河裹著蒼茫的暮色一路前行,一路散播醒魂的稻香。
洗馬河
水從山澗跌落,碎了又愈合的那塊碧玉,是洗馬河。
不用遼闊的版圖,不用寬廣的河床,一條山谷就打開了你樸素的夢想。
春芽、夏花、秋果、冬雪,纏繞著彎彎山道;晨曦、夕陽、流云、鳥影,鋪滿淺淡的心湖。
這涓涓流水,喂飽了干涸的田野,浸透了九月的稻香,滋養著古樸的村莊。
握一粒不死的柴火,洗馬河澄澈的水,洗過星星和弦月的水,照見你不滅的心燈,引你一路前行。
黃昏了,暮靄里松濤陣陣,獨唱的漢子唱敗了歲月。月落了,繡花的女人繡出了心花。
洗馬的人老了,去了遠方。洗凈的馬飛了,去了天堂。
洗馬河,沉靜的水啊,我躬耕、吟詠、浴魂,一只最美的馬蹄印在心上。
松林坡
那不是松樹,是人的忠骨。
那不是紅土,是鮮血的凝塊。
那不是楊梅,是火紅的心愿。
松林坡,松濤如海河呼嘯,紅土似烈火燃燒,楊梅像不死的火種。
1950年3月20日清晨,七十多名解放軍戰士遭到十倍于我的土匪伏擊。戰火、硝煙、血腥、悲壯,撕碎了寧靜的黎明。松林坡上,光榮犧牲的28名解放軍戰士,站成一片千年不倒的青松。
我看見滿坡的樹把根箭一般插進大地,一群人隱身進了歷史的冊頁。漫山的楊梅熟透,生活的味道那么甜蜜。
懷念吧,懷念一棵青松和它體內生銹的子彈,你的痛才能接近和平。
聽聽那槍聲,這響亮的鞭炮,主持了一場最隆重的葬禮——屬于大多數人的正義,將永存于大地上!
小鎮馬場
一冊散落在丘陵上的史書,馬場大河讀得熱淚盈眶。
一匹馬帶著雪花飛,帶著黑夜飛,帶著希望飛。深深淺淺的蹄印,鋪滿長長短短的民謠。
陽光中那些青瓦,月光里那些桂花,歲月中傳唱不衰的花燈調子,紛紛從夢中驚醒。
曠野站滿莊稼,院壩擠滿糧垛,桌上擺滿酒碗,秋天讓你毫無防備醉倒在大地上。
鐵匠鋪的爐火越燃越旺,鐵砧上的鐵器越錘越硬。
豆腐坊的石磨越轉越圓,磨槽間的日子越流越長。
年邁的母親擠在菜場中間賣菜,除去泛黃的菜幫,抖掉蔥根的泥,上稱的重量才坦然舒心。她發稍的白,是我心底的霜。
鳳池書院和志勵學堂的書聲穿街過巷,爬上翠云山頂摘下剛升起的啟明星。寫春聯的老者,還在寫他的“春滿乾坤福滿門”。
馬幫馱著金黃的谷子過去了,馱著苦澀的鹽巴過去了,馱著嘹亮的山歌過去了。只剩下山風,不動聲色地撫摸這安詳的村莊,打開那宿愿的榮光。
馬場大河
站在大河岸上,沐浴氤氳的河霧,我知道,水是多么令人回味的瓊漿。
烏蒙十萬大山,鼓動著十萬條脈搏,我的母親河,你是動脈中晝夜兼程的那一條。
想昨天,水拍船沉,多少眼眶擠滿眼淚和凄愴。而今一橋飛跨兩岸,強壯的肩臂扛著平安與和諧的希望。
每個田壩的稻香麥浪,每個渡頭的聚散離合,每一聲切切的呼喚,每一次斷腸的回望,你默不作聲凝固在窄窄的地圖上。
月亮落進山坳,想挽住你的臂膀。你卻邁步向前,往晨曦泄漏的地方尋找生命的渴望。母親河,每一次跋涉打開一片新的輝煌。
秋天已經到來,越走越瘦的水在我的故鄉徜徉。它們悄悄起飛,遷徙往云朵之上。
如果我失眠,是去岸邊撈失眠的月亮;如果我沉睡,已守住浪尖金色的陽光。
去吧,有去時的沉寂,有來時的澎湃,才有一條河流永不屈服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