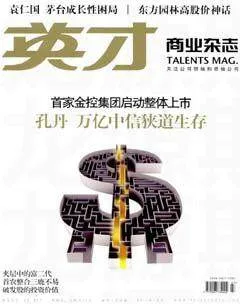北京最大的農業國企掛牌一年張福平 整合三鹿不容易
文|本刊記者 羅影/圖|本刊記者 梁海松
“整合三鹿”成為首農集團掛牌一年來的大事:拿到了廠房、設備、人員和部分渠道,但整個市場的恢復要從頭來。
也許,對于北京首都農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首農集團)董事長張福平來說,上任一年中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以至于對于首農集團已經掛牌一周年這件事,張福平有些“詫異”。
2009年5月,北京市國資委下轄的三家涉農企業——三元集團、華都集團、大發畜產公司聯合組建了首農集團,成為北京最大的農業國企,原三元集團董事長張福平出任首農集團董事長。
從三元到首農集團,張福平保持著一貫的低調作風。即便是當年置身競爭激烈的乳業戰場的三元股份,在三聚氫胺事件中獨善其身、進而做了一次“蛇吞象”的震驚業界的收購后,張福平口中依然沒有豪言壯語。“那時候,有媒體報道說我要做第三,其實是記者領會錯了。我說的是,歷史上我們曾經是第三。”他字斟句酌地向《英才》記者解釋。
其實,在張福平眼中,銷售額的差距并不代表一切,對于始終被賦予“保證首都食品安全”使命的首農集團來說,市場份額或許并非其首要考慮因素。
“三元模式”
“三鹿事件之后,有一點更加明確,沒有自建奶源的企業是沒有前途的。”看清楚這一點,張福平更加把自建奶源作為重要戰略。
與中糧提出的“從田間到餐桌”相似,首農集團沿襲了之前三元的思路,也在倡導“從牧場到餐桌”的經營理念。
以乳業為例,首農集團擁有從奶牛育種、奶牛養殖、飼料生產、乳品加工、物流配送到銷售等一整條產業鏈,甚至還有動物防疫體系。“產業鏈完整,整個流程可控,才能保證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的產品是安全的。”張福平解釋,正是出于對食品安全的考慮,三元才一直堅持全產業鏈模式。
其實,做全產業鏈成本高、投入大,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說,并非效率最優的模式。根據國際乳品協會的統計,在乳制品產業鏈上,奶牛養殖、乳品加工、乳品銷售三個環節的投入比通常為7.5∶1.5∶1,而利潤比卻為1∶3.5∶5.5。
由此可見,如果只做乳品加工和銷售,利潤更高。2008年三聚氫胺事件爆發之前,中國大部分乳品企業正是這么做的。而風險最高、投入最大、利潤最低的奶牛養殖環節,則被拋給了農戶。三聚氫胺事件之后,“公司+奶站+農戶”的模式暴露出致命弊病。散養的奶牛,喂養不科學,防疫不到位。此外,農民自己把原奶送到奶站,又增加了一道不安全因素。而自建奶源以保障質量的方式,則被業界稱為“三元模式”。
不過,自建奶源并非適合所有企業。據東方艾格高級乳業分析師陳連芳介紹,其實在三聚氫胺事件之前,有不少區域性乳業品牌也有自己的奶源,像濟南的佳寶乳業、福建的長富乳業等,“區域性品牌大多加工規模有限,在當地自建奶源基本夠用。而像蒙牛、伊利這樣的企業,他們的加工規模實在太龐大,沒有可能自建那么大的奶源基地。”
與三元在北京市場上主打的巴氏奶不同,伊利、蒙牛、光明在乳品領域的主打產品都是常溫奶。雖然后者的營養價值不如前者,但由于目前中國的冷鏈系統不夠完善,導致運輸方便、便于保存的常溫奶占據了乳品市場65%的份額。這65%中,又有50%-60%被伊利、蒙牛兩家瓜分。如此龐大的產能規模,自建奶源的確難以保證原料供應。
不過,在2009年修訂的乳制品工業產業政策出臺后,“乳品企業必須有40%可控制奶源”的規定,讓所有的乳品企業都必須花心思建立自己的規模化養殖場。
“三鹿事件之后,有一點更加明確,沒有自建奶源的企業是沒有前途的。”看清楚這一點,張福平更加把自建奶源作為重要戰略。目前,三元的奶源有80%來自自建基地。張福平計劃,在未來3-5年內,在建設自有奶源方面投資15億元。
對于那些準備采取“三元模式”的同行,張福平的忠告是:“堅持全產業鏈模式,一要耐得住寂寞,不能被市場的變化所動搖;二要舍得投入,不能因為產業鏈前端周期長、見效慢而減少投入。”
“投入多、見效慢”的確讓三元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屢受批評。
整合三鹿
“整合三鹿”被張福平視為首農集團成立一年來的一件大事。
“投入多、見效慢”的確讓三元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屢受批評。收購三鹿的案例最為典型。
“三鹿的核心資源都被三元收購了,此外,三元自己還投入了很多營銷費用。但2009年整個河北三元的銷售才6個多億,相對于三鹿原先的一年40億的銷售額,實在太說不過去了。”行業分析師的話直接而尖銳。
實際上,當時收購三鹿的決定也曾讓張福平忐忑。但如同三元集團此前的很多戰略一樣,經濟效益可能并非是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三聚氫胺事件后,三鹿的工廠停產、工人下崗、協議奶農的奶沒人收,情況很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最主要的是讓職工先上崗。”張福平總說,“三元是站在行業的角度來做這件事的。”
當然,收購三鹿對三元本身來說,也并非毫無經濟效益。三元原先的主要市場是北京及周邊地區,而三鹿在全國十幾個省都有銷售渠道;三元原先的產品重點是液態奶,而三鹿的奶粉、特別是嬰幼兒配方奶粉,曾在市場上占據半壁江山;最重要的是,三元一直長于源頭控制,營銷是短板,而三鹿正相反。“收購之后有個明顯的變化,以前我們只在北京電視臺做廣告,現在則要到很多其他省份的電視臺做廣告了。”

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完美的互補。但真正做起來,并不是那么容易。“整合三鹿”被張福平視為首農集團成立一年來的大事:“我們拿到了廠房、設備、人員和部分渠道,但整個市場的恢復要從頭來。”
對于張福平來說,收購三鹿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作用:等來了試點股權激勵機制的時機。張福平知道三元與伊利、蒙牛、光明等同行的差距,很大部分在于缺乏激勵機制。但要想在集團內部推行股權激勵,需要“等待適當的時機”。
于是,收購三鹿之后,三元成立了幾家分公司,并開始在這些分公司里試點激勵機制。“國有股占51%,個人股占49%,個人是要拿錢的,完成任務有獎勵。比如上海分公司,銷售團隊的骨干并不是自己培養的,而是市場化招聘的。有了激勵機制,分公司剛成立半年,銷售收入就達到了5個億,今年計劃要做到10多個億。”
這種在其他企業再正常不過的激勵機制,此刻讓張福平興奮異常,因為解決痼疾的曙光終于乍現。5年前,三元曾經進軍過上海市場,但終因虧損過大而退出。而現在,實行了股權激勵的新上海分公司,成了集團的銷售楷模。
“大首農”方式
未來三元乳業在首農集團里所占份額大約為1/3,另外的大部分份額則是用其他產業填補。
在營銷環節,三元正在逐步與市場接軌,但這并不意味著三元的發展將從此大幅提速。“其他幾家的所有環節都市場化了,但我們不打算這樣做。食品行業是一個良心行業,首先得保證安全質量。所以,在源頭的環節,我們寧可速度慢點。”張福平說。

張福平:“堅持全產業鏈模式,一要耐得住寂寞,不能被市場的變化所動搖;二要舍得投入,不能因為產業鏈前端周期長、見效慢而減少投入。”
中國乳業看起來處在超高速發展的軌道中,但這種發展是粗放的、非常規的。“利益鏈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乳品行業將在相當長時間內處于一種低水平飽和的狀態——永遠徘徊在人均一年消費30千克左右的水平上,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陳連芳感嘆道:“這本來應該是一個朝陽產業的,現在搞得像夕陽產業了。”
要擺脫這種困境,或許大力發展其他業務是一種不錯的方式。在張福平的規劃里,未來三元乳業在首農集團里所占份額大約為1/3,另外的大部分份額則是用其他產業填補。
目前,首農集團在奶業、養豬業、養鴨業、養雞業四方面都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產業鏈。產業布局分為農牧業、食品加工業和物產物流業三大板塊。
在張福平的計劃中,首農集團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頗多。最現實最容易操作的是建立農產品交易市場,“類似山東壽光素材集散中心的模式”,其目標是在北京的5環到6環之間,建設8-10家交易市場和物流配送基地。
其次是在種植業上下文章。其實,首農集團不光在畜牧業上擁有無可爭議的優勢,在農產品種植上也有鮮為人知的優勢。一直以來,三元堅持操作培育高端產品的企業,在蔬菜種植方面,其培育技術和管理經驗,高于一般的競爭對手。為了揚長避短,首農集團計劃進軍安全有機的高端蔬菜市場。
糧食種植也是首農集團下一步要進入的領域。同樣,張福平并不打算做大面積的普通種植:“一般農民能做的事情,我們就不做了,我們要做高端的、能體現科技含量的事情。現在中國很多農作物的種子都被外資壟斷了,比如大豆,而這個本來應該是我們的優勢。”目前,首農集團正在同北京大學未名凱拓農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合作,力求在糧食育種方面做出成績。
僅僅是首農集團手里的土地資源,就讓人艷羨:首農集團目前擁有3萬多畝基本農田,還有一些一般農田、國有土地總面積達十幾萬畝。
“一年以來,我們做了各種計劃和報告,畢竟,走路先要看清方向。”張福平并不是一個急于收獲的人:“現在的首農集團,各方面來看都處于投入階段,未來幾年內會有不少大項目上馬。我們計劃用5年左右的時間,做成一家年銷售額300億的企業。”
張福平坦言,成立一年的首農集團,跟競爭對手相比還是有差距,不過“自己跟自己比,是上了一個大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