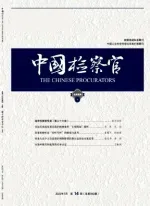檢察機關與非法證據排除
文◎謝佑平
檢察機關與非法證據排除
文◎謝佑平*
一、《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頒布的意義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賦予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資格,并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規則及操作規程。該規定的出臺,對于完善刑事證據制度,強化人權保障,提高偵查起訴階段的法治化水平,實現司法公正以及落實國際性公約的相關規定等都有重大意義。
(一)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防止冤假錯案,實現保障人權與控制犯罪雙贏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是對公民身體健康和人身自由的直接侵犯,將“棰楚之下”獲取的虛假證據作為定案依據,不僅冤枉無辜還會放縱真正的罪犯。非法證據排除可以對偵查人員起到阻嚇作用,從源頭上減少乃至消除偵查人員非法取證的動機,規范取證行為,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究,有效防止刑訊逼供和冤假錯案的發生,實現人權保障和犯罪控制的雙贏。
(二)有利于彰顯程序公正,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公正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不但侵害公民的人權而且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使社會民眾對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產生質疑,損害法律尊嚴和司法權威。西方國家一般采用聽審程序排除非法證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師可以親自參與程序,能夠對排除非法證據的結果直接產生作用,參與聽審程序能夠增強當事人對程序結果的認同感。正如貝勒斯所言:“各方一旦能夠參與到程序過程中來,就更易于接受法律結果,盡管他們有可能不贊成判斷的內容,但他們卻更有可能服從它們”,[1]程序公正的實現有利于樹立司法權威,維護法治尊嚴。
(三)有利于完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為刑事訴訟法修改奠定基礎
《規定》明確規定了證據排除的范圍以及具體的排除程序等,為排除非法證據提供了明確的適用依據。該規定的出臺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并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奠定相應的基礎。
(四)有利于落實國際性公約的實施,實現相關制度的國際接軌
目前,我國已經簽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簽署和批準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以下簡稱 《禁止酷刑公約》)。《規定》明確規定以刑訊逼供等方式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定案證據與 《禁止酷刑公約》“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的規定相契合,將國際性公約中規則轉化為我國的法律,有利于落實該規則的實施,實現我國刑事司法制度與國際社會的接軌。
二、我國檢察機關與非法證據排除
根據《規定》第3條規定,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階段有權依法排除非法證據。“這與我國檢察機關承擔的訴訟監督職能是相適應的。將非法證據的排除提前至審查批捕環節和審查起訴階段,對于盡早發現和糾正偵查中可能出現的錯誤,及時維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偵查監督,避免冤假錯案,意義重大。”[2]據此,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環節,應當依法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切實擔負起法律守護人的角色。
(一)檢察機關是排除非法證據的當然主體
首先,根據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對偵查機關活動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對偵查階段獲取的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是檢察監督的應有之義。檢察機關“對于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不僅有權監督而且有責任防止非法取證行為”。[3]發現和排除非法證據并不是偵查監督的宗旨,通過監督制約偵查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才是監督的最終目的。換言之,通過審查證據的合法性,發現并確定非法取證行為的存在并予以排除、追究非法取證主體責任,減少甚至杜絕非法取證行為是檢察機關偵查監督權的完整體現。
其次,檢察機關的職權如公訴權在性質上屬于訴訟請求權——提請審判機關予以裁判的權力。但部分權力,如作出不予批捕和不予起訴的決定同樣具有實體性效果,能夠對犯罪嫌疑人的實體權力產生直接的影響。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有助于檢察機關做出準確的決定,科學合理的決定程序的進展,避免因程序的不當推進侵害公民的權利,還可以節約司法資源。
最后,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15條的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于“任何訴訟程序”,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兩個階段,理應適用該規則。此外,聯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第16條規定:“當檢察官根據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者認為其掌握的不利于嫌疑犯的證據是通過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權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過拷打,殘酷的、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或以其他違反人權辦法而取得的,檢察官應拒絕使用此類證據來反對采取上述手段者之外的任何人將此事通知法院,并應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確保將使用上述手段的責任者繩之以法。”[4]更是明確了檢察機關在排除非法證據中的重要地位。
(二)排除非法證據是強化法律監督、降低起訴風險的重要途徑
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對于偵查機關的違法行為,檢察機關通常采用發出糾正違法意見書或違法通知書等強制性不足的方式進行監督,導致監督的效果不盡如人意。根據新的規定,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中發現的非法證據檢察機關應當排除,不得將其作為批捕和起訴的根據,這一強制規定勢必促使偵查機關轉變辦案方式,依法收集證據。另外,當檢察機關作為追訴機關行使公訴權時,檢察機關負有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舉證責任,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中提出的關于證據合法性的質疑,檢察機關負有證明該證據合法的義務,這促使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就需要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爭取在審查起訴之時就將非法證據預先排除,避免在庭審過程中陷于被動地位。
(三)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是確保審判質量的必然要求
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目的不在于為了排除而排除,而在于阻斷非法證據信息與事實裁判者之間的聯系,使事實裁判者對案件結果的認定免受非法證據的干擾。由此之故,非法證據排除效果的優劣取決于事實裁判者與非法證據接觸程度的輕重。達馬斯卡認為“在二元法庭,法官可以通過預審,裁定將不可采納的信息阻擋在事實認定者的門外,是不可采但其他方面卻可信的證據不在事實認定者的頭腦中留下任何印記——假設法庭的這兩部分相互間實行聲音隔離的話。相反,在一元法庭,雖然同樣是由個體決定證據的可采性和證據應有的證明力,但卻無法避免被禁止但又有說服力的信息的污染。它總是要對裁決者的思想產生影響。”[5]在美國,非法證據排除的后果是該證據不能進入庭審,不得被事實裁判者(陪審團)看到和聽到,能夠真正起到排除證據的作用。在德國,被排除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由于該證據依然包含在卷宗中,事實裁判者仍然可能受到該證據的影響,非法證據排除的效果遠不及美國。[6]
我國的法庭審理模式屬于一元法庭模式,法官集事實裁判與法律裁判于一體,非法證據進入庭審程序難免使法官受到干擾,影響法官在庭審中的判斷。賦予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過程中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資格,將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之外,法官根本無從接觸該證據,可以避免法官遭受誤導、影響實體裁判結果,實現審判的客觀公正,確保審判質量。
三、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設計
《規定》明確規定審判機關在非法證據排除過程中應當通過專門的聽證程序進行判斷和決定,并對法官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操作規程予以明確和細化。對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具體的程序性規定則相對粗疏,導致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過程中排除非法證據缺乏可操作性。我們認為,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中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亦需采取聽證程序,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程序的啟動與初步審查
《規定》僅規定庭審中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是被告人,對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環節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則語焉不詳。我們認為,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環節,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方式有兩種:一是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請啟動。檢察機關受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請之后進行初步審查,如果能夠明確認定合法性有異議的證據并不是非法取得,可以直接對批準逮捕和起訴的事實進行認定;如果對證據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舉行專門的聽證程序進行判定。二是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檢察機關在審查過程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產生懷疑時,可以依職權啟動聽證程序。也可以直接將該證據排除,不作為批準逮捕和起訴的根據,如果偵查機關對此提出異議,檢察機關經過審查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舉行聽證程序。
(二)排除非法證據的聽證程序
在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過程中,檢察機關通過初步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偵查機關用于申請批捕和檢察機關用于起訴的證據是非法取得的,應該舉行專門的聽證程序對存在質疑的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判斷和決定。
首先,參與聽證程序主體的角色分配。“程序是一種角色分派的體系。程序參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職,互相之間既配合又牽制,”[7]作為一種司法性程序,聽證程序的參加者至少需要三方主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且三方之間的關系類似于控、辯、審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相對于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而言,檢察機關具有中立的地位,偵查機關則類似于控訴方,犯罪嫌疑人類似被告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對偵查機關獲取證據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偵查人員應當證明有異議的證據具有合法來源,如果無法證明證據的合法性,偵查人員就要承擔證據被排除的不利后果,而對證據合法性的最終認定以及是否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均屬于檢察機關的權限。
其次,證明責任的分配。在刑事訴訟中,一般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自己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明責任。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仍然應該由追訴機關承擔,即偵查機關應該向檢察機關證明其取證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就應當認定該證據是非法證據予以排除。這是因為:一方面作為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的偵查機關的舉證能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望不可及的,另一方面刑事取證行為給公民帶來的威脅比一般國家行為更大。至于《規定》關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規定,我們認為不屬于證明責任的分擔,而是為了更有力的反駁對方,被告人需要做的準備,“是當事人行使辯護權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8]
最后,聽證程序的具體運作。排除非法證據的聽證程序實質上是一種司法性程序,具體而言是由相對中立的檢察人員主持,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師共同參加,并圍繞有異議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質證的程序。偵查人員對證據的合法性承擔證明責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就偵查人員的證明進行反駁,在質證的過程中,雙方可以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然后由檢察人員在聽取雙方陳述,核查雙方提供證據的基礎上認定證據的合法性并作出是否排除該證據的決定。
值得一提的是,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應該將排除的非法證據單獨存檔備案,不得同其他證據一起移送到審判機關。防止非法證據在法官頭腦中留下印記,無形中被作為定案的根據,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流于形式。
(三)建立和完善聽證程序的配套制度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目的的實現以及聽證程序的順利推進需要從程序上預防和控制偵查機關的非法取證行為,還需要從實體上懲戒非法實施偵查行為的主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理想效果的實現離不開相關制度的配套運行。
首先,律師幫助權和沉默權的確立。賦予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等階段擁有律師幫助權以及沉默權,完善辯護制度,不僅可以保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確的運用和聽證程序的順利推進,而且可以遏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從程序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其次,程序性制裁機制的完善。在西方國家,非法證據的制裁機制一般包括排除規則、對非法取證人員的內部懲戒和民事賠償責任的承擔,排除規則的適用更多的是對偵查機關整體產生效果,如果在適用排除規則的同時配套運行內部懲戒機制或者民事賠償責任制度,將制裁落實到非法取證的個人,制裁的直接性將能夠更有效的遏制非法取證行為。
最后,救濟程序的確立和完善。作為一種司法性程序,聽證程序應當具有可救濟性,當事人對非法證據排除與否的決定不服時應該有權獲得救濟。具體的救濟方式可以參照不批準逮捕和不起訴的救濟程序,即偵查機關可以要求復議、復核,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可以在申訴過程中提出審查要求。
注釋:
[1][美]邁克爾·貝勒斯:《法律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張文顯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頁。
[2]卞建林:《鑄證據基石,促司法公正》,載《法學雜志》2010年第7期。
[3]楊玉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在中國確立問題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3期。
[4]張智輝、楊誠:《檢察官作用與準則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頁。
[5][美]米爾建·R·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李學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頁。
[6]參見鄭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頁。
[7]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頁。
[8]樊崇義:《只有程序公正,才能實現實體公正——學習“兩高三部”頒布的“兩個規定”》,載《法學雜志》2010年第7期。
*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