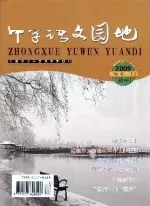淺談聯想的創造性和規律性
石文虎
聯想也是一種想象,是由此事物想到彼事物的想象。此事物與彼事物在自然關系上并不相聯、相通,聯想卻能超越事物客觀的間隔或差距,將它們組合為一個整體,這就明顯體現出聯想的綜合創造性。運用聯想,如同插上了彩色的翅膀,能使文章為之生色。但是,聯想并非自由散漫的“飛翔”,在寫作運思時,聯想的“自由”建立在對審美對象內在必然規律(即本質、意蘊)的認識基礎上,大都要受意旨控制。誠如康德所言:想象是“自由的”,但又是“合規律性的”。聯想的“創造”,不是天馬行空般的放肆;聯想的“規律性”,也不是作繭自縛般的拘謹。這就是兩者的辯證關系。
一、在時間、空間相距遙遠的事物上發現“相近”
你乘坐的列車呼嘯著駛過南京長江大橋,眼望著水勢浩淼的長江,想起當年乘輪渡過江的艱難;你走進剛剛對外開放的“水立方”,凝視著一池碧水,想起獲得八枚北京奧運金牌的菲爾普斯;你復讀一年終于考取了理想中的大學,看見父母喜極而泣的樣子,想起去年落榜時流下的眼淚……這些都可以說是聯想,只是這樣依循事物原有的淺表的相互關系而生發的聯想,是大家都容易做到的,在寫作中,并不能幫我們打開思路,進入一個廣闊的新天地。
晉人陸機說:“精騖八級,心游萬仞。”這是何等的氣魄。也就是說,上下五千年,剖析歷史,縱觀宇宙,宏觀的世界,微觀的內核,無一不可發揮你的聯想。
高中語文教材曾選過秦牧的著名散文《土地》。作者對著眼前的土地沉思,想到兩千多年前晉公子重耳逃亡途中的故事。風塵仆仆的一群貴族斷了糧,向路遇的老農要食物,老農撿起一個土塊給他們,重耳大怒要鞭打老農,一位大臣說,這是天賜的土啊,是國土的象征。重耳就下跪,鄭重地接過那個土塊,祈求上蒼保佑他有朝一日回國掌權。這是時間聯想。作者又想到保衛著海島也建設著海島的解放軍戰士。一座小島孤懸在茫茫大海中,只有石頭,沒有泥土。戰士們回家探親時,都從家鄉帶回一包土,積少成多,這樣他們就在島上栽起了花,種起了菜,使荒涼的海島變得滿眼蔥綠,花團錦簇。這是空間聯想。作者還想到歷史上許多保國守土的故事,現實中許多開發、美化大好河山的故事,還有當年一些華僑背井離鄉時帶著一捧“鄉井土”的故事。一篇文章就是由這樣許多的時間聯想和空間聯想串成。作者稱他的聯想,是騎著思想的野馬奔馳,隨時可以放韁馳騁在廣闊的時空,又可以收韁回到現實。敢于“放韁馳騁”,其實就是在時間、空間相距遙遠的事物上發現“相近”,從而把本來互不相干的若干事物自然而有機地聯系了起來,真可謂“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而圍繞著“土地”進行的廣泛聯想,不僅有力地表現了珍愛土地、保衛土地、改造土地和建設美化土地的主題,更使作品的意蘊深沉豐厚,給人一如乘船出海,愈行愈深、愈遠、愈廣的感受。
因此,我們要引導學生,寫作運思時不為此時、此地、此事、此物、此人所囿,努力往與此相距“遙遠”而又“接近”的事物上聯想。我們在多大范圍內認識了事物的時、空關系和屬性上的聯系,我們的聯想區域就有多寬,我們的創造性就有多大。
二、發現不同類事物之間不尋常的共同特征
不是著眼于事物在時、空位置上的接近,而是著眼于不同類事物在性質、特征上的類似,這種聯想俗稱相似聯想。相似聯想的基礎在于發現不同類事物之間的共同特征。在寫作中,越能夠發現事物之間不尋常的共同特征,越能夠產生新穎的創意。
如大家都熟知的《白楊禮贊》一文,作者看到白楊樹在北方風雪的壓迫下能夠傲然挺立,枝枝葉葉靠緊團結,對抗著西北風這種特征,便聯想到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堅強不屈的北方農民和守衛家鄉的“哨兵”;借禮贊極普通而又不平凡的白楊樹,以歌頌中國人民的精神和意志。“白楊樹”與“北方人民”是不同類的,但二者在本質上都有樸質、堅強、上進的共性。正是發現了這不尋常的共同特征,作者才可以由此及彼托物寄意。
再如,一位身患絕癥的病人經過手術終于延續了生命,主治醫生吐了一口氣,在手術紀錄上滿意地畫了一個圈。雖然這個圈標志著病人重新獲得生命,但就圈本身的形態與生命之間卻處于一種 “漠不相關”的形態。有的作者或許會細膩地描寫等候在手術間門口的人群的臉色、神情、言語,以及護士興奮地傳出的消息、隨之而帶來的氣氛的改變等等,這樣的描寫顯然吃力而笨拙,且了無新意。在一部電視劇中,我們看到過一個成功的細節:那正是表現了一個關及多人情感的嚴重手術成功的一剎那,手術室大門緊閉,擠在走廊里等待的人一片焦灼。已經到了該做完手術的時間了,等待的人群看著手表,神色緊張。突然,從不知哪間產科病房里,傳來一個新生嬰兒的啼哭聲,肅穆而緊張的氣氛一下煥釋了。劇作家以一個生命的降生,來比喻手術病人的復生。
在這里,嬰兒的啼哭聲已升騰為一個生命的符號,它的聲音形態與它所象征的意義之間的共同特征便是“新生”。觀眾通過相似聯想,一聽便能領會劇情所遞送的符號信息的抽象內涵。把它比之于有關醫生在手術紀錄上畫一個圈的描寫,比之于對那些等待人群的細致刻畫,我們不難體會到相似聯想的創造性魅力。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不妨說,許多新鮮的比喻、精彩的象征,常常就是相似聯想的機智運用。
在一些記實文章中,同樣可以運用聯想把此事物與彼事物聯結起來,拓寬思路,深化主旨。有一篇人物通訊,寫大慶的一位女工數年如一日照顧因公傷失去雙臂的丈夫。作者在充分描述了這位女工對工作的熱愛、對家庭的奉獻和賢惠以后,又展開這樣一番聯想:
這位大慶婦女,不知她姓甚名誰。但卻是那樣熟悉,好像曾經相識,啊!我想起來了……
抗日戰爭的時候,不正是你,為子弟兵推磨壓碾,在磨道上,你邁動纏過的小腳,你白發飄飄,你年行數千里,你碾的細面,喂過千萬抗日大軍。這是你?這當然不是你。那時候,暴風雪還在這草原上肆虐橫行,大慶的石油還在地層深處埋伏,你這女兒,也還沒誕生呢,可是,多么神似。
解放戰爭的時候,不也正是你,牽著馬,馬上騎著披紅掛綠的未婚夫,沒過門的媳婦送郎參軍。你強壓住亂蹦的心,驅不散臉上的紅云,你仰頭對馬上的人兒說:“你去打敗老蔣,家里的事有我來……”沒過門的姑娘,把根大辮子挽成一個不聽話的髻,把他的媽改口叫“俺娘”。這是你,這當然不是你。大慶的女兒,那時你才四歲呢,可是又多么像你。
很顯然,作者從這位大慶女工身上發現了中國勞動婦女共有的特征:深明大義,堅忍勤勞。于是通過聯想,把這位大慶婦女與革命戰爭中的母親、妻子的形象合為一體。這樣,人物的事跡不再局限于本身,而是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意義,主旨也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三、揭示互相對立的事物的個性特征
如果說相似聯想主要著眼于不同事物之間的共同特征,對比聯想則是由一事物而聯想到與之有對立關系的事物,揭示互相對立的事物的個性特征。
唐詩“霜葉紅于二月花”,可謂膾炙人口的名句。詩人運用對比聯想,把存在對立關系的秋天的紅葉與春天的紅花聯袂成詩。“紅于”二字表明,在詩人的主觀世界里,秋風熏陶的楓葉比春雨滋潤的鮮花更紅、更美。正是這一個性特征的揭示,一反封建文人“悲秋”的傳統,唱出了一曲高亢的秋色贊歌,表現了詩人獨特的美學觀和藝術創造精神。其中的哲理意蘊,更激人聯想,發人深思。
現在的熒屏上,表現婚姻倫理道德的電視劇很多,十分熱鬧,卻鮮有創意。有一個電視小品也寫了這么一個短暫的婚姻,篇幅不長,沒有對話,卻讓人耳目一新,久久回味。這對戀人在處于熱戀階段的時候,他們一次次在一條幽靜的長巷中散步、道別,每一次,都遇到一對相扶相持的盲人夫婦,點著竹竿走過。年輕的戀人毫不在意,只是偶爾投去憐憫的匆匆一瞥。不久,經常互相道別的大門口貼上了雙喜紅字,盲人夫婦似有所聞,微微一笑,竹竿點著爆竹的殘屑走過。以后,不知為什么,年輕夫婦煩惱了,反目了,最后,無可挽回地走向離異。在一個凄涼的夜晚,他們在深巷相背而立,決定各奔東西。這時,又傳來篤篤的竹竿聲,盲人夫婦相扶相持,淺笑連連。這對年輕人似有所悟,第一次那么專注、那么認真又那么感慨地注視著這對盲人遠去的背影……
這個電視小品連年輕夫妻離異的原因都沒有講清,更遑論評判雙方的責任和是非了。編導似乎對此沒有太大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運用對比聯想,展示兩種人生情感方式一次次巧遇的場景。藝術意蘊,就在這一組組個性特征鮮明的場景中浮現和升騰,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效果。
對比聯想的創造性,在中學生議論文寫作中也有廣泛的體現。有一年全國高考,作文題是“樹木·森林·氣候”。有一篇滿分作文,考生聯想到幾天前結束的世界杯足球賽,指出阿根廷隊奪冠并非馬拉多納一個人的功勞,在于他們有一個堅強的群體,形成了一個足球的“森林”,從而改變了球壇的“氣候”。而中國足球隊也有球星,但沒有形成足球的“森林”,因此也就改變不了“氣候”。由于鮮明地揭示了有對立關系的事物的個性特征,結論也就水到渠成:要形成“森林”,改變“氣候”,需要一定的條件,這條件就是重視和普及。文章通過對比聯想針砭我國的足球問題,反映出當代中學生視野開闊、思想活躍、創造性強的特點。
有一則材料作文,大意是:一位山東老漢在買了一張車票后,又掏出50元錢補了兩張票。他說,25年前,帶老伴到臨沂城里看病,錢用光了,回家時,乘車沒有買票。改革開放后,農民有錢了,他應該把當年欠的車錢,補繳給國家。
絕大多數學生都圍繞“誠實”擬題,大談“誠實是中華民族的美德”。這樣寫,固然沒有偏題,但內容毫無新意。筆者指導學生運用對比聯想,細讀材料,揭示老漢的“個性特征”。學生終于注意到材料的關鍵句是“改革開放后,農民有錢了,他應該把當年欠的車錢,補繳給國家”,從而發現老漢的個性特征是“不忘本”,是“心里裝著國家”。由此聯系社會生活,往相反的方面聯想,一些借改革開放的東風富起來,而今卻偷稅漏稅的老板、大款,便在老漢的對比映照下,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可見,對比聯想有助于學生開拓思路,關注社會,針砭時弊,提高思維品質。
四、情感的能動與情感的定向
聯想以記憶為基礎,卻要以情感為動力。記憶和聯想猶如種子與花朵,春種秋收;情感則如左右收成的氣候。在生活的旅程里,江河湖海,花鳥蟲魚,紛繁復雜的事件,各式各樣的人物……全都像一顆顆種子,撒在人們大腦的地壟內。氣候適宜,記憶的種子會迅速地發芽、開花,在作者的意識世界里,構成一片聯想的百花園。
秦牧的《土地》發表于1960年。那時,國外濁浪排空,國內天災人禍,海峽對面更叫囂著“反攻大陸”。正是對祖國大地、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無限摯愛的情感激流,觸發了作者豐富的聯想,筆觸所及,時而古,忽而今;方論華夏,頃即域外,思接千載,情系大地,沒有一點故作姿態的虛假,完全是激情不可抑制時的自然迸發,火熱心懷的真誠袒露。
茅盾在望不到邊際的黃土高原上,看見在西北極普通的白楊樹,會覺得它不平凡,進而聯想到樸質的北方農民、守衛家鄉的哨兵,以及他們的精神和意志,是因為他對抗戰圣地延安懷著美好的憧憬,對 “磨折不了,壓迫不倒”的抗日軍民,充滿了敬意和深情,“讓那些看不起民眾、賤視民眾、頑固倒退的人們去贊美那貴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頎的),去鄙視這極常見、極易生長的白楊樹吧,我要高聲贊美白楊樹!”
當然,情感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鼓舞、感動、憤慨、悲傷、震驚……都可以成為催生聯想的能量。只要有情感對知覺、對記憶的沖擊,就會產生聯想。相反,一個作者如果情感貧乏、內心冷漠,即使他大腦的地壟內撒滿了記憶的種子,也不能開出燦爛的花朵。
聯想的展開總是朝向預定的目的。一方面,它是“自由”的,寫作時,憑借著對事物本質特征的認識和把握,我們可以“自由”地聯想到許多有聲有色的意象形態。另一方面,由于情感的能動作用,一定的情感、情趣表現在作品中構成著聯想的目的,這就突出了情感(情趣)為聯想定向的功能特征。
梅花的習性是冬天開花,它本沒有什么感情、節操,只是自開自謝,自枯自榮。可是,當我們賦予它人的情感時,它便成為花中的偉丈夫。這一意象形態,顯然是由不怕嚴寒的本質特征決定的。然而,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因情感、情趣的定向,梅花的意象形態又各具特別的意蘊。郁郁不得志的陸放翁聯想的是“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懷著革命樂觀主義,聯想到“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飄零異鄉的愛國華僑,則由梅花聯想到“美麗的赤子之魂”……
同是寫茶花,楊朔由茶花之美麗可愛,聯想到育花的勞動者,以最大最美麗的童子面茶花象征祖國的未來,辭采動人,極富情韻;鄧拓則從茶花的來源、品種、特征,聯想到古人歌詠茶花的詩篇和凄婉動人的民間傳說,贊頌茶花秀艷與高尚的品格,知識廣博,涉筆成趣;而李華嵐通過詩意的聯想,借助高山飛瀑、麗日深潭、九天織女等鮮活的意象,著力描繪茶花之美色,在充分鋪墊的基礎上,讓讀者想到特別輝煌的生命來自特別辛勤的努力的主題內涵。
同樣是散文,楊朔把散文當詩寫,他的聯想充滿詩情畫意;鄧拓為文有其學者風格,他的聯想平實而豐富;李華嵐的散文詩在文壇獨樹一幟,他的聯想往往通向哲理。可見,不同的情感情趣,調節掌控著作家的聯想,既表現出作家富于個性的創造,又體現出他們將自己的想象限制在特定軌道中運行的規律。
總之,在聯想生展、飛躍的每一步,任何一個事物都可能與許多事物發生聯系,但為什么此物與特定的“彼物”而不是與別的“彼物”相聯結,這正是情感、情趣的定向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