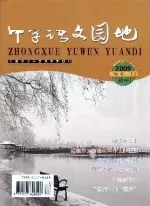淺談銜接教育與作文評價對高中作文教學的影響
廖文紅
不可否認,高中作文教學是困擾語文教學工作者的難題之一。可是,我們是否能冷靜下來想一想,究竟是學生不愿寫而又不得不寫所以敷衍成文,還是他們真的不能領會命題人的用意所以不會寫因而勉強成文?
我想,作為一個中學生,他不可能對這卷面分值百分之四十的作文等閑視之。那么,中學生是不是真的不愿寫呢?看看他們的周記吧。作為一個中學語文老師,說實話,我真的不愿意看中學生的大作文,但倒是非常愿意看他們的周記:敘事,有板有眼,具體生動,老師視之,也常常眉開眼笑地向同事復述之;抒情,則發其并不成熟之情,懵懵懂懂,小心眼的誤解、學業繁重的牢騷、成長過程中杞人憂天的煩惱、情竇初開的迷惘等等,老師視之,或為之喜或為之愁。一句話,敘真事、抒真情、說實理——彼處花不開,此處卻綠柳成蔭。
我們再拿去年江蘇省高考作文題 《懷想天空》為例。懷想,《現代漢語詞典》注釋為:懷念。所以,這個題目從表層含義理解,應該理解為“懷念天空”。這個內容從語法結構來看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如果從情理角度來說,可能就有點“說不清”了,因為我們平常所說的“懷念”的對象,我們的學生一般都理解為是曾經存在而現在不存在的、對某個個體有著某種特殊意義的某個人或者物,即某個具體的“人”或者是“物”。“天空”顯然不是。那只能把“天空”抽象化,然后“隨物賦形”把它具體化。如果要把“天空”具體化為某種思想精神、興趣愛好、生活空間,那就基本符合題意了。可是,我們有沒有想到,對于一個中學生來說,這個思維過程未必有點“苛求”了。錢理群教授指出:“……有一個時期,我們又用‘文學家’的眼光去看待‘語文’,文學欣賞成了語文閱讀課的全部內容,作文教學實際上是要求學生按成年人,甚至作家的方式寫作,而完全忽視了對學生作文基本功的訓練。 ”(《何為“語文”》,載《語文學習》2007年第6期)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此。
中學生為何畏懼寫作?原因很復雜。單純從寫作教學這方面來說,我感覺到存在著教學過渡中缺乏有機的連貫性與評價方式的一致性。我們都知道,不同區域或者不同的學校的語文老師在具體的作文教學過程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小學、初中、高中各個階段的老師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學生,按照自己的標準去評價學生的作文。比如說,高中階段對學生的作文要求,由初中階段要求敘清一件事,一下子上升到“透過現象看本質、揭示問題產生的原因、觀點具有啟發作用、材料豐富、形象豐滿……”不錯,我所說的是作文發展等級的要求,可是我們的老師在評價學生的作文時,又何嘗不是從高一開始就用這樣的標準呢?
從學生的學習時間安排上看,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高一學年是高中階段最為繁重的一學年。九門課加上英語口語、體育一樣都不能少,而這一學年,又是語文教學特別是作文教學的一個重要銜接與轉化過程,學生沒有更多的時間坐下來讀書、思考,沒有更多的時間練習寫作,如何寫出“深刻、豐富、有文采、有創新”的作文來?作業任務繁多,在學生看來,作文又僅是作業的一項而已,學生匆匆忙忙,又如何不草草了事?過了高一再來說作文銜接,為時已晚。帶來的一個事實便是,有眾多的中學生,他們的作文水平還僅僅是停留在初中階段,連同他們初中階段在作文中使用的例子、引用的語言、列舉的人物都是一樣,甚至有可能倒退!
再說我們的評價方式。同樣類型的作文,在初中時可能會有一個不錯的分數,而到了高中,可能就會被打入三流作文,挫傷了學生的信心;同樣是寫作,認認真真寫作的得分有可能還不如馬馬虎虎應付之作,有學生的原因,也有我們老師的原因;說假話大話空話的作文有的是,裝上一張面具,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成年人去說教也很多,而我們的老師對這部分作文的態度是什么?如果縱容之,完全不顧那面具底下發出的稚嫩的聲音,本質上我們老師是不是在教學生撒謊騙人?我想,高考作文常出現被閱卷老師視作為 “品德低下”甚至“惡劣”的撒謊作文也就不足為奇了。
語文老師也很無奈,因為我們不可能要求學生放棄繁重的作業而整天捧著名篇名著去 “愉快閱讀”,我們不可能讓學生在一周僅有的一二次自習課時到閱覽室去。但我們可以嘗試在銜接教育與作文評價方面作出我們的努力。作為初高中的銜接教育很重要,這段時間可以清楚地告訴學生,三年后他們應該達到什么水平,要想達到這個水平,他們平時應該做些什么,高中階段作文要求學生寫什么、怎樣寫以及以怎樣的標準去評價。我是這樣要求學生的:
一、寫真事,說真話,抒真情
圍繞一個“真”字做文章,而且利用作文評價明確這種導向。讓學生明白作文其實很容易,就是寫出自己日常所見、所思、所感而已,引導學生去觀察生活、體悟生活,只有生活,才是寫作真正的源泉。其中一個方法是,把大作文周記化,讓學生把周記與作文結合起來。對于多數學生而言,作文訓練的目的,僅僅是教會他們說清自己想的內容,在這個基礎上再講求思維的嚴謹,講求一定的文采。
作文的方法技巧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相對于內容而言又是次要的。作文有法,但無定法。而且,形式方面的東西是靠積累獲得,是要靠他們在不斷的閱讀體悟中,根據自己的愛好去挑選、模仿、運用的,老師說這個好,但于某些學生而言它偏偏就是不好——不喜歡!所謂的“個性化”,是與千篇一律為敵的。高考作文要求“個性化”,而個性化是教不出來的,非得要學生自己去閱讀、思考、體悟方可。現在的作文評價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形式至上的導向,我覺得這很危險,正如錢理群教授說的那樣,我們千萬不能——其實也不可能——讓每個學生都要成為作家。用名家名著的標準來要求學生,我們老師自己做得到嗎?
二、鼓勵閱讀,引導學生閱讀經典,培養多思的習慣
時間有限是事實,我們要關心學生在極其有限的時間里讀什么。要注意的是,千萬不要讓學生對閱讀產生抵觸心理,特別是在高一的時候。先把要求降低,先從閱讀有趣的作品開始——哪怕是從《伊索寓言》開始也行,只要學生能夠讀出新意來,也要比聲稱讀過這個那個名家的名篇,但讀完什么都沒有留下強得多。嚴格的要求是慢慢達成的,只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
從讀書的范圍來說,教師也不必作過多的限制。比如說一些武俠類、言情類,消極的、積極的,知識類、娛樂類……,只要健康的就行,但有一個條件,讀過之后要有所得,并形諸文字。如果實在沒有時間,我們的語文課不就是時間嗎?少說一點語言知識我看不會失去什么。沒有什么可看?我們的語文課文、讀本中的文章,都是專家幫我們精挑細選的,都是精品所在,為什么不能讀?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老師自己也應該多讀書。學生對老師讀什么書是非常在意的。我不止一次觀察到我的學生在我不在教室的時候,紛紛走到講臺邊翻看我讀的書。過不了多少時間,我發現有好幾個學生也買了那本書在讀了。
平時,我們還應該有意引導學生閱讀經典。經典既是民族與人類文化的結晶,也是語言藝術的典范,它代表一個時代人文和語文的頂峰。引導學生閱讀經典,讓他們“享受那種對最微妙的細節、最隱晦的暗示、最輕柔的韻味”而帶給他們“心領神會的特殊的幸福”(赫爾曼·黑塞《我最愛讀的書》,楊武能譯,《讀書》1990年第12期)。多讀經典過程,“是使閱讀者經歷一番文化濡化的過程,它可以改變人的氣質”(劉夢溪《今天為什么還要閱讀經典》,《中華讀書報》2003年11月26日)。
三、客觀評價
在一開始評價學生作文時,一定要善于發現每個學生作文中的閃光點,并鼓勵其保持、完善。不能因為作文整體的思想性不高,或者作文技巧不成熟,或者沒有寫夠字數,或者書寫不規范而打低分,從而打擊他們的信心。甚至可以根據某個閃光點打高分。充分肯定學生的個性,但一定不能讓學生任性。歸根結底還是那句話,要求是要逐步達成的,教師只能逐步引導學生去貫徹要求,不能一開始就讓那些條條框框把我們的學生死死地束縛住。
老師閱讀學生作文時認真與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千萬不要用分數去打擊他們的積極性。不要吝嗇筆下的分數。當然,我們下筆打分時還應該客觀公正,不能隨心所欲地亂打一氣。高分應該有高分的理由,哪怕只是一兩處有閃光點;低分也應該有低分的理由,一切都應該從學生能夠接受的角度出發。
學生平時很重視老師給的評語,如果沒有評語,他們會覺得老師根本沒有看,如果他自己事先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寫作,結果老師沒有看,那下次作文還會認真去寫嗎?另外,老師的評語確實對他們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我注意到,每次發下作文本后,學生總是那么聚精會神地看老師給的評語。我們怎么能馬虎待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