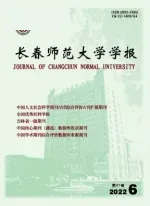略論3-6世紀北方社會習俗對疫病的影響
王 飛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吉林長春 130012)
3~6世紀北方地區疫病頻繁暴發,對當時社會各層面都帶來了嚴重的影響與沖擊。對于導致疫病頻發的因素,已有學者作以探討考察,但這些學者大都關注這一時期政治局勢、軍事行動以及自然災害對于疫病的影響,而對當時社會習俗對于疫病所造成的影響卻鮮有研究。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北方社會習俗對疫病的發生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的習俗可能會加劇疫情的傳播與蔓延,有的習俗甚至會直接導致疫病的發生。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的民眾衛生情況、飲食習慣及喪葬習俗等社會習俗對疫病所產生的影響作以初步探討。
一
首先對當時民眾衛生情況對疫病的影響作以考察。現代醫學知識告訴我們,民眾的衛生條件和習慣對預防傳染病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民眾的衛生條件主要與兩方面因素有關,一是個人洗沐情況,二是民眾所處的生活條件。我國古代民眾的洗沐習俗,在秦漢時期已初步形成。彭衛先生在《秦漢時期洗沐習俗考察》一文中指出,“考察秦漢時期的洗沐習俗,由其洗沐方式和盥洗設備可看出洗沐已成為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這是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1]但這種生活習慣當指社會某些特殊群體而言,尤其是指有條件的社會上層,而漢代是小農的汪洋大海,對于這些小農而言,由于生活條件的限制,個人衛生條件一般不會太好。王充在《論衡·解除篇》中指出:“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可見普通百姓身上生虱子是比較常見的。不僅是普通百姓,就是一些上層人物身上也會因沐浴少而生虱子,如《風俗通義·過譽》記述東漢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趙仲讓“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魏晉南北朝時期,沐浴習俗可能較漢代更為普及,特別是社會上層對于勤沐浴之習可能更為普遍,如《南史·梁本紀下》載南朝梁簡文帝撰寫《沐浴經》三卷。但對于廣大普通民眾而言,由于生活條件的限制,能真正做到經常淋浴的人恐怕為數不多。殷偉、任玫著《中國沐浴文化》一書在《魏晉南北朝貴族沐浴奇習》中也認為條件優越的沐浴至少是中產以上的人家才可以為之,應該說是為貴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貧苦百姓是無法享受的。[2]此外就算當時的上層社會人士,對沐浴的態度與作法也不一致。如晉朝的王猛常捫虱而談,當然他不會經常沐浴。由于個人衛生條件不好,身上長有虱子等寄生蟲,這為傳染病的產生與傳播創造了條件。
民眾居住條件與生活環境也會對疫病產生影響。這一時期的人口應主要是集中在廣大鄉村,對于住在鄉村的普通民眾而言,其居住條件與生活環境都相對較差。據張承宗、魏向東在《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一書《居住與建筑風俗》中考證:“至于漢族人民,仍以住房為主。這一時期普通百姓居住的房舍,大多采用木構架結構,墻壁為干打壘的土墻,屋頂或呈懸山式或為平頂,房屋多圍成院落,內設畜欄和廁所。民間最為簡陋的住房,純為草、竹等自然材料建造,既不牢固,又低矮潮濕,居住環境十分惡劣。”[3]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普通漢族百姓生活條件相當簡陋。此外,由于其房屋多圍成院落,內設畜欄和廁所,這樣一來,衛生條件將進一步下降,這種設施會加重對生活區域的污染,從而有利于病菌的繁殖與傳播。對于北方地區的游牧民族而言,其居所以搭帳蓬為主,類似于今天的蒙古包,如《南齊書·河南傳》載:“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為貲,一謂之“貲虜”……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后稍為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對于何為百子帳,《南齊書·魏虜傳》載有“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為‘傘’,一云‘百子帳’也。”通過以上記載,可見這種百子帳的結構是比較簡單的,其并沒有專門的用于處理糞便等排污設施,因此衛生條件也普遍較差,這也利于病菌的滋生與傳播。由于普通民眾的居住與生活條件較差,尤其是衛生條件簡陋,這既會引發疫病,也有利于疫病的傳播與蔓延,如曹植《說疫氣》載“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4]此則表明生活條件簡陋的貧困之家感染疫病的機率要遠遠高于生活條件優越的富貴之家。此外,就生活條件而言,一般來說,城市內的居民生活條件要好于居住在鄉村的民眾,但在中國古代社會,城市內也未形成有效的公共衛生設施,況且城市內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動頻繁,因此城市內也往往暴發疫情。如這期間先后為國都的洛陽、長安等地區,均暴發過大規模疫情,《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載:“三年春正月戊子……京都大疫。”《晉書·武帝紀》載:“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陳書·徐陵傳》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
二
這一時期的飲食習慣對于疫病也有很大影響,如北方地區流行的寒食節。據說這是為了紀念春秋戰國名臣介子推,北方地區要絕火寒食一個月。《后漢書·周舉傳》記載:“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由此可知,東漢中期在今山西太原一帶就流行寒食這一風俗,而且是在冬天寒食一個月之久,以至于老幼體弱者多有死者。也正是因為這一寒食風俗導致有很多民眾病死,所以周舉才提倡禁寒食,用溫食。而其結果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看來周舉這種說教式方法禁寒食實際作用不太大,這一習俗并未由此而禁。為進一步禁止寒食,曹操曾下達過《明罰令》,其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子胥沉江,吳人未有絕水之事。至子推獨為寒食,豈不悖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贏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5]周舉禁寒食還只是從說教的角度,而曹操下達《明罰令》禁止寒食,則是從國家法令層面禁止寒食。由此可以推斷,這一時期的寒食不僅從太原擴大到上黨、西河、雁門一帶,其所帶來的危害,特別是對當時民眾健康的損害一定是較前更為嚴重,否則不會以國家法令形式加以禁止。但這種習俗并未因此而禁絕,十六國時石勒曾禁寒食,但很快又取消了禁令。據《晉書·石勒載記下》載:“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諛駁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冱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于是遷冰室于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通過這段記載可知,寒食這種習俗在十六國影響又所擴大,石勒雖曾下令禁寒食,但也沒能達到目的。北魏時期寒食這一習俗仍在流行,并影響很大,因此朝廷再次禁寒食,《魏書·高祖紀》云在延興四年 (即474年)朝廷下令“辛未,禁斷寒食。”但事實上,這種習俗還是有其強大生命力,并未因朝遷的一再禁止而停止。據上可知,自漢代起在北方地區就開始流行寒食這一習俗,此后直至北朝這種習俗在北方長期流行。這種習俗在寒冷的北方地區流行,必定會導致多種消化道疾病的產生和蔓延,以至于經常會有人由此而死亡,這也必然會對北方地區疫病,特別是消化系統的疫病產生推動作用。
除這一時期北方地區寒食習俗對疫病有所影響外,北方民眾的飲食方式與飲食結構對于疫病的發生與傳播也有一定影響。據張承宗、魏向東在《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一書《飲食風俗》中考證:“現在人們都習慣三餐制,但在先秦時期,先民們大都一日兩餐,以適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社會作息規律。漢代以來,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財富逐步增加,一日三餐制方才出現并逐步普及開來,但兩餐制在貧窮家庭依然存在,直到唐代以后,一日三餐制才徹底取代了兩餐制。魏晉南北朝是由一日兩餐向一日三餐過渡的時期。與一日兩餐制和一口三餐制并存一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食制與合食制也并行不悖。”[3]這一時期是一日兩餐向一日三餐過渡的時期,對于廣大窮苦之家的民眾來說,應還是一日兩餐,辛勤的勞作而只能一日兩餐,其結果是多數貧困之民會引發營養不良,從而導致這些人降低對疫病的抵抗能力。而這一時期用餐方式從分食制開始走向合食制,這種合食制則會通過食物傳播細菌與病毒,加大疫病傳播的機會。對于這一時期普通民眾的飲食生活,張承宗、魏向東在《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一書中認為,當時民眾普遍陷于貧困狀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經常性的情況。在相對安定的時期,老百姓的日子稍稍好過一點,富裕人家一年當中還能吃上幾次肉。[3]生活水平如此之低,則必會造成廣大民眾營養不良,一旦有疫情發生,這些人便很難抵制住疫病的侵襲了。
三
還一個與疫病密切相關的生活習俗就是這一時期的喪葬制度,其中尤以喪葬禮儀與葬法影響最大。漢代以來,特別是漢武帝時期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步占主導地位,這對喪葬制度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于漢代的喪葬禮儀,據徐吉軍、賀云翱著《中國喪葬禮俗》第二章《事死如生的喪葬禮儀》載,漢代的喪葬禮儀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葬前之禮。這一階段包括招魂、沐浴飯含、大小斂、哭喪停尸等項內容;第二階段為葬禮,包括告別祭典、送葬、下棺三個環節;三是葬后服喪之禮。這其中沐浴飯含要為死者沐浴;大、小斂要為死者穿衣入斂,赤貧者往往不用棺槨而以板床代替,甚至用草席卷尸;外地親屬要趕回奔喪。[6]如若死者是因染疫病而亡,那么這一系列的喪葬禮儀將成為傳播疫病的重要途徑。如為死者沐浴、入斂以及要停尸三日,這樣一來,死者會成為傳染源,而參與喪事的親朋好友則成為被傳染的重要對象。以上所言是漢代喪葬禮儀,魏晉時期與漢代基本相同。《晉書·禮志》云:“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北魏時期,雖是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其喪葬禮儀也很快漢化,沿承了魏晉之俗。對此,金愛秀在《北魏喪葬制度初探》一文中有詳細闡述。[7]事實上,以上所述的喪葬禮儀風俗也確會帶來疫病的傳播。如《南齊書·孝義傳》載:“建武二年 (495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床,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赤斑病即為麻疹,是一種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此記載雖是發生在南方地區,但這種現象在當時南北方是一致的。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小兒母是因感染赤斑病而死亡,但其死后尸體并沒有被直接處理,而是被置于其家床下,這無疑會增加周圍人員的感染機會。對于參與因染疫而亡者的喪禮會傳播疫病,這一時期的醫家已有所認識,如隋《諸病源候論》在談及喪注候時云“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住易傍人也。人有臨尸喪,體虛者則受其氣,停經絡腑臟。若觸見喪柩,便即動,則心腹刺痛,乃至變吐,故謂之喪注。”[8]此記載明確指出因染注而死亡者會死后傳染他人,特別是若人有臨尸喪,其中體質虛弱者染病的機率會更高。這也說明當時這種現象較為普遍,否則醫家不會將此種現象專例為一種癥候。
除喪葬禮儀對疫病的傳播有所影響外,這一時期死者的埋葬方法對于疫病的傳播也有較大影響。若從防治疫病的角度看,對死者的最佳埋葬方法當首推火葬。因為通過火葬,死者所攜帶的細菌或病毒都會被一同消滅。但可惜的是,這一時期僅是部分少數民族地區采用火葬方式,如《晉書·石勒載記下》:“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這說明十六國時期的羯人是采用火葬風俗的。此外,這一時期的突厥人也有火葬風俗,如《北史·突厥傳》載:“死者,停尸于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于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時而葬。”但對于人數眾多的漢族人,或是漢化了的少數民族而言,主要還是采用土葬方式,這與自漢代以來儒家思想影響日深有直接關系。儒家提倡事死如生,入土為安,但這種土葬方式實確有利于疫病的傳播。對于3~6世紀的北方地區而言,饑荒、戰亂頻繁,曹操所言“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現象時有發生,大量人口死亡后暴尸荒野,這無疑會加劇疫病的傳播與擴散。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的民眾生活條件、飲食方式以及喪葬制度等習俗都會對疫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的習俗會加劇疫病的傳播與蔓延,有的習俗則可能會直接引發疫病,因此這也應該是考察影響疫病因素的一個重要方面。
[1]彭衛.秦漢時期洗沐習俗考察[J].中華醫史雜志,1999(4).
[2]殷偉,任玫.中國沐浴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1.
[3]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23,47,70.
[4]趙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5]歐陽詢.藝文類聚: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62.
[6]徐吉軍,賀云翱.中國喪葬禮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84-85.
[7]金愛秀.北魏喪葬制度初探[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15.
[8]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二十四[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