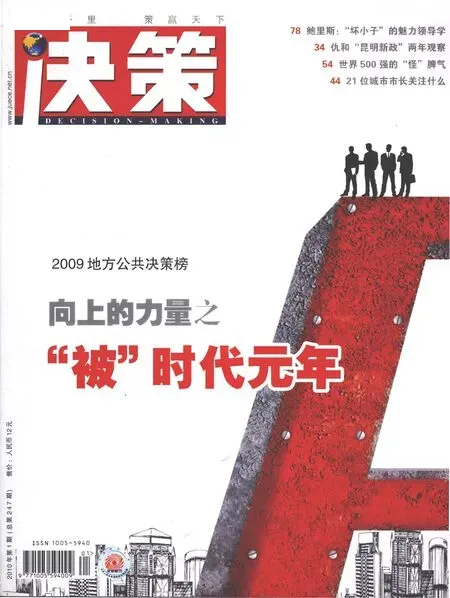伍皓探路“網絡執政”
■本刊記者 吳明華
“沉默是金,是千百年來官場總結出來的不二法寶,但我曾天真地放言,面對網絡時代,沉默是‘禍根’。現在看來,官民溝通的新路還是很艱難。”

《南方窗》“周年末》度“人年物度”人、《物決候策選》“”2、《00南9風年十大地方決策新銳人物”……2010年新年剛到來的時候,曾經在云南刮起陣陣新聞改革旋風的伍皓,似乎是“名利雙收”:不僅再度成為輿論焦點人物,而且“轉正”成為最年輕的宣傳部副部長。“試用
在期過”去的的伍一皓年,面里對,新網官絡上輿任論、事仍件處,在采取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應對手法。從“躲貓貓”事件中組織網民第三方調查,“小學女生賣淫案”親自披掛上陣參與網上討論,到創新網絡發言人制度等。使云南這個邊陲地區,一躍成為輿論關注度最高和輿
個論頭監不督高最、性活格躍率的直地潑方辣之的一伍。皓,此前做過16年的記者,對于“網絡執政”他有自己獨特的“揭蓋子”理論“:一壺已經燒開的水,如果還使勁捂著蓋子,結果只能是連壺底都被燒穿;而蓋子一揭,盡管有可能會燙著自己的手,但沸騰的民意也就會變為蒸汽慢慢消散。”
然而,伍皓“網絡執政”的一次次嘗試,在傳統思維濃厚的官場,引起了新舊思維的激烈碰撞,受到巨大的壓力和指責;而在網絡上,伍皓也同樣面臨網民們強烈的爭議和質疑。
宣傳部來了個年輕人
“很多政治經驗豐富的老領導一再勸誡我,不要在意網絡上的東西,根本不必去理會,它傷不到你一根毫毛。他鬧騰他的,你不理他,鬧騰一會兒也就沒勁兒了;你越想著要尊重他、回應他,越把他當回事,他越會瘋狂地奔過來咬你。這就是網絡,這就是網民。”
2008年底,年僅39歲的伍皓突然接到一紙調令,從新華社云南分社常務副總編調任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這個宣傳部新來的年輕人不但沒有聽從“勸誡”,反而接二連三做出出人意料的舉動。
2009年2月12日,昆明市晉寧縣看守所在押人員李蕎明非正常死亡,當地公安局把原因歸結為“與獄友玩躲貓貓游戲”發生意外。這一解釋很快在網上引發一片質疑聲,“躲貓貓”也迅速成為“第一網絡熱詞”。
“前幾天因為開會一直沒有時間上網,18號晚上會議結束后,打開電腦一看鋪天蓋地都是‘躲貓貓’。”多年形成的新聞職業習慣讓伍皓生出了強烈的好奇心,“第一反映就是宣傳部門的職責是不能讓真相‘躲貓貓’,我們要讓真相‘亮堂堂’。”
“互聯網上形成的公眾輿論,必須借助符合互聯網傳播規律的手段來化解。”伍皓突然產生組織網民實地調查的想法。當他把這個想法在QQ群里提出來后,得到了網友的一致擁護。
伍皓做事雷厲風行。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公檢法等相關部門代表開了個協調會。一開始,他的建議遭到各部門的反對,警方代表擔心這樣做會把事情鬧大不好收場,也有部門代表提議按照過去的老辦法處理。
“現在官方調查很難取得網民的信任,大家都會懷疑是你們自己掩蓋真相,網絡的事情還是用網絡的辦法來解決。”伍皓最終說服了相關部門代表。
當天下午,伍皓就在網上邀請網民參加“躲貓貓事件調查委員會”。網民的積極性超乎了他的預料,一下午就有1000多網民報名。當晚,宣傳部就從中選出了調查團名單,由4名政法界人士、3名媒體記者和8名網友組成。第二天早上,調查組即赴晉寧縣調查。
在伍皓的協調下,民間調查團順利進入晉寧縣看守所,也得到了警方“適度配合”,但檢察機關以法律禁止為由,拒絕讓他們看相關錄像和案卷。調查團只能簡單問了幾個問題后,草草收兵。隨后提交的“流水賬式”調查報告模棱兩可,沒有明確的結論,連伍皓也覺得不滿意。
民間調查的舉動,給高漲的輿情又注入了一股興奮劑。而此時網絡輿論卻急轉直下,矛頭轉向了伍皓。網民質疑伍皓此舉是官方的作秀工具,警方又指責其為干擾司法,認為他是越權、越位。兩頭不討好的伍皓,一時間遭受了巨大的壓力。
事后伍皓自己反思認為,第一次組織第三方調查沒有經驗,而且“當時確實想得也比較簡單,我覺得讓網民進入到案發現場,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能夠給社會公眾一個滿意的答復。”
雖然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但在伍皓看來,“通過這次活動,至少我們對司法部門的監督產生了效果。”
陷身“網絡江湖”
“躲貓貓”事件在真相大白后,網絡輿論才逐漸平息下來。由于云南省委主要領導在公開場合的力挺,對伍皓一邊倒的壓力也慢慢緩解,伍皓得以“全身而退”。
“如果碰到像‘躲貓貓’這樣的熱點事件,宣傳部只求自己沒有風險,明哲保身,能躲就躲,不去疏導公眾情緒,我倒覺得是最大的失職。這樣的‘太平官’我做不來,讓我去當‘縮頭烏龜’,我覺得實在有愧宣傳部副部長的職責。”話音剛落,隨后的“昆明少女被指賣淫案”,讓伍皓再次卷入網絡輿論的風暴中心。
2009年3月16日,昆明兩名小學女生因為父母故意“調包”,導致被警方以涉嫌“賣淫”錯抓。之后,媒體又因為看到作假的“處女檢驗報告”而刊登了錯誤報道。此事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受“蒙騙”的網民憤怒地指責昆明警方,從而迅速形成一場公共輿論事件。
與組織第三方調查不同,這一次伍皓選擇親自上陣和網民“肉搏”。7月初,正當網絡輿論達到高潮時,伍皓公開在網上發帖,先是點名批評記者的失實報道,接著又公布此案中警方的9大過錯。
“沸沸揚揚的‘小學生被指賣淫’事件,就像一壺已經燒開的水,揭開蓋子是我的職責所在,我應該把我所知道、所掌握的情況,盡可能地告訴公眾。”伍皓希望以平等的身份和網民進行交流。
在短短3天的網絡互動里,伍皓一共發表了6個帖子,結果不但沒有起到溝通的效果,卻引來了網民成千上萬的口水。有人覺得他是在“攪渾水”,也有人說他是“騎墻行為”、“官方行為”,甚至謾罵、侮辱的聲音也不絕于耳。
相關部門對伍皓的做法更是不滿。有人認為,正是伍皓挑起了民意的沸騰,“不講政治”和“政治上不成熟”的批評隨之而來。事后,云南省紀委、監察廳聯合調查組不僅對相關媒體給出了嚴厲的處罰建議,還批評伍皓“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建議“談話提醒”。
在各方壓力之下,伍皓無奈以沉默退場。“沉默是金,是千百年來官場總結出來的不二法寶,但我曾天真地放言,面對網絡時代,沉默是‘禍根’。現在看來,官民溝通的新路還是很艱難。”
“或許,還是選擇沉默最穩妥。”意識到“此路不通”的伍皓,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都選擇“暫時沉默”,并且在隨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保持了與新聞的距離。
2009年11月,伍皓發現了另一網絡輿論平臺,即剛剛流行起來的微博。他希望用這個快捷的渠道來第一時間公布信息。但沒想到馬上引來了網民們的非議,認為他是在作秀。最后,伍皓甚至和網民爆粗口對罵。
在網民的“窮追猛打”下,一個多月后,伍皓無奈宣布“自愿自動自殺式”關閉微博。雖然最終沒有關閉,但還是改了名,而且越來越多地記錄家庭生活、人生感悟,不談國是。
幾次網絡互動試驗的受挫,讓伍皓感受到“網絡江湖”的復雜,“也許,還是有路可走的,只是我暫時還不知道哪條路能夠走得通。我也不是一個害怕失敗的人,我會繼續試驗、探索。”
“推窗效應”
盡管屢屢去“揭蓋子”,但每次都被“燙手”。伍皓“揭蓋子”的舉動給云南官場帶來強烈的沖擊,官場對他的壓力也開始反彈。
云南有高層官員指責伍皓,“工作觀念過于超前,會把云南引入輿論災難”。因為對伍皓有“尖銳的意見”,有些領導對于是否讓伍皓通過試用期也持爭議態度,云南官場一度有傳言他會被摘掉官帽。
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伍皓手下的新聞處長曾經幾夜都睡不著,經常是很困惑,發短信問伍皓說我們是不是真的錯了。而伍皓自己也不免擔驚受怕,甚至還有點心驚肉跳,但他還是比較篤定,“我寧愿被燙手,絕不愿意被燒穿。”
“在行政系統,新任命的官員一般都會選擇四平八穩地度過第一年試用期,但伍皓在每一次突發事件中都會置身于輿論漩渦的中心,因此飽受爭議和批評。”在宣傳部的官員看來,與傳統的官員相比,伍皓顯然是個另類。
雖然有爭議,但伍皓最終還是通過了組織部的考核。2009年底,伍皓不僅成功邁過一年的試用期,還被委以重任,在原來分管新聞宣傳之外,又加上了外宣和網絡。
“進步的過程需要有人做先驅者,我可以當先驅,但不希望自己成為先烈,所以說自己要把握好度。”在伍皓看來,一個人的能力和水平就體現在對度的把握上。
“我每干一件事,看起來比較隨心所欲,心血來潮,但實際上,對上,每樣我都能夠找到政策和理論依據;對下,能夠找準老百姓和人民群眾的渴盼點,切合他們的需要。”伍皓在微博里這樣總結自己的“職場生存法則”:該裝孫子的時候就去裝孫子;隨時在上司的視線里;敬仰自己的上司。
“你不再是新聞記者,以你現在的身份,去對網友進行回應,說不定還會掀起更大的風波,引來更多的口水。有什么關系呀,網上的口水又污不了你的衣衫,愛怎么樣由他們去吧,你哪有那么多時間去跟網友打口水仗啊?”同事勸伍皓不要理睬網絡上的謾罵。
但在他看來,一個官員如果對網民的質疑不理睬、不回應,是對網絡民意的輕慢和漠視,“我不想做一個目中無網的官員。”
“為什么你與以往的宣傳部領導表現不一樣?”許多新朋舊友都奇怪地問伍皓,在他們看來,一旦各種突發事件發生、各種事件矛盾激化,宣傳部門一般都只會利用管理優勢對媒體進行壓制,或者對公眾的信息訴求進行逃避,而伍皓卻反其道而行之。
伍皓把自己過去一年中推出的改革創新稱為“推窗效應”,“好像打開一扇窗,讓清新的風吹進來,這些就可以空氣交換,而且潤物無聲。恰巧我們國家所有的改革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上級不反對或者不明確制止,就是對你的一種認可,就是鼓勵你可以去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