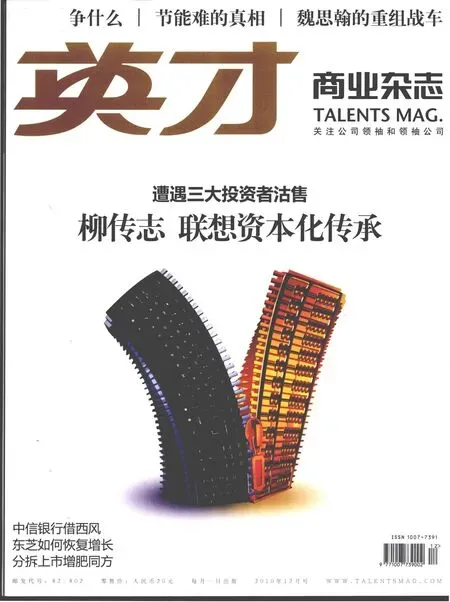柳傳志是世界級企業家嗎?
文|姜汝祥
獨立觀察
柳傳志是世界級企業家嗎?
文|姜汝祥
聯想并購IBM的PC業務,其中所經歷或所得出的“知識體系”,遠比目前很多企業的成功或失敗重要得多,而柳傳志正是對這個知識體系貢獻了大智慧的那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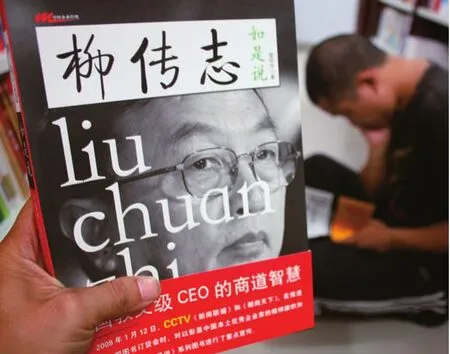
11月4日,法國里昂商學院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把“世界企業家”大獎發給了柳傳志,前兩屆得主分別是羅技公司創始人丹尼爾波里爾和日本“經營之父”稻盛和夫。
獲得這樣一個獎勵,是不是就足以說明柳傳志是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家?或者說,柳傳志能夠與稻盛和夫相比嗎?柳傳志自己對這個獎項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用“有中國特色”的語言,表明了他的態度:“這個獎項頒給我,說明了評審方對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重視。”
我覺得柳傳志獲得這個獎其實并不十分重要,因為類似的獎勵,張瑞敏、李東生們也曾經獲得過,重要的是他獲得這個獎的時間:在《時代》周刊兩次把中國工人列為年度人物之后,在中國經濟經歷金融危機的考驗之后,國際上對中國經濟泡沫爭論不休,此時,柳傳志獲得這個獎,表明了全球商界認可了柳傳志所代表的中國企業家的努力。
評審團認為柳傳志獲此獎的理由是:聯想在柳傳志的領導下成為一家國際公司,這一過程展現了柳傳志的創業能力、領導素質,以及全球視野。更為重要的是,聯想是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國企業”的一個絕佳代表。
放在這樣一個國際化背景之下,再來看柳傳志對記者坦蕩而稍顯偏執的回答,就特別值得中國企業家關注。因為國際化是21世紀中國企業最重要的主題,過去幾年我寫了很多文章呼吁中國企業家要集體關注TCL李東生在國際化中的經驗與教訓,因為李東生所經歷的是中國一流企業家未來必然要經歷的。這個結論是不是正確,對比一下日本與韓國企業的歷程就知道了,沒有國際化的本土企業,無論多么強大都會被時間淘汰,因為未來只有一種生存方式:全球化生存。
按這種邏輯,現在最值得中國企業家集體關注的,就是聯想柳傳志以及華為任正非了。聯想作為中國一流企業國際化的代表,并購IBM的PC業務,其中所經歷或所得出的“知識體系”,遠比目前很多企業的成功或失敗重要得多,而柳傳志正是對這個知識體系貢獻了大智慧的那個人。
既然如此,中國企業家陣營似乎就應當停下腳步,去思考一下問題:柳傳志與聯想的智慧之源是什么?哪些是我們可以共享的中國智慧?哪些卻只是柳傳志與聯想個別化的“藝術化”獨創。
我認為 “事業經理人”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可以共享的中國智慧之一,這個詞是柳傳志的發明,從邏輯上講,這個概念是“中西”結合的產物,這一產物讓不少本土企業家覺得“過于理想”,卻讓崇尚西方管理的學者覺得“過于中庸”。我覺得,這是柳傳志對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化的一大貢獻,因為它回答了一個問題:中國企業家靠什么動力來支撐他們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敬畏之心”與“自我超越”?
企業的業績表面上是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對商業規律與時代趨勢的把握,但在更深的層面,卻是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對自我生命的態度與認識,因為商業規律與時代趨勢是以極其困難復雜與極具權力誘惑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如何不被困難所擊倒?如何不被誘惑所迷惑?我想,只有“事業”這個包含了豐富內涵的詞,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家內心產生敬畏,敬“天命”然后方知“成事在天”。
從這個意義,我們也對柳傳志的復出有了些許新的理解,這一理解的出發點,不再拘于柳傳志本人的復出或是退出,而是從時
代的角度看聯想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如何去獲得這種包含著“天命”的“事業感”。
以楊元慶為首的聯想第二代完全可以比柳傳志更大氣,柳傳志的復出會影響,但卻并不能構成阻礙或推動這一代人成功的關鍵要素。關鍵的要素是獨立于環境的“事業天命”,正如一句話所說的:擁有使命的人,一切都會為你讓路。
這個讓路者當然也包括柳傳志本人。
21世紀既不是西方的世紀,也不是東方的世紀,而是中西交融的新世紀,在這樣一種文化大背景下,融匯了中西方特色的“事業經理人”因為中國企業而具有了國際意義。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日本世界級公司豐田創始人豐田佐吉,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韓國世界級企業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他們為什么是世界級企業家?不完全是因為企業規模,而更多是因為他們的經營智慧,代表著非西方傳統的企業走向世界級水平時所需要的“創新與突破”。
比如豐田佐吉最大的智慧貢獻是“造物即造人”,意思是造優秀產品的前提是先打造優秀的人,這代表了具有儒家文化傳統的東亞國家對“得人心”的重視,而顯然這一思想同樣為西方企業所接受與學習。
當然,在強調指出柳傳志的世界級之后,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柳傳志身上的中國特色。應當說,柳傳志身上有著這一時代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共有的束縛,那就是從計劃到市場過程中的制約與誘惑。
從聯想MBO過程到聯想的多元化投資業務結構,都有著這種時代的烙印。聯想的MBO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沒有這個MBO是無法想象會出現聯想事業經理人團隊,這是一個成功的典范,但如果說在早期是事業天命的體現,那么在后期的利益博弈過程中卻會出現對“事業天命”形成威脅。
我特別希望聯想像豐田,索尼甚至像三星一樣,專注于從業務與團隊本身去突破“天花板”。
同樣,聯想的多元化投資體系,也代表著中國市場機會的價值,這樣一個舞臺對聯想第二代領導人,并不是一個好舞臺,因為這個舞臺至少到目前為止,時興的游戲規則仍然是“資本的游戲”,而不是“客戶的游戲”,而作為一家中國一流公司的代表,聯想的使命只有在“客戶價值游戲”中才能夠完成,這就是致力于做德魯克所說的“創新的企業”。
無論豐田,索尼,還是三星,都是這一類致力于客戶價值的“創新企業”的代表,而過多的把精力用在資本層面,搞控股式多元化,我覺得那至少是一種對現實利益的“中庸”。
我從內心深處,特別希望聯想像豐田,索尼甚至像三星一樣,專注于從業務與團隊本身去突破“天花板”,即使是多元化,也像三星一樣有著明確的戰略遠景與重點。
而作為一個致力于研究中國企業發展歷程的學者,我內心深處一直有一個愿望,那就是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寫一本《改革開放的中國企業史》,那時我如何寫聯想,寫柳傳志?從這個意義上講,聯想與柳傳志更多的不是對現在的業績負責,更是要對中國企業的歷史負責,畢竟,聯想是一家參與并領導了中國企業史的公司,柳傳志是一個參與并領導了中國企業歷史進程的公司創始人。
(本文作者系北京錫恩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