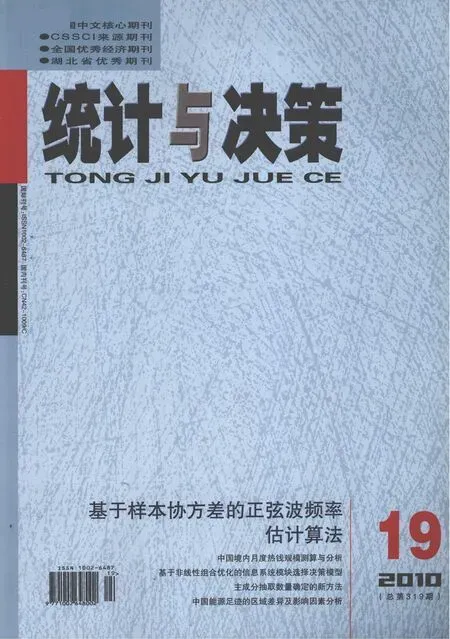加權網絡簇系數及其對集群知識創新的影響
彭 英,楊 照
(1.南京郵電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南京 210046;2.南京大學 商學院,南京 210093)
加權網絡簇系數及其對集群知識創新的影響
彭 英1,2,楊 照1
(1.南京郵電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南京 210046;2.南京大學 商學院,南京 210093)
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存在過度依賴成本的競爭,集群發展遭遇“大而不強”的瓶頸。因此,并非擁有產業集群就擁有經濟競爭力,創新網絡的形成才是集群競爭優勢的源泉所在。文章從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刻畫入手,回顧了簇系數及加權網絡簇系數的發展,剖析了集群創新優勢形成的機理;在此基礎上得出,權重知識網絡中的簇系數越大,集群創新能力越強,簇系數隨時間演化會逐步減小;最后給出了簇系數的補償策略,借以形成集群創新的持續動力。
加權網絡;簇系數;知識網絡;集群創新;BBV模型
0 引言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集群作為獨具生命力的“社會生產綜合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然而,隨著知識和信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日益明顯,原有基于空間的集聚現象已經不能單純依靠運輸成本和集聚的外部經濟性來獲得競爭力,空間集聚并不必然意味著集群區域持續競爭優勢和創新能力的產生。因此,集群創新網絡作為一種獨特的創新組織形式,由于其具有集群資源共享、知識溢出效應、成熟的創新環境、創新人才的聚集及創新風險的分散等特性[1],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普遍認為,知識是集群主體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源泉,知識網絡通過影響集群主體間的互動學習機制和集群內知識創新來形成集群的創新優勢。那么,作為集群內知識流動的重要載體,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結構怎樣?知識網絡的演化機理如何?知識網絡的演化與集群主體學習機制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將有助于集群的持續成長,對于集群提升創新能力、獲得持續競爭優勢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將通過對集群創新網絡的刻畫,借助復雜網絡理論中的BBV模型及加權網絡簇系數的演化特征,分析簇系數對于集群知識創新的影響,并給出簇系數的補償策略。
1 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界定
集群,是指某一特定領域內相互聯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機構的集合。集群是由生產網絡、社會網絡和知識網絡相互融合而成的復雜網絡結構。其中知識網絡是生產網絡和社會網絡發生和發展的積累和標志,是集群創新的重要源泉和獲取持續競爭力的關鍵。各國學者對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界定,包括對知識網絡的內涵和知識網絡的構成要素的界定。
情報學領域關于知識網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Price提出的“引證網絡”,管理學領域關于知識網絡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工業界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美國科學基金會(NSF)認為知識網絡是一個提供知識、信息的利用等社會網絡。Beckmann認為,知識網絡是進行科學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機構和活動。Kobayashi認為知識網絡是由具有知識創造力的結點的集合以及結點間的聯系所組成的系統。Coats認為知識網絡是由若干單元(子系統)構成的相互之間進行知識交流、知識供應的網絡結構體系。在歐洲創新研究小組(GREMI)的推動下,許多學者(Capecchi,1997;Cooke,1993;Saxenian,1994;Morgan,1997)開展了對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研究。Nunzia研究認為,在產業集群知識網絡中存在強聯接與弱聯接,如果企業僅僅具有其中的一種,則不可能取得很強的市場地位。Giuliani認為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節點之間的連接具有復雜性。
蔣恩堯等從技術層面將知識網絡看成一個用于解釋大量的資料與信息,記錄、包裝并傳遞專業知識給員工、業務伙伴、顧客及供應商;李丹等認為知識網絡是組織與能為其提供所缺知識的外部組織進行合作所相應構成的網絡體系;張麗妮認為知識網絡在廣義上講是指一種知識參與者實現知識在個人、團體、組織和組織間等級層次上的創造與傳遞的社會網絡;姜照華等從區域經濟角度認為,知識網絡是區域創新體系的骨架,而企業、高校、中介機構、政府等則是區域知識網絡結構上的一個個節點(單元)[2]。產業集群知識網絡構成如圖1所示。其中,U1,U2,U3…Un代表知識網絡 內 各 個 結 點 ;X1,X2,X3…Xn代表各個結點的知識 產 出 量 ;I1,I2,I3…In代表各個結點接受網絡外知識輸入量。

我們認為,集群創新系統中的知識網絡是用以描述集群內主體之間知識活動關系的一種復雜網絡結構。知識網絡的構成要素為知識、知識主體和知識活動。在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主體一般包括生產商、批發商、運輸商、零售商、消費者、公共服務機構、代理機構、政府、大學、科研機構等。知識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系形成了知識網絡。隨著知識網絡的演化,集群內部的知識主體的學習機制得到發展,二者之間相互促進。
2 集群知識創新的機理
Saxenian通過對硅谷的研究發現,知識網絡的發展促進了集群的創新。Kabecha研究了肯尼亞的集群創新系統發現,以中介組織為核心的知識網絡更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技術進步。Vonortas研究拉丁美洲多個國家的集群創新系統發現,政府的服務政策和措施在中小企業技術進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Yamawak和Britton分別證明了日本和加拿大產業集群內部的網絡連接,比區域間聯系和國際間交易在提升創新能力方面更占優勢。中國的學者通過對江浙、廣東等地的集群創新系統的研究發現,知識網絡有利于集群主體創新能力的提高。
集群知識學習是指知識網絡節點通過網絡關聯實現與其他節點的知識來源相連接,彌補集群知識主體的知識缺口,實現集群知識不斷擴容的過程。秦鐵輝等(2006)認為,企業作為集群知識網絡中的知識主體,其組織關聯的類型主要有五種[3]:“核心企業—相關企業”、“企業—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企業—金融機構”、“企業—中介服務機構”。集群知識網絡中的知識主體關聯關系可以描述如圖2所示。
在集群知識創新系統中,集群知識體系不是多個個體知識的簡單相加,而是它們的有機融合,這個知識活動過程包括知識擴散與知識聚合[4]。集群知識體系中的知識活動如圖3所示。在集群層面的知識網絡中,一方面,分散的個體知識通過各種網絡關聯逐漸向集群知識匯集,從而實現了集群知識的聚合;另一方面,集群知識沿著相反的方向向個體知識擴散,從而實現了集群層面的知識擴散。

眾多學者對產業集群進行研究時發現,產業集群的創新優勢來源于集群內有效的知識網絡[5~6]。集群創新優勢的形成機理如圖4所示。產業集群知識網絡通過影響集群組織間的互動學習機制和集群內知識創新來形成集群的創新優勢,而且有效的集群互動學習機制能加速集群內知識創新,集群知識創新能優化集群互動學習機制,它們彼此之間互相促進,協同發展,共同形成了集群創新優勢。

3 加權網絡簇系數對集群知識創新的影響
隨著復雜網絡理論研究的興起,基于復雜網絡的分析方法被逐漸應用到知識網絡的研究領域。復雜網絡最一般的抽象是無權網絡,Watts和Strogatz[7]通過建立W-S“小世界”網絡模型,認為較短的平均路徑長度(交流頻率)使得網絡能夠更快速、更準確地傳播信息,較高的集聚系數(交流集中度)可以促進團隊內部大量、頻繁的知識交流。Vito Latoral和Massimo Marchiori基于無向權重網絡討論了小世界網絡模型的效率和成本,為創建低成本的知識共享網絡提供了研究依據。Cowan通過建立復雜網絡上的一種知識擴散模型和一種知識增長模型,分別研究了網絡結構與知識擴散間的關系、網絡結構與知識增長間的關系[8]。國內學者李金華在W-S模型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網絡上的知識傳播模型,認為網絡的隨機化程度越大,網絡中知識的擴散速度越快,知識的分布越均勻;通過仿真研究,認為知識流動引起網絡知識同化,網絡結構取決于擇優性與隨機性兩類機制。然而,由于無權網絡僅反映節點之間的連接方式,而不能描述節點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強度,因此其模型有其局限性。權重網絡不僅更好地體現真實網絡的特點,而且反映了網絡中節點之間的相互作用細節,有利于把握知識網絡系統的復雜特性[9]。
Watts-Strongatz提出的無權形式的簇系數,總結了無向無權網絡的一些重要統計性質,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其中ki為節點i的度,ti表示節點i的鄰居節點間的實際連接數,aij為連接標志,當節點i和j有連接時aij=1,否則為0。Ci,WS∈[0,1],當節點i只有單個鄰居或鄰居間沒有連接時,Ci,WS=0,當節點i的所有鄰居節點兩兩間都有連接時,Ci,WS=1。
近年來,在權重網絡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擴展了這個概念,使其發展成加權網絡簇系數。Barrat、Onnela、Holme等人分析和定義了加權網絡的簇系數,李穩國等人提出的加權網絡簇系數,更為合理地保留原來實際存在的鄰居節點間權重邊,反映整個網絡的簇群關系[10]。借助BBV網絡模型進行仿真分析,得到各種簇系數隨時間演化及與權重的關系如圖5和圖6所示。由圖中可知,在BBV網絡中各簇系數隨時間演化時,一致減小;對于拓撲結構相同而權重不同的網絡,權重越大集聚效應越強,簇系數越大。
在產業集群創新中,一方面,通過知識網絡給集群內的各知識主體提供了便利的信息傳遞渠道,降低了技術創新中需要利用相關知識的認知成本,尤其是低編碼水平的隱性知識的學習成本;另一方面,集群內各知識主體也在交往互動中推動了集群整體的創新合作。當然,對于集群創新系統中的知識網絡,由于環境的復雜性和集群知識主體(如大企業、中小企業、中介組織、科研機構、政府等)的參與程度不同,可能形成不同點權、邊權的網絡結構,這些不同類型的網絡結構對于集群知識主體學習機制的影響也不同。根據BBV網絡模型的仿真分析,權重越大集聚效應越強,簇系數越大,集群層知識的聚合越強;而簇系數隨時間演化,會逐步減小,進而降低集群層知識的聚合度,如果不加以補償,集群主體知識創新能力將會降低。
4 結論與展望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產業集群創新系統是一個動態演化的系統,由不同的創新主體所構成的集聚體。集群創新是基于嵌入在特定關系網絡中的知識管理活動,網絡關系強度的不同對知識創新產生不同的影響。在權重知識網絡中,簇系數越大,集群創新能力越強;另一方面,簇系數隨時間演化會逐步減小,作為補償,我們可以通過保持網絡知識的差異度削減該趨勢。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那些試圖提升集群知識創新水平的政策決策者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現實中,通過在集群創新知識網絡中識別并促成高中心性或高中介性的知識主體,形成集群創新的持續動力。本研究的進一步工作,需要借助實證研究的手段,驗證該結論與現實當中的集群創新知識網絡演化的吻合程度。
[1]張永安,付韜.集群創新系統中知識網絡的界定及其運作機制研究[J].天津: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9,(1).
[2]姜照華,隆連堂,張米爾.產業集群條件下知識供應鏈與知識網絡的動力學模型探討[J].天津: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7).
[3]秦鐵輝,彭捷.SECI框架下不同組織和層級間的知識轉化研究[J].北京:情報學報,2006,(12).
[4]邢小強,仝允桓.基于企業內部知識網絡的知識活動分析[J].天津: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7).
[5]陳得文,陶良虎.產業集群知識網絡運行分析[J].商品儲運與養護,2008,(2).
[6]徐盟.產業集群內網絡化創新機制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09,(4).
[7]D.Watts,S.Strogatz.Collective Dynamics of'Small-World'Networks[J].Nature,1998,393(6684).
[8]Cowan Robin,Nicolas Jonard,Muge Ozman.Knowledge Dynamics in a Network Industr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Social Change,2004,(7).
[9]S.Boccaletti,V.Latora,Y.Moreno M.Chavezf,D.-U.Hwanga.Complex Networks:Structure and Dynamics[J].Physics Reports,2006,(424).
[10]李穩國,王力虎,陳明芳.加權網絡簇系數[J].計算機工程與應用,2008,44(28).
(責任編輯/浩 天)
C931
A
1002-6487(2010)19-0043-03
教育部人文社科資助項目(09YJC630117);中國博士后基金資助項目(2009045118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09SJB630047);南京郵電大學引進人才項目(NY208013)
彭 英(1971-),四川三臺人,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復雜系統理論、知識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