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記者調查門”事件的思考
對“記者調查門”事件的思考
編者按:近期各地陸續曝光了一系列粗暴甚至以刑事手段“對付”記者的事件。種種跡象表明:輿論監督與公共權力摩擦日趨明顯。日前,《新聞記者》雜志和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聯合舉行了“公權力和采訪權關系”新聞法制研討會。專家學者呼吁:不要動輒使用刑事手段對付記者,媒體有權對新聞“線人”信息予以保密。
呂怡然 《新聞記者》雜志主編
我看新聞人“被”成為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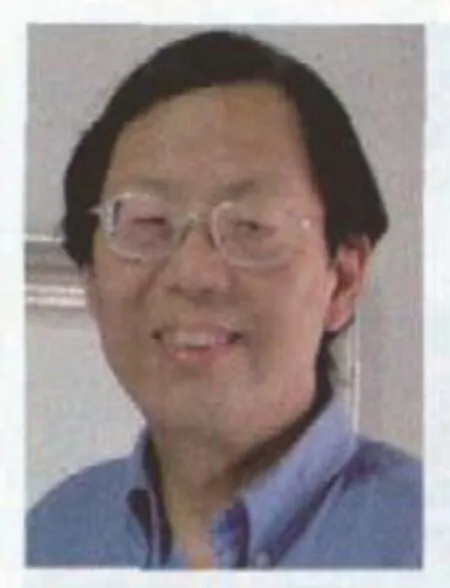
當今是多媒體時代,也是媒體多的時代。媒體非常多,與過去相比,無法想象。現在的信息傳播,就好比是空氣流通。到處都是信息在流動、信息在傳播。所以信息的傳播者,或者說我們的職業新聞人,本身也就不時地成為新聞,“被”成為新聞。
報道新聞的人,越來越多地成為新聞的報道對象,甚至演化為公共事件。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地聽到我們的記者被威嚇、被通緝、被傳訊、被拘留、被毆打、被追殺,等等。記者成為很多新聞事件中的中心人物。近來,更有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之勢。千龍網記者阿良因為批評山東萊陽地方企業遭到當地警方追蹤調查就是典型一例。
這些,是不是都是我們行使輿論監督權利以后惹的禍呢?公權力和我們的報道權、監督權、話語權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我們的公權力,對我們的新聞采訪是支持、保障、維護、捍衛,還是對抗、蔑視、厭惡、仇恨?這之間的關系,很耐人尋味,值得我們探究。我們的記者,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弱勢群體。在公權力面前,特別是這樣。中國記協維權委員會對9個省市16個城市進行調研,在收回的1476名記者問卷中顯示,半數以上記者曾經在新聞采訪中遭遇不同程度的阻撓。這說明,我們新聞記者現在行使采訪權、監督權、報道權、話語權,不那么容易。
同時,我們也有兩個方面的問題。最近,看到一篇新加坡《聯合早報》寫“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艱難處境”,專門講我們輿論監督很難,要揭露黑暗的層面很難。第二篇文章,是《福布斯》雜志發表的文章,叫“黑暗的中國新聞界”。說中國新聞界很黑,黑到什么程度呢?什么都可以用錢來搞定,包括國家級媒體,這些暫且不論是否符合事實。但他認為中國新聞界充滿了黑暗。從這兩篇文章的兩個標題,正好是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的報道權不能落實,我們的記者受到侵害。另外一方面,我們自身到底如何?新聞界到底是怎樣的狀況?這兩個方面,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究的。
通過探討,通過信息和觀點的傳播,但愿能使學者小范圍里的滔滔不絕,變成社會公眾的滔滔不絕,用我們第五權力支持我們第四權力,來制約公權力,希望公權力能夠為我們的老百姓謀利,而不是為少數人充當“看家狗”、充當“保安隊”。■
莊建偉 華東政法大學民商法副教授
不要濫用刑事司法公權力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經營主體,對于其在市場經濟中的任何經營行為必然會受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注和監督,這當然更少不了新聞媒體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隨著國家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新聞媒體針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報道自然也會越來越多。這種報道無論是褒揚性質的,還是批評性質的,只要不是惡意詆毀,都首先應當視作為新聞監督權、報道權的正常行使。當然,新聞報道一出來,往往會引發相應的利益沖突,有的利益沖突激烈,就需要上升到法律的層面來解決這種沖突。

但解決此類利益沖突的法律途徑是有層次性和相對的次序性的。它的層次性表現為私法領域和公法領域的兩種解決問題的途徑。私法領域中利益沖突解決方法表現為利益沖突方相互之間的直接交涉,直至對簿公堂。在此類事件中的利益沖突相對方也只是新聞媒體機構(包括記者)與被報道的企業或個人;而公法領域中的利益沖突則是因為私法領域的私利益之間的沖突轉變成了與社會公共利益或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這時利益沖突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之所以發生這種質的變化,是因為在此類事件中的新聞媒體機構(包括記者)的報道觸犯了刑律,形成了某種犯罪嫌疑,此時的利益沖突方就轉變為新聞媒體機構(包括記者)與國家司法機關,便也形成在公法領域內解決利益沖突的局面。這時,解決該種利益沖突的手段就表現為國家刑事司法方面的公權力的強行介入:警方的刑事調查、檢察機關的刑事檢察、直至法院的定罪量刑。大量的社會利益沖突都首先應當在私法領域中得到問題的解決,這時,國家刑事司法的公權力不應當介入。只有當私利益的沖突已經轉化為公法領域的利益沖突,國家刑事司法的公權力才能發揮其作用。
千龍網“阿良事件”與浙江遂昌“仇子明事件”的共同性在于,當媒體針對企業的報道一發表,警方便隨即出動,立即對撰稿記者采取刑事司法調查手段,行動之迅速,手段之強硬,實在令人咋舌。正因為如此,這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警覺。
根據筆者手頭所得資料來看,萊蕪警方在向千龍網及記者劉洪昌調查時,不僅未向被調查人宣布記者的報道行為可能觸犯的是哪一個刑法法條,構成了哪一宗罪的犯罪嫌疑,也未表明是不是因有人報案而前來進行調查。在沒有拿出相應的事實依據前,就武斷地聲稱記者的報道失實,并且一味地向被調查人要求提供新聞線索的“線人”的情況及追問記者是否收了別人的錢。這樣的刑事調查,不僅有違刑事司法調查程序的規定,而且這也反映出警方是在越權動用刑事司法調查手段,強行地不當干預私法領域的利益沖突。在浙江遂昌事件中,警方當時還先給記者仇子民明安了一個罪名,然后才對其采取刑事司法調查的手段。然而在“阿良事件”中,警方連罪名都不提了,就直接采取刑事司法調查的手段。
當私法領域的私權利與公權利不正當地結合在一起時,所產生的一個必然問題就是公權利的濫用。所謂不正當結合,就是指公權利的行使是在違背了權利行使的法定程序、方法、領域的情況下來保護私法領域中的私權利。其表現是,本應該由被報道企業本身通過民事救濟途徑解決的問題,卻變成了警方的直接刑事司法調查。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使市場經濟中企業公平競爭的條件缺失,也會使新聞媒體及記者們的合法權利受到嚴重的傷害。我們真誠地希望,警方應該停止這樣的行為,今后也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楊可中 華東政法大學刑訴法副教授
對“記者調查門”的法律思考

通過記者“調查門”事件,有些問題值得引起思考。筆者先就警方說新聞與他們的調查情況不符,對當地企業造成了不好影響問題予以探討。
記者調查采訪的事實是否必須與司法職能部門調查的事實保持一致,這涉及對事件的真實性的認識和調查的動機等諸多內容。這里面包含了三個不同的概念:客觀真實、新聞真實和法律真實。
客觀真實,是指在意識之外,不依賴主觀意識而存在的事物和狀態;而新聞真實,僅僅是新聞工作者根據新聞規律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狀態,認識與存在總是有差距的。同樣,法律真實,也是法律專家根據訴訟規律、證據規則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狀態,同樣不代表客觀事實。因此,對新聞真實的判斷,如果僅僅從法律真實的認識規律出發,甚至將法律真實等同于客觀真實,而罔顧新聞真實,或者將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混為一談,都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
新聞的輿論監督只負有啟動監督程序的義務,徹底查明事實是司法機關的職責,雖然新聞機構如能查明事實更好,但若未能查明,不能要求新聞媒介承擔其他機關所應承擔的義務。而如果他人提供的材料失實,自有承擔責任的主體,他人提供了虛假的材料,他人就應該為此承擔責任,而不能由負監督職責的新聞媒介承擔責任。這是由新聞媒介的價值取向決定的。
阿良記者在千龍網發表報道后,該企業所在地的山東萊陽市委宣傳部多次出面稱該報道失實,要求撤稿,緊接著當地警方又出面對記者展開追蹤調查。筆者認為,宣傳部門錯位行政甚至濫用公權力,是對新聞工作者正當的采訪權和報道權的侵害,更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剝奪。而當地警方輕易介入展開調查的舉動更令人吃驚。
在筆者的記憶中,改革開放以來,記者因報道而被追究刑事法律責任走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最早的案例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80年代。1986年《民主與法制》的記者因報道一起“瘋女”案件而被其丈夫以誹謗罪告上法院。最后記者被法院認定有罪,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但這之后的報道糾紛,隨著民事法律的陸續頒布,大都通過民事侵權渠道予以解決。近些年又出現以刑事案件處理糾紛的回潮態勢,這種以刑事方式處理糾紛的態勢令人擔憂。
如何切實保護記者的合法權益?
我們知道,記者仇子明案件之所以能得到較圓滿的解決,主要依靠的是相關上級部門的干預。但從理性的、法治的角度思考,筆者認為,健全法制建設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首先,應早日制定和出臺“新聞法”。這是依法保障記者采訪報道的“護身符”。記者因采訪報道而引發的官司,如果能在“新聞法”框架下進行,很多問題應能得到破解。
其次,修改侮辱誹謗罪和損害商業信譽罪的規定。根據現行刑法第246條的規定,侮辱誹謗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但是,該法第二款又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屬于公訴案件。現在不少地方追訴公民或記者的依據就是這第二款。筆者建議細化關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內容。
此外,近年來發生多起企業以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為借口來對抗和打壓輿論監督的事件。輿論監督往往涉及公司的負面新聞,客觀上對公司商業信譽必然帶來損害。特別是在一些公司企業受到政府偏愛,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時,地方政府和官員就必然指使司法機關以對方涉嫌損害商譽犯罪追責。因此,建議在該條法律規定的適用上應對記者和媒體采取特殊保護,在實際應用中考慮到新聞法出臺存在較多困難,全國人大可以考慮出臺修正案,或者最高法院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用于過渡,以保護媒體從業人員的權益以及對不法行為進行懲處。■
編輯: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