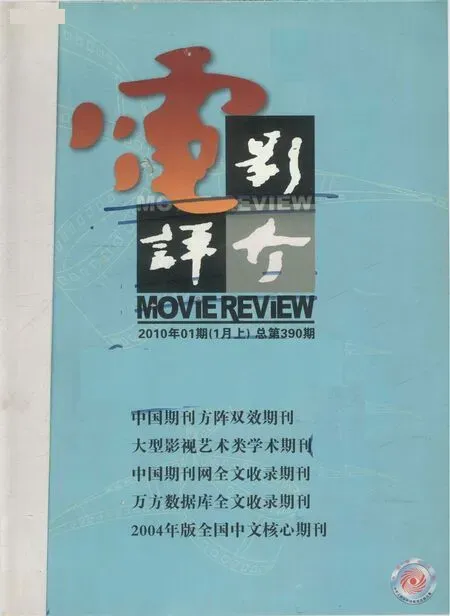從顛覆到癲狂
康定斯基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電影作為一種大眾藝術,一種消費文化,更應貼近時代的潮流。在中國當今的電影藝術領域,張藝謀無疑已成為了一個最重要的電影文化符號,其代表著多重的象征意義。無論是在藝術層面上,還是從商業視角來看,張藝謀都是中國電影潮流中最具創造力、最具影響力的先鋒旗手。
一、電影潮流的顛覆者
當下,電影的基本功能已由教化與啟蒙轉向為娛樂與消遣。然而,娛樂與消遣需要不斷地更新與刺激,需要不斷地被取代和顛覆,這導致我們的電影潮流一次又一次地被顛覆,而張藝謀就成為了每一次顛覆的開拓者,我們可以回眸一下這位顛覆者的大致歷程。
第一次是對“政治電影”的顛覆。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是《紅高粱》,這是一部文藝氣息很濃的作品,影片用一種獨特的社會視角來觀照一個時代,以童稚觀點回憶“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整部影片在一種神秘的色彩中歌頌了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贊美生命是該片的主題。這相較于我國前期大部分以主角又紅又專,高大全為特色的“政治電影”而言,無疑是一種顛覆。該片1988年獲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大獎,這是中國新時期電影創作的新篇章,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新開始。后來,他又拍了《活著》、《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一系列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具有濃厚的文藝氣息。
第二次是對文藝片的顛覆。進入到21世紀,中國也慢慢邁進了一個日漸繁榮的消費時代。面對美國的好萊塢大片的強烈沖擊,中國的電影行業處于一種生存的困境。這時,張藝謀又走在時代的前列,挑戰商業大片。2002年,他打造了中國第一部古裝武俠商業大片——《英雄》。《英雄》讓張藝謀贏得當時驚人的票房,全球票房1.77億美元,2004年8月在美國上映連續兩周票房冠軍。爾后,他又接連拍出《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皆賺得缽滿盆滿。在他的引領下,中國電影業進入了一個商業大片的時代,顛覆了以往的文藝片時代,當然更主要的是使中國的電影業暫時走出了生存的困境。
第三次將是對武俠大片的顛覆。奧運會后,當張藝謀再度回歸電影時,武俠大片處于行將沒落期。作為一名中國電影業的先鋒開拓者,他當然又要充當一次潮流的顛覆者。在把握住時代的趣味后,這一次,他把目光轉向了娛樂片。于是,就有了2009年他推出的新片《三槍拍案驚奇》(以下簡稱《三槍》),而張藝謀的這一次華麗的轉身,會不會把我們的電影引入一個新的潮流——娛樂的癲狂時代?
二、《三槍》將帶來娛樂的癲狂
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在他的力作《娛樂至死》中這樣描述:“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1]很顯然,這是對我們當今這個泛娛樂化時代的一種觀照。確實,無論在什么時代,我們都需要娛樂。在過去的鉛字時代,我們需要娛樂,在這個娛樂化時代,我們更需要娛樂。因此,《三槍》是順應這個潮流的,將會是我們電影真正走向娛樂的一次大膽探索。
這次,張藝謀是揣著一顆童心,而不是藝術家的心來看待當今娛樂電影的。看來他已經徹底放下包袱,立志要把觀眾帶到一個娛樂的癲狂狀態。這里,我把《三槍》中充滿二元對立的娛樂因素進行了一番梳理,概括如下:其一、片名的中外結合。我們知道《三槍》是從好萊塢的劇本《血迷宮》改編而成,但片名《三槍拍案驚奇》顯然與中國古典名著《三刻拍案驚奇》有著一脈相承之處。其二、演員的剛柔相濟。三位主演中,孫紅雷一貫是硬漢形象著稱,而小沈陽大家都知道是帶女人味的男人,閆妮更是一位“調情影后”,尤其是孫紅雷與小沈陽的形象反差,其娛樂效果明顯。其三、畫面的莊諧相襯。畫面的詼諧效果尤其從演員的著裝上就可窺一斑,小沈陽的粉紅色的衣服與閆妮的綠色衣裝體現出真正的紅男綠女;而趙本三套上灰黑色的古代將軍鎧甲加上他幽默的對子眼,會立即讓人忍俊不禁。其四、劇情的多元摻和。《三槍》是一部由喜劇、愛情劇與驚悚劇組成的有機綜合體,電影上半部分,張藝謀對感情簡單布局,很類似之前《紅高梁》、《菊豆》的某些情節;隨著劇情鋪開之后,到了下篇卻是伏筆眾多、危機重重。其五,幽默搞笑的臺詞。影片中幽默搞笑的語言是其一大特色,如老板娘對李四說:“我一直想找個肩膀依靠,沒想到找了個假肢,還是個次品。”等臺詞,聞之,讓人忍俊不禁。
總之,《三槍》中充滿了諸多的娛樂元素,讓觀眾在這種視覺的盛宴中體會到娛樂的癲狂之美。
三、癲狂之后的沉思
叔本華說:生命是一團欲望,欲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與無聊間搖擺。[2]尤其是這個后工業時代,隨著理性與宗教的破產,許多80、90后,不愿做只有理性的“蠻人”,而更愿做只有感性的“野人”。他們喜歡簡單感性的快樂,他們排斥深度模式,他們解構崇高,他們擁抱這個娛樂化的時代。這就是為什么“無厘頭”電影現在仍然受到港臺、大陸青少年的熱捧,它十分突出地彰顯了諸如解構、荒誕、狂歡等后現代美學的特征,亦以其獨特的語言形式和敘述手法為大眾欣賞和接受。張藝謀也始終認為,電影就是拍給80后、90后這些年輕人看的。正如巴赫金所認為的那樣,狂歡它表現出一種超越同時代人的更為達觀、更為輕松舒適的生存理念。
是的,當今電影主要關乎娛樂,而非教化,是讓人們帶著輕松的心情去享受生活;但是,娛樂化的電影是否一定要消解所有的深度,卸下所有的責任,或者說娛樂化的同時,至少“電影需要有一種人性的自省”[3]?在今天,尤其是在電影創作面臨市場經濟沖擊的態勢下,一部好的電影是否能同時集藝術價值、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于一身?重新認識“教化”與“娛樂”的關系,并進而拓展對電影功能的理解,應該是一樁十分具有文化意義的事情。
[1][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
[2][德]阿圖爾?叔本華.作為意識和表象的世界[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9.
[3]林黎勝.驢的人性或人的驢性[J].電影藝術,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