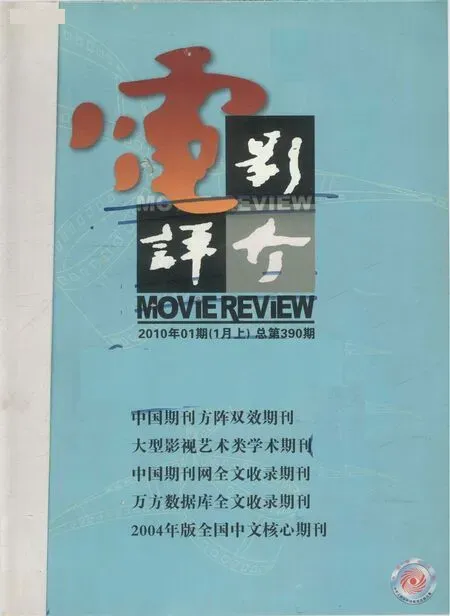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暖》 的影像修辭手段
電影導演霍建起從自修美術到求學于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擔任美工設計,都和美術有關。也許是緣于這份醇深的專業浸染,他后來導演的影片都很重視影像的修辭效果,比如《贏家》、《那山,那人,那狗》、《藍色愛情》、《九九艷陽天》、《生活秀》等電影作品,觀眾對片子里的影像設計意圖和效果想必是不會忽略的。根據莫言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由李佳、郭小冬和香川照之主演的電影《暖》更是充分顯示了影像畫面的修辭功能,它極力牽引觀眾進入視聽背景之后的人物及故事體驗中。
電影開片的抒情式風景鏡像暗示了整部影片的敘事結構,即以“我”的行蹤和思緒為線索,劃定了一個“回鄉——在鄉——離鄉”的結構框架。這個框架其實很普通,只要在前兩分鐘甚至更短的時間里就能夠明察導演的這一意圖。那或明或暗的大樹先以遠鏡頭形式出現,慢慢推近;再以移鏡頭形式向左淡出銀幕,繼之而來的是連綿峰巒,自上而下盤旋邐迤的山路;淡入一個青年人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茫茫青山與蘆葦叢,瞬即視線隨著自行車的運動來到了山里面的一個村落,出現無邊的金黃稻浪和秋波翻現的鄉間小路。在這系列充滿動感的構圖中,配以第一人稱的旁白,從而透露影片的結構傾向:村里十年前的大學生,如今回鄉替當年的曹老師謀事并作短暫的居延,必然在影片結尾處也即事情辦完之后以再度辭鄉而終。可以設想,只要對魯迅的小說《故鄉》稍有一些印象,我們就不難發覺,兩者的結構完全相同,只不過文本表現的具體媒介不同罷了。如果把《故鄉》的開篇文字置換成電影鏡頭的話,估計與《暖》類似,只須將群山換你河流、自行車換作烏蓬船而已。也許霍建起是有意采用“回鄉——在鄉——離鄉”的敘事結構,借以喚起觀眾的參與熱情,并將觀眾導入其特設的召喚結構而最終在影片含蘊方面打破觀眾的心理期待視野。總之,他的首尾圓融呼應的結構意圖,完全可以在開片之初猜測出來。這是一種顯山露水的修辭手段。
其次,影像修辭手段著力體現在其替補語言表達的效能上。影片中,戲班里的武生自始至終鮮有臺詞,他大都以臉譜形式和一些肢體動作出現,成為符號化表征,即成為女主人公暖的生活企求。可以說,他表演技藝時的畫面,正是呈現在暖面前的生活幻影,在暖心里激起愛的漣漪和憧憬;然而,這種美麗情愫是建立在臉譜化和戲劇化的非現實基礎上,注定要以絕望和創傷告終。武生出現的畫面往往采用慢鏡頭或特寫鏡頭,如武生幫暖化妝的影像部份,基調舒緩,如歌如訴,雖沒有片言只語,卻足以表現暖內心的細水微瀾。而她的陶醉感,恰恰反映出城市文明對于閉塞農村少女的巨大誘惑力。同時,希望越強烈,失望的痛感就越劇烈。影像的無聲效果也由此產生。這種修辭效果無聲勝有聲,較好地替補了語言臺詞不能達意的缺陷,而激起觀眾情不自禁的惜惋默嘆。當然,這一修辭手段體現在很多方面。又如秋千架驟然斷裂之后長時間的特慢鏡頭,以及村人匆忙搶救暖的搖晃鏡頭,非常沉郁而簡省地交待了人物命運轉折的關捩點和前因后果,也非常有沖擊力地喚起觀眾由衷的感喟及思索。再如,林井和,也就是“我”去探訪暖的家時,暖在樓上梳妝臺前對鏡顧盼,反復地為悅己者容,而樓下則是其啞巴丈夫與舊情人“我”的長久對峙,無言的尷尬、疑懼、拒斥等內心活動都相當明晰地經由人物的神情纖毫畢現。這些情景畫面,皆無需人物臺詞從中輔助表義,觀眾亦全然可以心領神會其中的人物關系及意旨。
如上所舉,影片中的秋千架旨關大節,其中的多次特寫乃影像修辭的反復凸現手段。一個鄉村的普通秋千架成為敘事的關結物,許多悲歡離合的情緒都能在其中搖蕩出來,顯現在觀眾眉睫之前。它出現的頻率很多,既可作為影片的文本之眼,又可推動故事發展,還可渲染命運氛圍,解釋人物與境遇關系,預示生活的幻想與失望,諾言與無奈,等等,可謂淋漓盡致。比如啞巴與林井和一塊蕩秋千的鏡頭,導演設計成井和站在秋千架上,俯視啞巴;而啞巴則推動秋千,似乎暗含一種城市人對鄉村人的居高臨下的優勢姿態;啞巴的憨憨笑聲,又似乎在寬容或默認這種差異懸殊的事實。井和與暖也蕩過幾次秋千,最意味悠長之處有兩個。其一是,井和即“我”特意取出母親的紅紗巾,蓋在暖的頭上,然后共蕩秋千,晃來晃去,表白出小伙子美妙的戀愛心理。但好景不長,紅紗巾在大幅度的搖蕩中飄落下來,畫面緩慢,悠長,輕柔,重疊,復現,漸次飄落于地上。這個蕩秋千的情形,寓意自然存于其中,等待幾代人和親身體驗式的解讀。紅紗巾從高高的秋千架上飄落,勢必造成觀眾心理期待落空,原以為是一段美好愛情征兆,不料以后事與愿違。這就涉及第二個畫面,即更為扣人心弦的“我”和暖共蕩秋千的畫面。兩人相向站在秋千架上,暖頭靠在“我”并不寬闊的肩膀上,使我充溢了幸福感。畫面色調由明轉暗,由溫轉涼,依據觀看電影的一般經驗,也許觀眾覺得鏡頭會轉入次日早晨。其實不然,這既暗示自然時間的遷移,又折射人物命運的急轉直下。那個秋千架依然晃動,來回不止,產生心理延宕的效果。而且,畫面拍攝角度選擇恰當,從底部向空中拍攝,使得觀眾心理不由自主正襟危坐,仿佛在擔心什么似的。尤其是加上秋千架枯澀刺耳的嘎吱嘎吱的音響效果,這鏡頭在觀眾心理上的震攝力獲得了張力。果真,該發生的最終發生了。接下來的是散架的秋千依然在無助而沉默地晃動,讓觀眾自己去填補影片的留白。那個四分五裂的秋千,交待了暖瘸腿的原因,昭示了幸福感覺的瞬間煙滅。真是此憾綿綿無絕期,此憾卻關秋千架。秋千架的斷裂,表征著聯系城市與農村的紐帶的脆弱性,表征理想與世俗之間的糾葛與鴻溝,表征了罪孽與懺悔之間不確定的關系。此外,皮鞋、雨傘、蘆葦、草垛等特殊影像都體現了“我”對鄉村文明進行回瞥時產生的留戀與悔意及莫可名狀的無奈感。這種依賴特寫而反復凸現的修辭手段,使影片主旨的輻射收效甚佳。
另外,大量的閃回鏡頭,將現實與回憶融為一體,產生影像的互文修辭效果。故事的敘述卻仍然極為流暢,沒有絲毫滯澀感,做到了敘事順序井井有條又穿插有度。如“我”回到家里埋頭洗臉時,鏡頭閃回到少年時代與暖共蕩秋千及一起讀書返家的情形,很自然地將故事的原始發生時間引出,原初的戀情也順延出來,可謂水到渠成。那雙皮鞋先穿在小女孩的腳上,后來閃回到與皮鞋有關的故事,現實與過去相互交織,相互推進,相互發凡,展開影片的下一步敘事。完全可以說,這些閃回鏡頭構成了影片的半壁江山,是各種對立關系中一端。古樸體驗與此在的遭遇發生碰撞,寄寓在閃回鏡頭與現實鏡頭的穿插印證關系中。從而,影像的這一互文修辭功能通過這些平衡相對的關系群浮現出來了。
很明顯,各種影像修辭手段在電影里的運用并非盡善盡美。就拿結尾來說吧,顯得太倉促突兀了。它僅僅停留在河邊就定格了。依我之見,影片結尾最好與開頭有所回應,也即補上“我”推著自行車孤獨地走在山路上,而暖一家的背影漸漸淡出畫面,以遠鏡頭和拉鏡頭再度淡入描繪那棵大樹、那些蘆葦和那綿延的峰巒,最后淡出以至閉幕。惟有如此,首尾結構才能真正做到形式上圓合而意義上開放,像魯迅的《故鄉》樣處理得從容有致,余韻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