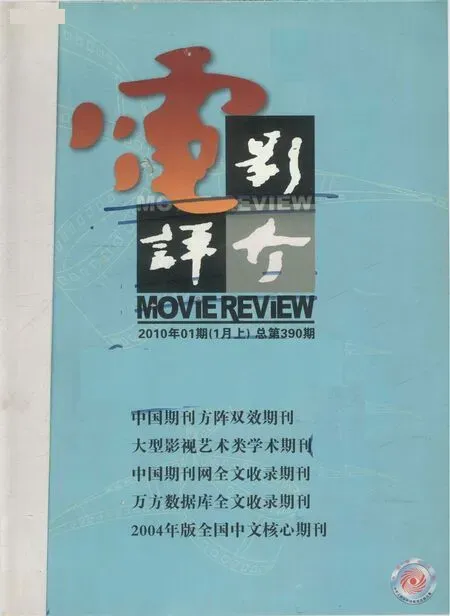接受美學視域下的《建國大業》
《建國大業》由172位明星共聚一部電影,創造了電影歷史上明星最多的神話,并且上映三天半后票房過億,刷新國產片最快過億紀錄。據有相關媒體報道,《建國大業》在全國的票房已超過4億,同時創造了國產電影票房的最高紀錄。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一部主旋律的電影為何能贏得不同品味觀眾的歡迎呢?本文試圖以接受美學的視角,從“隱含的讀者”、“召喚結構”等方面解析。
一、接受美學及其主要觀點
接受美學又稱“接受反映文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聯邦德國出現的一種文學美學思潮,它是以讀者的文學接受為旨歸來解釋闡發諸種文學現象的美學理論。接受美學的核心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姚斯認為只有運用“歷史接受法”,才能真正理解作品及其意義和價值。他說:“必須從三個方面考察文學的歷史性:文學作品接受的相互關系的歷時性方面;同一時期文學參照構架的共時性方面以及這種構架的系列;最后,內在的文學發展與一般歷史過程的關系。”[1]可見,姚斯的理論注重文學的本體性。在他看來,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并不是客觀的,而是與受眾的價值體驗有著密切的關系。一部藝術作品,通過預示、暗示、特征顯示,為讀者提示出一種特殊的接受。所以,接受美學給我們的啟示是,一部好的電影來源兩個方面,一是電影本身,一是觀眾的賦予。今天,我們用接受美學的視野來審視《建國大業》,探尋被受眾推崇的藝術魅力。
二、從“隱含的讀者”出發,找準看點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周年。《建國大業》以1945年抗戰勝利直至建國前夕這一波瀾壯闊的時代為背景,以史詩的筆法和視野,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團結奮斗直至取得最后勝利的光輝歷程,也反映了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個性和時代特征。這部主旋律影片作為祖國生日的獻禮,迎合了當下觀眾的審美心理。“接受美學”認為,“隱含的讀者”是作家本人設定的能夠把文本加以具體化的讀者,也是伊瑟爾認為的“文本預先被規定的讀者的行動性”。作為每一個炎黃子孫,在面對祖國強大充滿驕傲和自豪的同時,都不禁要回望過去走過的艱辛道路,《建國大業》充分考慮到了觀眾的接受心境和期待視野以及“隱含的讀者”的廣泛性。
三、構建“召喚結構”,增強電影的藝術性
接受美學認為,作品本身是一個“召喚結構”,它以其不確定性與意義的留白,使不同的觀眾對其具體化時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所以對于一部電影而言,觀眾的理解本身也同樣包含著創造的因素。反過來講,觀眾之所以能充分調動主體的能動性,對作品的符號進行解碼,還在于電影本身所創造的藝術內容的豐富性和藝術形象的生動性。
1、“圓形人物”的立體展現《建國大業》,塑造了性格豐滿的人物,表達出了人物的復雜性和多面性,而不是為了某一個固定念頭而把人物展示在種種的矛盾沖突之中。毛澤東、周恩來是時代的偉人,他們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屏幕形象早已在觀眾心中定格。但《建國大業》敢于突破傳統,打破了人物形象臉譜化的模式。聽到馮玉祥遇難的消息時,毛澤東踢翻了洗腳盆,周恩來大發雷霆,怒氣沖天,摔東西,詞語嚴厲,這都是在以往影片中看不到的,他們是時代的偉人,同時也是一個個普普通通的鮮活的生命。對蔣介石的刻畫更是與以往的形象大不同,在《建國大業》中,蔣介石可謂是“一個英雄的末路史”,他并非十惡不赦的罪人,而是經過痛苦掙扎,最后才四面楚歌,可以說他的失敗并非個人的失敗。《建國大業》塑造了眾多鮮活的形象,個個性格飽滿,富有生命力,看完之后給人更多的思考,啟示人們電影所展示的只是人物形象的一部分,還有更多的人物內涵值得人們自己去想象和品味,這也正是“接受美學”所倡導的“留白”的藝術性。
2、形象、個性化的語言 這部電影在追求敘事的宏大氣勢、尊重史實的同時,力求影片的觀賞性和趣味性,語言的個性化也體現了這方面的特點。馮玉祥的一句“大白天,黑暗啊,不打燈籠我找不到道”,形象的揭示了當時社會現實和他面對現實時內心的苦痛;蔣經國用“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表明整頓經濟的決心,而杜月笙卻說“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蔣先生搬不動吧?”風趣、幽默,充滿諷刺。蔣介石在窮途末路時發出了“國民黨的腐敗已經到骨頭里了”“反要亡黨,不反要亡國”的感慨,增添了悲涼感。這些形象、個性化的語言創造了豐富的藝術形象,也在感性的外殼中蘊藏著意識的、精神的內涵,語言本身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耐心咀嚼。
3、生動的細節展示 前蘇聯的米哈伊爾-羅姆說過:“導演應當明確規定觀眾應該往哪看和怎么看。他設計的鏡頭,應當使觀眾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使觀眾所注意的人物,細節是他這時必須注意的人物,細節,從這方面來說,導演就是一個對觀眾實行獨裁的人。”[2]細節,作為重要的鏡頭語言,有著重要意義,可以說一個好的細節,可以照亮全片,可以震撼人心。《建國大業》無疑是這方面的典范。影片中對于細節的運用恰到好處,例如劉燁飾演的老兵代表活著的和死去的紅軍戰士向毛主席匯報時,聲音嘶啞但器宇軒昂,感人至深。范偉飾演的郭師傅把煙放在耳后,“主席的煙我不舍得抽”,充分展示了人民對毛主席的尊敬、崇拜和喜愛之情。這樣的細節運用還很多,毛澤東與蔣介石同時以中山裝出席記者招待會,淮海戰役取勝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醉酒的情形,毛澤東在閱兵儀式上的潸然淚下等等,這些細節的運用,對于刻畫人物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也留給人們對于人物更多的思考。
[1]姚斯 《文學史作為文學理論的挑戰》轉自胡經之 王岳川《文藝美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第338頁
[2]米哈伊爾-羅姆 《電影創作津梁》中國電影出版社 1994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