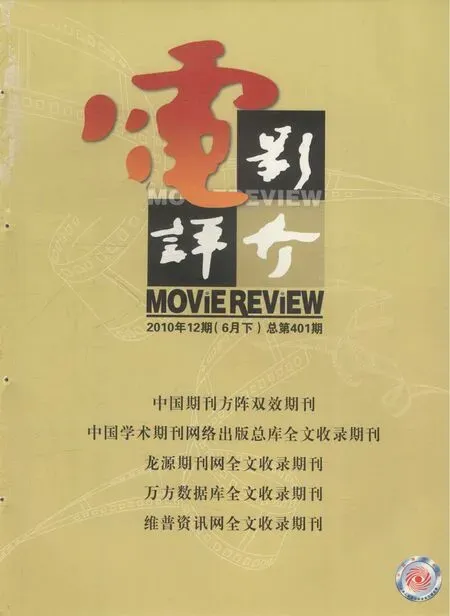民族動畫創作中的束縛與超越
一
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動畫的美學特征是豐富而多彩的,有專家就曾指出:“一個國家的美術電影趨向成熟的標志之一,是它藝術作品更多地包含著本民族的藝術趣味和適應本民族的欣賞習慣,也就是這個民族在漫長的藝術發展道路上,逐漸形成的美學原則”。[1](28)由于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潤澤,所以在中國動畫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具有民族藝術風格的動畫作品。這些動畫作品的產生和發展顯示出獨特而鮮明的民族個性和人文品質,具有著獨具特色的審美情趣和藝術特征,所以才能走出國門而蜚聲于國際動畫影壇。中國民族動畫的成熟及發展為當代中國動畫藝術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大量內容,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民族動畫的繼承和發展再次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并給予了極大程度的提倡和宏揚。但是,中國動畫創作的現狀和受眾對當前民族動畫作品的認可,卻和理論界的爭鳴顯示出大異其趣的表現形態,盡管動畫界依然亦步亦趨地追隨著民族的創作方向,依然以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藝術情調來進行創作,但動畫作品的認可度卻仍然沒有多少好轉,面對理論與實際所產生的這個悖論問題,我們該做出怎樣的選擇?新的經濟背景和文化景觀下民族性的創作方向到底該如何選擇?基于此問題本文做了一些理論層面上的思考。
具有中國民族特性的大量動畫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化的根基下產生的,并且在作品中凝結著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審美理想以及本民族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趣味等,所以,中國動畫中帶有民族特性的動畫作品,不論其動畫形象本身還是故事內容以及表現形式,都是深深地扎根于傳統文化的根基上建構起來的,在其作品的深層價值結構中都體現著民族文化的縮影。以60年代前后中國動畫的輝煌成就為例,這一時期的動畫創作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樸素恬淡、計白當黑的筆墨情趣,而且可以感受到意境悠遠、畫面雋永的造境情調,以及可以品讀到“中和之美”的創作審美指向和“團圓”軌跡的故事結構,等等,這樣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氣質在動畫的創作中得到了很好地體現,贏得了中國觀眾的認可,同時也得到了世界觀眾的褒揚。但是這里我們有必要進行思考,為什么當時所展現的文化內涵和藝術格調得到了世界的認可,而現如今的動畫創作盡管也依然沿用民族的創作思路和創作手法,乃至同樣的表現題材和藝術元素,卻創作不出享譽世界的優秀動畫作品呢?
二
單純從傳統文化本身來講,經過文化多年的積累和沉積,一個民族必然會形成穩定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活動取向。“一定的文化沉積層,是一個民族成熟與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2](150)所以,在一定的地理環境及人文環境的長期孕育下,必然會形成獨特而鮮明的群體性的性格特征、價值追求、審美取向、情感方式等以民族文化為核心的多方面的展現形態,各個層面又會不斷影響和促成獨特而穩定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的形成。這種文化及觀念一旦形成,便具有著穩定的結構模式,無論從思想維度上、還是藝術追求或是審美理想上,都會以“典范”的姿態來形成一種文藝創作的范本模式。這種范本模式盡管在傳承民族文化和展現民族藝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臨范”創作方式的背面,也必然會遮蔽和壓抑著創新和開拓的潛勢。
以六十年代中國動畫的代表作品《大鬧天宮》為例,“1978年《大鬧天宮》在倫敦電影節上取得的成就最為奪目。當時取得的獎項是‘最佳影片獎’。在電影節的紀念冊中,影評人凱恩?拉斯金這樣寫道:‘這部影片可以和《圣經》中的神話故事以及希臘的民間傳說媲美。它們同樣是充滿了無窮的獨創性、迷人的事件、英雄式的行為和卓越的妙趣。影片通過杰出的美術設計,而成為一部擁有強烈感染力的作品。’美聯社在倫敦電影節上的報道表示了同樣的尊敬:‘美國最感興趣的是《大鬧天宮》,因為這部影片惟妙惟肖,有點像《幻想曲》,但比迪斯尼的作品更精彩。美國絕不可能拍出這樣的動畫片。’”[3](76)“英國一家雜志認為這部影片‘具有中國獨特的藝術風格’。芬蘭報紙也說:‘它把動畫技術最杰出的特點和傳統的東方繪畫風格結合在一起’,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部影片創造了美術片輸出的最高紀錄,到目前為止,已在44個國家和地區映出。1983年6月,《大鬧天宮》又轟動了巴黎,12家影院聯合首映,僅一個月時間,觀眾已近10萬人次,這在今天的巴黎,這樣的成績是令人驚嘆的。《人道報》說,它是‘動畫片的真正杰作,就象一組美妙的畫面交響樂’。《世界報》說:‘《大鬧天宮》不但具有一般美國狄斯耐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藝術又是狄斯耐式的美術片所做不到的,即完美地表達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4](74)從此之后,中國的動畫創作就基本上以此作為動畫的創作方向和創作目標,或曰:其已成為一種動畫創作的“摹本”,所以,這一時期在審美趣味和美學追求上都以該片為典范,在“臨摹”方式的創作中也必然會出現保守自足的創作危機。在創作思路上開始停滯不前,題材運用上也出現了簡單重復的創作趨向,表現形式上也固化在民族元素的表層借鑒上。所以,在1987年法國阿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上,中國選送的《金猴降妖》等三部作品皆無緣獎項,并被評委指為“故事冗長”,“手法陳舊”,而且,阿納西電影節的評委中一半以上的人持此意見。[5](6-10)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觀念越根深蒂固就越容易形成一種固態化的藝術范式,也越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個反面,即表現為內驅力不足的創新枯竭和停滯保守的創作態勢。面對這樣的思想阻隔,我們將采取怎樣的方式來作出積極的進路選擇呢?
三
“一種藝術、一種文化,只有它是可交流的、可增長的,它才會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地域性的民族藝術也是這樣。”[6](233)在中國六十年代的民族動畫作品中,就具有著這種開放的交流潛質和藝術表現,所以在與世界的對話與交流中,才顯現出自己獨立的人文品質和藝術追求。從中國動畫民族創作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明晰地看到,從民族口號的提出到輝煌階段中國民族動畫的自由創作,都是以開放和交流的姿態來進行創作的。在縱向上,我國的動畫創作不僅可以靈活地運用動畫的創作手法,也可以自由地借鑒傳統各門類藝術的精華。在橫向上,中國的動畫藝術跨越了諸多域限,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的文化,在民族的基礎之上憑添了時代的風貌和特征。這樣在雙向維度上的交流和發展,使中國民族動畫獲得了更進一步的提高和飛躍。
同樣以《大鬧天宮》為例,該片對傳統民族藝術進行了大量的借鑒,它的成功并非以內容的翻空出奇、表現手法的民族借鑒所取勝,而是其所孕育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交流和融匯中所獲得的一種價值的張揚。當該片被送到其他西方國家所播映之后,人們除了對精巧的創意,(如開頭部分花果山的小猴子們,將水簾洞的水象來開帷幕一樣地將水向兩邊拉開)民族化的表現形式(如程式化的表演風格、京劇化的臉譜、以及從廟宇佛像、剪紙木刻、年畫等民間藝術的借鑒等)的欣賞外,還對主人公的塑造產生了認同。我們知道,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觀念中,具有著反傳統、反歷史、反理性的傾向,崇尚自我,追求個人體驗和個人的主觀感受,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再來品讀《大鬧天宮》這部作品,必然會在交流中產生文化上的自由張力。一個呼喚自由、追求自我、個性張揚且藐視強權的叛逆形象與其內在思想所同構,從而在消解異質文化的過程中,建構起更具跨越性和認同感文化意義。所以,《大鬧天宮》被世界范圍所交口稱譽的本質原因,是在交流中引起了不同文化的交融,產生了具有交流和增長資質的審美新視界,從而作品中不僅體現了民族的文化范式和審美情趣,而且在交流的過程中也升華了作品的文化價值。
“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如果喪失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就會迷失于異文化之中,只有以自身的文化作鋪墊,藝術才有生命的基礎。”[7](72)當然,這種鋪墊是在交流和開放的基礎之上所孕育和形成的。具有中國民族特性的動畫作品,必然在創作中會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由于文化本身將向著開放與吸收的視野進行不斷擴展和豐富,所以,中國民族動畫的創作及所展現出的審美內涵和審美理想以及所體現出的文化心理和人文情懷,也將會隨著時代與文化的變遷而呈現出多維度的拓展及演變,只有在這樣的交流與融合中,才能使中國動畫更具有獨立的文化品格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從而確立和實現自己的文化身份。
對于傳統我們應該繼往開來,不斷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探求出本民族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取向,從而在動畫作品中體現出本民族的審美理想與藝術旨歸。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要關照到民族化與全球化的對立統一,對民族文化既不故步自封,對世界文化也不頂禮膜拜,而應當用平等交流的姿態與世界進行對話。所以,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中,我們依然提倡民族性,僅管民族文化有著強大的典范性和一定意義上的反面束縛作用,但我們堅決不能放棄對傳統文化的自覺研究,“我們只能通過對話求同存異,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達到微妙的協調,在沖突與融合論之間獲得一種良性的參照系。……倡導東西方之間的真實對話,以更開放的心態、多元并存的態度、共生互補的策略面對東方和西方。”[8](191)所以,中國民族動畫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并不是單一形態的發展格局,應該呈現出多元、交流、包容的發展傾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不斷從其他領域中吸取和借鑒新的內容,從而使作品更加適應當代人的審美心理和審美需求。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對話與交流所達成的一致目標,完成本土動畫藝術的新增長和新跨越。
[1]韓競.中國動畫片的審美情趣[J].南京藝術學院2004年碩士論文.
[2]宋生貴.傳承與超越:當代民族藝術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張宏.中國動畫電影鼻祖萬氏兄弟和 <大鬧天宮>[J].電影藝術,2005,(6).
[4]張松林.尋覓美術電影民族化的足跡[A].中國電影年鑒1985[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
[5]張松林.中國動畫片在阿納西電影節未獲獎后的反響[A].中國電影年鑒1988[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
[6]宋生貴.塞上風景[M].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
[7]鄧波.傳統或現代:中國動畫片的選擇[J].四川: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3).
[8]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