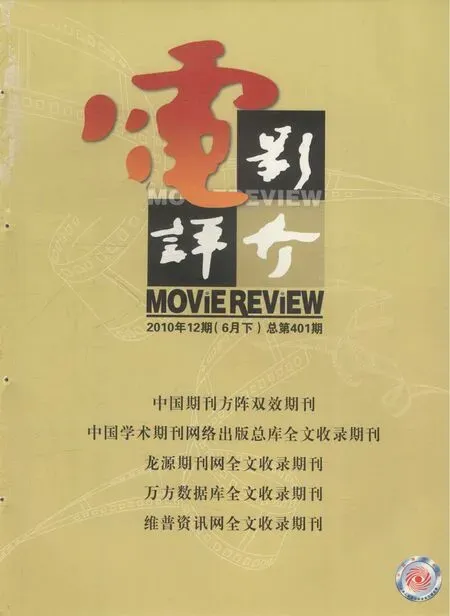淺談麒派藝術
京劇流派,是京劇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京劇表演藝術高度成熟的重要標志。京劇表演藝術的流派以藝術家的表演風格為基礎,各流派相比較而存在、相競爭而發展,并進而體現在藝術家群的表演之中。
在京劇的老生流派中,就有譚派、余派、楊派、奚派、言派、高派及“南麒北馬關外唐”等等。“南麒”指的是上海的周信芳大師,周先生的藝名為麒麟童,所以其創造的藝術流派就被業內稱之為麒派。我是一名青年京劇老生演員,雖然遺憾沒有機會對麒派表演藝術進行系統的學習,但我對麒派藝術卻情有獨鐘。
我對麒派藝術的熱愛源自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觀看了兩部周信芳先生生前拍攝的電影——《坐樓殺惜》和《徐策跑城》,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我被周先生那充滿張力、蒼勁渾厚的麒派藝術深深吸引住了。從此,我開始關注并漸漸喜愛上了麒派表演藝術,并慢慢對麒派藝術有了些許的理解和體會。
麒派唱腔的咬字嚴格恪守傳統的字韻規范,不是為唱而唱,不是賣弄技巧,而是從劇情出發,是為了充分地表達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感情,從人物的內心深處出發,從塑造和刻畫人物入手,為揭示戲劇矛盾而服務,因此,無一字不緊扣著人物的心弦,無一腔不從人物的情感流出。其實著意從人物情感出發來塑造人物,是我國戲曲的優良傳統,麒派則是繼承和發展最好的典范。麒派唱腔呈現給觀眾和聽眾的是強烈而又鮮明的藝術風格,感情真摯、充沛而飽滿、字字真切、句句傳神、嗓音渾厚、鏗鏘有力、蒼涼中有韻味,剛勁中顯柔韌,直抒胸臆,動人心魄,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強烈的震撼力。
周先生的嗓音雖然沙啞,但是演唱富有感情,其唱腔挺拔蒼勁、念白清晰、咬字頓挫富有音樂性。尤其是他吐字收音和潤腔、避短的技巧非一般演員能及,所以他不但不以字害腔,反而有以聲傳情之妙。聽周先生的唱腔酣暢樸實、蒼勁而雄渾,其特點十分明顯,加上起伏頓挫、錯落有致的念白,真是令人賞心悅目。周信芳大師曾對王金璐先生說過:“我嗓子不好,只能對付著唱。別人有一條好嗓子,卻不考慮自己的條件,偏要學我的唱法,豈不可笑!不能專把嗓子不好的青年人交給我培養,難道學我的戲路的人就可以不要好嗓子嗎!”雖然周先生的嗓音條件并不理想,但他能根據自己的嗓音條件創造出不同凡響的、感人動聽的麒派藝術,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麒派的唱腔極重視人物思想感情,不為西皮、二黃諸多板腔形式所限制,真正“歌能為感而發”。周先生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善于利用并正視自己的不足,使之成為自己的特點。周先生不僅善于唱高撥子或漢調,也不光是唱《斬經堂》和《追韓信》這些自己的看家戲,就連一些傳統重頭的唱工戲如《逍遙津》、《珠簾寨》、《文昭關》、《魚腸劍》也無一不唱。甚至《四郎探母》生旦“對啃”的快板,《秦香蓮》中的王延齡和包拯等,他都能唱出自己的風格特點來。
周先生的念白,是麒派藝術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念白清晰、犀利,口勁之足,吞吐頓挫節奏鮮明,情緒飽滿,蓋口緊湊,并十分講究音樂性;更重要的是有深厚的內在感情,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周先生不但把念白念活了,還使它性格化了,有時連“嘿嘿”一聲冷笑、“唉”的一聲長嘆,也無一不傳神,有理有情,它和麒派的唱、做、打一樣,同樣是塑造人物的有力手段。
周先生在做工和身段方面更是有口皆碑,其灑脫的身段有著一種難得的節奏感和可貴的張揚氣勢。他善于通過外部動作表達人物內心的感情和思想變化,“踢蟒”、“抖袖”、“彈髯口”等等表演技巧在他的運用之下均能深入人物骨髓,將程式動作與寫實的生活動作有機的結合,而少有為程式而程式的賣弄。例如《清風亭》中的張元秀在妻賀氏碰死在清風亭后,此時張元秀悲憤交集,亦決意碰死,于是奔向柱子,以頭碰柱,感到十分疼痛,單腿朝后退,雙手扶頭,又跪著向前移到臺口,接著,向天叩頭,表示對天作無言的控訴,又用手指天、指地、指手中的二百個銅錢,指張繼保、指賀氏的尸體、指自己的心,然后向后“僵尸”倒地死亡,在這段表演中,雖然沒有一句臺詞,這一系列的形體身段將人物的內心表現得淋漓盡致,動人心魄。
麒派的另一個特點是在表演中有一種特殊的含蓄美,在特定的時間通過一個微小但具有強烈震撼作用的動作來達到使視覺亢奮的效果,這種表演方式,柔中帶剛,通常大家都會覺得"很有勁",這是由內力表現到外力的結果。
麒派藝術的再一個特點,是把程式融在生活化表演中,即既要體驗人物內在的思想感情,又要運用程式的藝術手段來進行表演,讓表演既生活化又處處不離程式,這就是麒派藝術的高深之處。
周信芳先生一生不斷的學習、實踐、摸索,不但吸取了譚鑫培、孫菊仙、王鴻壽、汪笑儂、苗勝春等等老先生的藝術,同時還吸取了其他行當和一些地方劇種的特長與精髓。在創造麒派藝術的過程中,周先生極其重視中國傳統藝術審美理念和京劇本身的傳統法則,所以他在創新中從不出規范,但卻能在不出規范的前提下把“四功五法”與傳統“法則”運用到最佳,使他所創造的人物鮮活、生動、豐滿,與觀眾產生共鳴。周先生這種遵循傳統、鍥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就是留給我后輩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