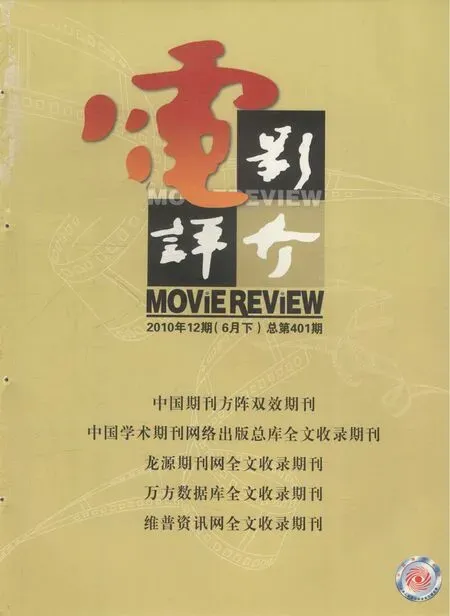許鞍華的影像敘事——談《半生緣》的改編
電影和文學(尤其是小說)的聯系是這么地緊密,遠遠超過了電影與其他藝術聯系的緊密程度。“把小說的敘事因素,把它那種從現實關系及其矛盾運動中刻畫人物性格、透視人物心靈的藝術可能性引進電影,這是電影藝術在對諸種藝術進行綜合中所取得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進展。”[1]文學向我們揭示了心靈,而電影則為我們展示了形象。
上世紀80、90年代以后,影視導演的改編開始傾向于現當代的一些作家作品,在香港就出現了對張愛玲作品的成功改編。它們是:1983年香港女導演許鞍華改編的張愛玲的成名作《傾城之戀》,1988年臺灣導演但漢章將《金鎖記》改編成的《怨女》,1994年關錦鵬的《紅玫瑰與白玫瑰》,1997年許鞍華的《半生緣》,1998年侯孝賢的《海上花》。
電影《半生緣》(1997年),改編自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這是許鞍華第二次改編張愛玲的作品。對于名著改編,雖然是從一種藝術形式到另一種藝術形式的轉換,但改編本身就是一種解讀,是一次新的創造。電影《半生緣》是許鞍華理解的《半生緣》,而不是張愛玲的。在電影中導演只有知道自己要講什么,才能真正講得好。那么要使影片“有戲”,就要對原著進行恰當地修改,敢于依據現代人的審美心理、審美需要和電影自身的特點對原著有取有舍,創造生動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節。
一、敘事視角及順序的改變
“確定從何種視點敘述故事是小說家創作中最重要的抉擇了,因為它直接影響到讀者對小說人物及其行為的反應,無論這反應是情感方面的還是道德觀念方面的。”[2]“敘述人稱從表面上看是解決指代的問題,而在實質上是敘述視角的選定。從敘述稱代上選定視角,有你、我、他的人稱視點;從敘述方位上選定視角,有仰視、俯視和平視;從敘述的層次上選定視角,有表層敘述(行為敘述) 和深層敘述(心理敘述)。”[3]
小說由于和電影同為敘事性作品,都要展現環境、刻畫形象、鋪敘情節,小說遂成為電影改編的主要來源。世界上著名的影片,絕大多數改編自小說。誠然,同一故事,能用不同模式(如小說、電影、戲劇等)加以敘述,而且“說法”并非相同,但重要的并非是所敘述的故事,而是敘述故事的方法。
在《半生緣》這部小說中,作者張愛玲選擇了全知全能的傳統小說的敘述視角,她的視點和當時的政治氣氛基本無關,她只是想用自己的筆寫一些舊事和“凡人”。所以,選擇這樣的視角從一開始就有了俯視的味道, 整個社會或所有人物基本都處在一個被描摹的地位,敘述人俯瞰全局無所不知。《半生緣》不以故事“開端時間”為起點進行順序敘述,而偏離“現時敘述”采用追溯過去的敘述方式。小說以世鈞十四年后的感悟開始回憶,回到十四年前曼楨、叔惠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時光。著力營造出一種悲凄、蒼涼之感。敘事學認為,時間的距離感容易使文本與接受者之間產生悲劇效果,該文本即是用遙遠的過去調動讀者的好奇和聯想,淡淡哀愁和憂郁氛圍自然營造,不留痕跡。
《半生緣》第一章的開頭是這樣的:“他和曼楨認識,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來倒已經有十四年了——真嚇人一跳!馬上使他連帶地覺得自己老了許多。日子過得真快,尤其對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顧間的事。可是對于年輕人,三年五載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楨從認識到分手,不過幾年的工夫,這幾年里面卻經過這么許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樂都經歷到了。”[4]小說開端是典型的第三人稱敘述,全知視角。此時,敘述者似乎試圖將讀者帶入男主人公的世界,去了解他的心理和故事。這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策略。然而,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作家又從作品里慢慢引退出來,變成有節制的敘述,作者通過“顯示”的敘事方式將故事與人物和盤托出,而作者自己的聲音從作品中消失。
十多年的情緣,張愛玲采用了一系列情節推動故事的發展,對傳統言情小說中的從相識——相知——相戀——誤會——消除——圓滿結局進行了顛覆。張愛玲的小說很少用大喜大悲來收場,她將世俗生活還原,揭示人性的普遍與深刻。“張愛玲在高潮來臨時每每筆鋒陡轉,避開人們預想的常規結局”[5],曼楨與世鈞的重逢,只能是“回不去”而徒增傷感,叔惠和翠芝的會面也只剩凄涼情緒的余繞,重逢卻無法圓滿,這是人生最大的無奈和缺憾。
對于電影《半生緣》,許鞍華將這部小說的內容納入了100多分鐘的電影中,對小說的敘事視角及敘事順序作了精心考慮。片中,許鞍華采用了男女主人公的視角交叉敘事。先用女主人公曼楨的畫外音引出男主人公世鈞:“他來城里已經好幾個月了,我一共見過他四次,每一次他都像看不見我,可能是他太專心做事吧,根本就沒留意旁邊的事情。”觀眾可以從這句話里聽出女主人公內心的不確定,進而設下一個小懸念。在這里旁白起到了強大的敘事功能。接下來四個鏡頭之后,視角轉變,男主人公上了電車,當路過多年前的那條街道時,久遠的記憶開始浮現,畫外音:“年輕的時候,我做過許多無聊的事,也見過許多過后就忘記的面孔。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我面前出現”,一個全景后,鏡頭搖著進入了小飯館,一個特寫鏡頭凸現出曼楨,反映出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的關注和重視,回答了先前的疑問,也解決了預設的懸念。電影從這兩個視角敘述著男女對方的故事,同時向觀眾表露了男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這兩個視角交叉進行,相當于一個全知全能視角。又如,影片進行到十多分鐘的時候,導演在倆人感情進展中加入的第二次旁白——世鈞:“我發現當你沒想過愛一個人的時候,其實你已經愛上了她……我想要去看她,卻一直找不著借口。”曼楨的旁白是:“我一直擔心叔惠會來我家拿鑰匙,我想每一個人總會有些事情是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世鈞已然愛上曼楨,而曼楨則開始擔心自己不堪提及的家庭是否會影響到這段感情。同樣是兩個視角交叉進行,幫助觀眾理解人物的內心,這是一種更貼切原小說的手法——讓人物直接用非對話話語來表達內心。張愛玲小說的況味,除卻影像,有些是只能還原為文字的。電影所采用的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敘事方式,通過劇中人的“眼睛”將他們的心理活動一一交代出來,使接受者處于劇中人物的位置,這就造成了接受者心理自居作用和想象性認同,引領著他們的觀看情緒。電影充分把握住了兩個主角的心理,使故事具有一種飽滿的可信性。影片貼切地進入主人公隱秘的心靈深處,真實地感受他們的思想。
在小說中采用的是倒敘的手法,回味過去的一段故事,客觀敘述和人物主觀感受交融。而電影則打破原著的敘事順序,總體上以曼楨和世鈞相識、相愛、分離、重逢為序,時間上先后承繼,這樣更符合電影藝術的敘事方式和觀眾的心理習慣。但是許鞍華在故事整體框架內部運用的是倒敘的手法,如影片開始不久用旁白這種能給人一種恍如隔世之感的方式,插入了世鈞在電車上對曼楨的回憶;用閃回通過曼楨的母親、奶奶的對話,交代曼璐與豫瑾的故事,這也為后面曼璐的心理刻畫做下鋪墊。這樣的順序與倒敘相交織的手法,使觀眾在體會倆人感情發展的同時又時不時被導演拉回現實中,對這段緣分保持有一種客觀、冷靜、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的態度,能更深層次闡釋出張愛玲原小說中蒼涼的味道。
二、情節場景的選擇
從敘事角度看,小說和電影都是講述故事的藝術。何謂故事?故事是敘述出來的事件。李幼蒸指出:“人類生活由各類事件組成。事件,即有目的的人的心理活動與行為及其結果;無數事件在時間和空間內的組合即歷史;對歷史的部分或全體的描述即歷史記敘。記敘的對象可以是真實事件,但也可以是想象事件,后者即為通常所說的‘故事’。”[6]而故事是由情節講述出來的。但是電影一兩個小時的長度決定了電影改編必須對小說的故事情節精挑細選,這即如菲爾德所提示的:“要精心地挑選那些事件,從而使它們能通過最好的視覺能力與戲劇性成分來描繪你的故事,使它們趣味盎然。……原始素材畢竟只是原始素材。它只是個起點,而不是終點。”[7]一般來說長、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尤其是改編長篇小說時,必須對書中的事件及人物關系恰當地進行選擇取舍,以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矛盾,從而實現敘事目的,揭示敘事意義。這就需要改編者對小說進行徹底的重組,確定主線。是否需要添加一到兩條副線,這要因人物、情節而定。
小說《半生緣》為電影《半生緣》的拍攝提供了豐富而有深度的文化資源及廣闊開掘的空間。許鞍華對小說中的事件、人物、敘事順序進行了精心取舍,挑選出最重要、最吸引人、最具表現力的場景、事件和人物,連綴成完整的故事,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其中也不乏原著的蒼涼和細膩,也是導演的個性體驗和對生活的領悟。整個影片以曼楨和世鈞的愛情、經歷為主線,曼璐與豫瑾、叔惠與翠芝的感情糾葛為副線,由一個個細膩的場景、鏡頭和畫面連綴起來,舍棄枝蔓情節。使敘事更具體、集中、緊湊,步步推進,一氣呵成。
影片用很長的畫面仔細地敘述了世鈞、叔惠、曼楨到郊外拍照,曼楨丟失紅手套,世鈞趁夜深人靜時獨自到郊外,借手電筒微弱昏黃的光亮,為曼楨找回手套的情節。其實在這要表現的是,世鈞在一片漆黑中尋找的豈止是曼楨的紅手套,還有他期待已久的愛情和幸福。送還紅手套,不僅成為世鈞向曼楨表白心跡的契機,也為故事的發展做了鋪墊。郊外灰黃的色調,輪到世鈞、曼楨照相時卻沒了膠片,突然下起的小雪,似乎都暗示某種凄冷、遺憾的結局。世鈞、叔惠、曼楨第一次在小飯店用餐,曼楨幫二人洗筷子,世鈞因過度緊張,無意間把剛洗凈的筷子順手放在骯臟的桌上,并誤飲了涮杯子的茶水,一個活脫脫的靦腆內向、手足無措的沈世鈞躍然而出;祝鴻才指著曼璐的相片問:“這是你妹妹什么時候照的”,曼璐一邊痛心地說“我真的老得那么厲害嗎”,一邊沖到穿衣鏡前,捧著自己濃妝艷抹的臉龐仔細端詳的一幕,把一個容顏即逝、希望和信念隨時光的流逝漸漸遠去的風塵女子的形象,真切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世鈞和叔惠回南京的前一晚,曼楨來到許家,帶來一盒點心并幫世鈞收拾行裝,兩人貼近地細語,有幾分柔情,也有幾分羞澀,曼楨一聲“你忘了把熱水瓶蓋上了”,有意打破這個局面,貼切地展現他們不溫不火、含蓄內斂的感情……影片通過環境、語言、動作、背景、造型,展示這些耐人尋味的情景,細膩刻畫出人物性格,完整地交代了情節線索,在瑣屑和細微中透射出蒼涼感。
電影改編是將一種藝術形式轉換成另一種藝術形式的藝術創造。它既要忠實原著,又要有導演今天對藝術形象的再認識。那么在電影改編中要善于把握好藝術分寸,處理好對原作的刪與增。但不管怎樣的增減,都要符合原著的精神。
先說“刪”。盡管在改編時刪除原作的某些內容,必然會損害原著,但這種刪減還是十分必要的。從篇幅上說,一部中篇小說改編成一部影片容量剛好,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成一部影片,就勢必要刪減原作中的一些人物、情節和線索。
許鞍華為使故事情節線索簡潔明晰,在電影《半生緣》中略去小說中許多次要情節和事件,簡化了很多人物形象。比如本來就曖昧不明的許石戀,電影里只有三場戲:劃船、爬山、婚禮,簡單地交代清楚,含蓄又精到。小說中,世鈞與叔惠回南京探望,沈母、世鈞嫂嫂及其他親戚竭力撮合他與翠芝的婚事。第二天,世鈞、叔惠、翠芝同去一鵬家赴約,被支去看電影。翠芝不慎折斷鞋跟,無奈中,世鈞回石家幫她拿鞋,回來時電影已近終場,他負氣扔下許、石二人,獨自補看錯過的半場電影。許、石單獨去玄武湖游玩,由此滋生一段隱隱約約的戀情。而電影將其簡化為三人同游玄武湖時,翠芝折斷鞋跟,于是世鈞回去幫她拿鞋,叔惠和翠芝單獨泛舟玄武湖,二人后來通信一事也被省略。有些時候電影為了情節的緊湊,一些次要人物乃至重要人物也要刪剪掉。一部電影中的人物不能太多,主要人物一般是二至三個,而小說中可以根據需要設置很多個主要人物,并表現其錯綜復雜的關系。如沈父、沈母與沈家姨太太的糾葛,祝鴻才與曼楨結婚后再發國難財,繼續花天酒地等情節,電影均淡化處理。許先生、許太太、世鈞嫂嫂、阿寶等小說中著墨不多者在電影中都是“蜻蜓點水”,只是作為某種符號存在。而石太太、沈家姨太太、金芳等次要人物,則根本沒有出場。
電影中對于曼楨受辱那場戲,拍到她半夜驚醒就戛然而止,與小說里“有人在這房間里”的恐怖氣氛相得益彰。許多枝節也大膽地刪去了,比如世鈞父親的病,曼楨逃出醫院的詳細過程,張豫瑾在上海生活的那部分,等等。電影的結局是:世鈞與曼楨重逢,百感交集但又無可奈何。鏡頭一轉,又是多年前那個初春的黃昏,世鈞打著手電找到了曼楨的紅手套,揀起來,輕輕地笑。那樣一張年輕的臉,那樣一顆年輕的心,世界在他面前還很美好。
再說“增”。將一部時間跨度達十多年的長篇小說搬上銀幕,需要取舍的素材太多了,稍有差池,就可能傷筋動骨,破壞整體結構。在這里,編導下了一番苦功,除了刪除一些情節事件人物之外,基本保留了原著小說的故事脈絡,同時還增加了一些小說中沒有的情節,如:張豫瑾為了顧曼璐悔婚去做舞女而跟人斗毆;顧曼楨為沈世鈞買手套。前一段出現在顧曼璐的回憶中,表明她是為了家庭迫不得已才淪落風塵,在她的內心一直為自己的犧牲而耿耿于懷,為后面對妹妹的報復提供合理的心理基礎。后一段則是顧曼楨的投桃報李,沈世鈞曾為她深夜去荒郊野外去找尋丟失的手套,由此,兩人開始漫長的十八年愛情長跑。此后,這雙始終未能送出的手套作為劇中的重要道具見證了兩人感情的起起落落。此外,還有細小情節上的增加,比如沈世鈞初見顧曼楨顯得手足無措,慌亂中端起曼楨洗過筷子的茶杯喝了一口,叔惠笑著指出后,他連說沒事,曼楨調皮地說,那你再喝一口。憨直的他居然真的又喝了一口。
除了對原著小說的故事情節做出合理的增減之外,影片還對其中的對話與細節做了修改,以適應電影藝術特有的視聽要求。比如在小說中是在出發前,顧曼楨就發現了沈世鈞臉上的污點,而在影片中是在拍照時她才看見,特地跑到他的身邊替他擦去。電影首先是視覺的藝術,影片正是要顧曼楨通過她顯而易見的肢體語言形象地表現出她對世鈞的關心。再比如顧曼璐騙他曼楨已結婚,并退還他倆的訂婚戒指。在小說中他出門不久就扔到路邊的荒草叢中,而影片卻是在他走水路護送父親的靈柩回南京途中扔入水中,使得他扔戒指的行為更具有象征意義。
三、環境、人物心理的刻畫
電影中細致地刻畫人物一般比較注重兩個方面,一是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二是環境描寫的襯托。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描寫是改編者遇到的更大的難題,它既不能晦澀難懂,也不能直白無物,心理活動的展現更多的是要和觀眾產生內心的共鳴,這就需要用電影鏡頭語言來解決。在小說中是較容易也傾向于揭示人內心深處的秘密的,電影則不然。對此,悉德?菲爾德說得較為中肯:“一部小說通常涉及的是一個人的內在生活,是在戲劇性動作的思想景象中發生的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緒和回憶。在小說中,你可以用一句話、一個段落、一頁稿紙、或一個章節,來描寫人的內心對白、思想、感情和印象等等。小說時常發生在人物的腦海內”;電影“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體的細節……是一個用畫面來講述的故事,它發生在戲劇結構的來龍去脈之中”[8]。但是電影在它的探索道路上,運用聲音等電影語言實現了很好的轉化,也摸索出了一些可以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途徑。如畫外音中的內心獨白、旁白,再如明暗冷暖色彩的渲染等等。
影片充分運用了電影的各種表現手法來發展故事情節,展現人物心理活動。比如影片開始時先用曼楨的畫外音引出世鈞:“他來城里已經好幾個月了,我一共見過他四次,每一次他都像看不見我,可能是他太專心做事吧,根本就沒留意旁邊的事情。”從這句話里可以看出曼楨內心的不確定。又如沈世鈞要回南京,顧曼楨來替他收拾行李,兩人對話到一半,突然插入他坐在北上的火車上微笑沉思的畫面,然后又回到他倆的談話,最后再接到他在南京坐人力車上回家的畫面。如果按照正常的時間順序來組織鏡頭也沒有錯,但時空打亂以后,臨別這一段就變成甜蜜的回憶,這時兩人關系尚未明確,她能不避嫌跑到叔惠家來替他收拾行李,足以表明她的態度。再比如沈世鈞第一次來顧曼楨家吃飯,飯后送她去補習,他第一次牽著她的手,向她表示愛意,來到補習家門口,他舍不得放手,又拉著她往回走。最后時間到了,無奈兩人只得松手,他眼看她走進門去,一個人慢慢地走到路口,遠處傳來歡樂的音樂,路燈投下紅彤彤的光芒。他坐上電車,從那家門口經過,只見里面透出一片奇異的紅光。影片在這里運用特殊的聲、光、影處理手法將沈世鈞初嘗愛情滋味、喜不自禁的心理直觀地表現了出來。昏黃的燈光,溫暖的調子,夜市有點喧鬧的人聲,加上小提琴優美舒緩的伴奏,倆人之間那種柔情蜜意被細致地表現出來。等到曼楨走進門去,世鈞循著一下子凸顯出的熱鬧音樂聲來到一片亮處,小提琴的舒緩變成了歡快的節奏,燈光也變作喜悅的紅色,鏡頭拉近,笑容在世鈞臉上散開。他內心在激情興奮與美好的期望中被渲染得淋漓盡致又不失含蓄。這一點是文字無法達到的效果。此外,曼璐與豫瑾重逢,欲與他再敘舊情,她蹲下身去替他撿錢,張卻一再申明,想起過去真是幼稚。她不禁愣在那里,兩人前后景一蹲一站,在一個鏡頭中便交代了兩人過去的恩怨情仇以及當下各自的復雜心態。還有顧曼楨被姐姐囚禁后,整理家里送來的衣物,翻到她買給世鈞的手套,這時一個上升的鏡頭將她背后窗外正往外走的世鈞的背景納入畫面。
電影《半生緣》,作為一件藝術品,作為一個改編經典原創小說、具有創新意識的電影,無論它是否具有經典性,都已變成具有當代閱讀意義的對照性研究文本。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改編過程中,許鞍華導演并未只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拘泥于小說,從敘事順序的改變到情節的選擇調整等等,都是以適合電影的聲畫表現及觀眾的接受為目的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些改動確實損傷了小說的豐富、多義與厚重,存在一些不足,但有很多地方還是優秀的。但我們對改編影片的評價,不能只以是否忠實于原著為標準,而應從電影的角度、從聲畫語言的影像化表現上,用與普通影片同樣的眼光來衡量得失。
[1]許南明,富瀾,崔君衍主編.電影藝術詞典(修定版).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第101頁
[2]戴維洛奇. 小說的藝術[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3]毛克強, 袁平. 當代小說敘述新探[J ].當代文壇,1997(5),12頁 .
[4]張愛玲.半生緣.選自陳子善主編《張愛玲文集》. 第一版.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第1頁。
[5]章渡. 反高潮――張愛玲小說的敘事風格[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4)
[6]李幼蒸.當代西方電影美學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51-152頁
[7]悉德?菲爾德.電影劇本寫作基礎.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第144頁,第154頁
[8]同上,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