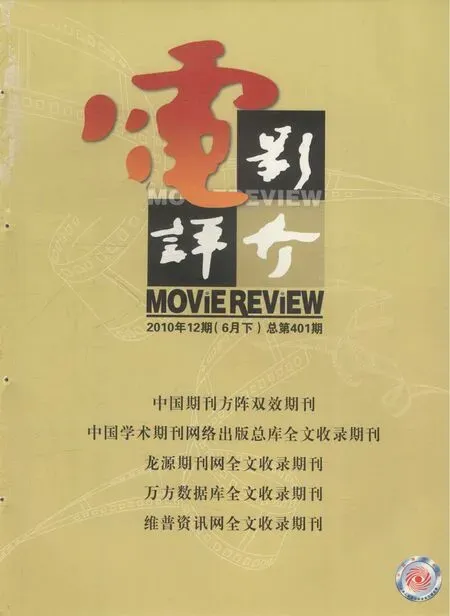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他”的成功可以復制——從結構主義視閾重品《阿甘正傳》
一、引言
運用于電影作品的分析,結構主義是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同時也是一種分析方法出現的。他對于作品的關注從內容分析轉向形式的研究,熱衷于剝離紛繁復雜的表象剖析出深層結構。作為一種文化思潮,結構主義側重社會道德和歷史文明的反叛與挖掘,他宣揚社會性和平衡式的制約方面,而不強調個性和創造性的方面。
《阿甘正傳》(Forrest Gump),是一部根據溫斯頓?格盧姆(Winston Groom)同名小說改編的美國電影,自上映以來一直廣受熱議,電影榮獲1994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等六項大獎。影片主人公阿甘智障的缺陷與豐盛人生的強烈碰撞極大地沖擊了人們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而“甘式成功之道”更成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思維謎題。從結構主義的理論視角切入,對被影評家們譽為“美國的文化寶典”的《阿甘正傳》進行剖析,探討其核心元素和對立關系,以及影片藉以傳達的深層文化和精神內涵。
二、關于結構主義
(一)結構主義的發展與定義
作為文學作品分析方法的一種,結構主義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藝》,其中包含了對文藝作品結構的分析研究。結構主義強調,任何一個文化系統內的每個元素均是從該元素與同一文化系統中其他每個元素的關系里獲得意義的。
伯特?麥認為:“結構是對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選擇,這種選擇將事件組合成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序列,以激發特定而具體的情感,并表達一種特定而具體的人生觀”。[1]許多學者也都曾從不同的層面給出結構主義的定義,著名學者霍克斯談到:“結構主義根本上是對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主要關注結構概念及對此加以描述。”[2]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及其相關理論對結構主義產生了巨大影響。索緒爾的差異論,即從差異出發建立起二元對立,并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結構觀,是結構主義思想的基石。[3]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之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 Strauss)將結構主義方法論應用到人類學和神話學等領域中,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結構主義思想本身,也真正使結構主義成為一種文化思潮在學術領域產生影響。
(二)結構主義與文藝作品
英國評論家彼得?沃倫在《電影的符號與意義》(signs and Meaning in the Cinema,1969)一書中指出,結構主義方法論是用客觀的結構主義方法分析影片本身的意義和形式。在《神話與意義》一書中列維?斯特勞斯認為,任何表面現象背后都有一個特定的結構,只要能抓住這個結構,就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通過把分析對象解構為一些相對獨立的結構,然后在這些結構內找出它們的對立統一的關系,就會發現意義產生于其中。
結構主義者關注的不是現象本身,他們對現象的抽絲剝繭,目的是在二元對立系統中分析這個現象的基本結構,挖掘出深層次的矛盾結構,例如“生與死”、“存在與虛無”等。從本質上來說,結構主義就是一種透過現象抓本質的工具。[4]
三、結構主義分析《阿甘正傳》
(一)影片簡介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掀起了社會價值批判和重建思潮,倡導以保守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價值回歸。影片主人公阿甘是個智商僅為75的智障者,正是這一思潮中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傳統的絕佳體現。《阿甘正傳》是這一時期“反智電影”的代表作,它通過講述一個智商僅為75的智障者的成功人生,引發了觀眾對社會文化、宗教、道德、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深刻反思。面對艱難的人生旅途,“智障”的阿甘實現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成功。
(二)阿甘成功人生的對立結構
結構主義敘事風格的文藝作品往往存在表層和深層兩個結構系統。表層結構,也稱外結構,是指文藝作品可觀、可感、可聽的情節、對白、音樂等外在組織形式,即作品的內容;深層結構,也稱內結構,是指隱藏在外在組織形式下,蘊含豐富內涵和外延的系統即作品的意義。
而這種結構往往以二元對立的形式呈現。分解阿甘的一個個成功,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表層二元對立結構:智障—大學畢業,智障—越戰英雄,智障—乒乓明星,智障—事業成功,從人生的角度來看,影片全方位地展示了阿甘的成功,而他取得的所有成功似乎都與他的“智障”對立并貫穿了全片始終,這多個表層二元對立結構構成了整個影片的基本脈絡。
(三)阿甘成功的深層結構
結構主義認為,事物之間在深層結構上的聯系,恰恰比表層結構既事物本身更能體現事物的本質。潛藏于作品深處的結構更能支配和影響作品意義的生成。
“跑”是影片中一個最為意象化的鏡頭。阿甘的奔跑貫穿了他的成功道路,也成為整部影片重復率最高的鏡頭。不論時空如何更迭,阿甘總是專心地甚至不顧一切地奔跑,“跑”似乎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他從備受歧視的童年跑到了人才濟濟的大學足球場;從戰火紛飛的越南戰場跑到了乒乓外交球場;直到在單純的奔跑中飽覽金黃大漠、漫天紅霞的人間奇景,阿甘跑出了一個個成功。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貫穿整個影片的“跑”象征的是阿甘的執著。片中充滿了這樣的深層結構:執著于愛情—有情人終成眷屬,執著于承諾—成功的捕蝦船長,執著于友情—越戰英雄,執著于細節—刷新槍械裝卸記錄,執著于興趣—乒乓外交明星……而阿甘成功的核心秘密也由此顯露出來:執著是成功的基石。
(四)阿甘的成功之道
擁有了成功基石的阿甘又如何在他的成功之道上奔跑呢——深層結構的解碼:
1、執著于夢想
“智障”的阿甘并非擁有出眾的外表與非凡的智慧,甚至與公眾對成功人士的想象大相徑庭,雖然他不止一次的佇立在人生的關鍵轉折點,但都能轉敗為勝、化險為夷,讓我們不得不相信,阿甘的成功不是誤打誤撞,更不是上帝庇佑,而是他卻始終執著的追求人類一切美德,他善良、真誠、守信,堅信“愚蠢是愚蠢的行為”,并以此作為人生信條為之不懈努力的最好回報。值得反思的是,夢想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指引人奮然前行,也會讓人固執己見,誤入歧途。影片中的丹上尉就是前車之鑒。為英雄而英雄的丹上尉與為友情而英勇救助戰友的阿甘收獲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爭紀念品。
2、執著于信念
阿甘的成功與他執著的信念是分不開的,假設阿甘只是一味地信守承諾,卻沒有堅定的信念做支撐,夢想也只能隨著時光流逝成為泡影。對捕蝦業一竅不通的阿甘為了兌現與戰友巴布一起捕蝦的承諾,當上了捕蝦船長。阿甘在捕蝦路上不斷遇到種種障礙,這也許是命運對每一個成功者的考驗,從一開始只撈得上垃圾,到暴風驟雨中追逐蝦群,從每天堅持出航,到最終拒絕回航,無不折射出阿甘的執著信念。影片中這種人類永恒追求的信念卻奇特在這個二元對立結構另一面的丹上尉的重新振奮中得到升華。通過協助阿甘建立捕蝦的事業,丹上尉被阿甘的永不放棄感染,逐漸恢復了自尊與自信,重新站了起來。可見一個擁有執著信念的人不僅能救人性命還能拯救人的靈魂。
3、執著于踐行
阿甘最終的成功不僅得益于他人的關心和指導,更得益于自己執著的踐行。當阿甘被一群同齡孩子欺負時,珍妮關切地朝他喊道:“跑!”跛足的阿甘沒有片刻的遲疑,沒命地向前沖去,終于能自由的奔跑;球場上,教練告訴他:“接到球就跑!”他沒有絲毫的疑惑,結果他跑來了大學畢業證,成了“球星”;他初到越南戰場,丹上尉命令他:“遇見危險就跑!”他單純地服從了,不但平安歸來,還成為“越戰英雄”。把簡單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簡單,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只有執著的人才能把任務執行到近乎完美。
四、結語
在結構主義的視閾下,可以看到夢想、信念與踐行這三個要素在阿甘的成功過程中反復出現,影片中阿甘的成功都是由它們組合演繹而成的。這也反復提示觀眾,在去掉阿甘“智障”的外表之后,本片仍然是圍繞著傳統的勵志主題來展開的,即:執著是成功的基石。由于影片表層結構的幽默詼諧使觀眾對阿甘的成功之道的理解產生了很強的主觀性與任意性,這也正是為何從結構主義視閾下最終得出阿甘的成功之道——執著于夢想、執著于信念、執著于踐行,而有別于對阿甘諸如“傻人有傻福”、“吃虧就是占便宜”、“有舍才有得”等成功之道的解讀。可見結構主義對文藝作品的解碼過程是為了發掘人類心理、精神、文化、情感等層面的深層內涵。電影《阿甘正傳》的成功,在于劇本捕捉到成功的真諦與世俗觀念的各種對立,通過出色地展現阿甘的種種成功,回歸了真善美的普世價值觀,引發了觀眾的群體沉思。阿甘的成功才是真正可以復制的成功。
[1](美)尼克?布朗.電影理論史評[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55—56頁.
[2]Hawkes,Terence.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Barkley &Los Angles:U of California P,1977.15-17頁.
[3]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O06,269頁.
[4]潘國豪,《勇敢的心》電影結構主義解讀[J].電影文學,2010,第1期,9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