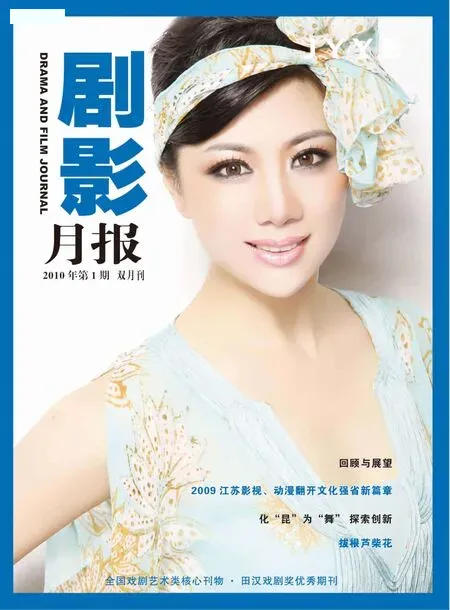西哈諾的什錦飯
——看日本戲劇《西哈諾》有感
■朱琰
西哈諾的什錦飯
——看日本戲劇《西哈諾》有感
■朱琰
法國的題材,意大利的音樂,日本的背景和表演,雖然是表面看似不著調(diào)的混合,然而卻令人耳目一新,回味無窮。也讓人們記住了一個名字——鈴木忠志,以及這個日本化了的話劇《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
全劇導(dǎo)演意圖非常明確,演員在嚴(yán)格執(zhí)行的設(shè)計下似乎都成了一顆顆跳動的,美麗的棋子。除了將三個國家的文化元素進行融合,導(dǎo)演處理的方式也是多樣的:對白的表現(xiàn)化,動作的電影化,切換的舞蹈化以及舞臺設(shè)計非常簡潔,從頭至尾沒有暗場等。
首先,是人物語言的處理。演員鏗鏘有力的咬字、噴口、吐字,雖然存在語言上的障礙,但卻聲聲直入觀眾心臟。尤其是扮演女主角羅姍妮的演員的聲音與語言風(fēng)格,完全顛覆了傳統(tǒng)日本女性在我印象里的那種輕柔與細膩。劇中的“羅姍妮”給人一種堅強不屈的剛硬外表,這點以她的語言風(fēng)格表現(xiàn)最為突出。以往我們見到的話劇女演員聲音普遍生理特點明顯,而劇中扮演羅姍妮的這名女演員聲音卻低沉有力。其他演員的語言風(fēng)格也同樣硬朗,低沉而憤怒。這跟導(dǎo)演訓(xùn)練演員的方法有關(guān),正如鈴木忠志自己所說:“演員的臺詞方式借鑒了日本能樂的發(fā)聲方法,聲音很低沉。在舞臺上我不會去區(qū)分男演員和女演員,對他們說話方式的要求是一樣的。”這種有別于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表演風(fēng)格的灌口式說話并沒有給人以單調(diào)枯燥的不適,反而有一種內(nèi)在的韻律和節(jié)奏。演員的聲音在一定程度上區(qū)別于單純的臺詞,常常無意中給人一種類似音效和節(jié)奏把控的融合感。整場演出演員表情并不十分豐富,幾乎全部以氣息對聲音力度和節(jié)奏的把握來表達情感,并且很少進行正面交流,比如開頭部分西哈諾和羅姍妮的那一段,兩人面朝觀眾,說話時幾乎沒有表情和身體面對面的交流。這一點也許與日本傳統(tǒng)的能樂和狂言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guān):演員扮演劇中人物,戴相關(guān)的假面具。有俗話說:“能樂是從選擇面具開始的。”即根據(jù)曲目和角色來選擇能面具,演員在出場前就要按自己的面型,準(zhǔn)備所戴面具的位置,因為演員戴上面具表演,開口、發(fā)生的時候,是不許上下顎動的,兩眼的視野也是有局限的,所以需要確定面具適合演員開口、發(fā)生、視線的位置等。可以說,演員戴上能面具表演,主要是靠動“心”,而不是動“身”,這是能樂不同于其他戲劇的演技基礎(chǔ)。在這場演出中,演員的表演存在著類似之處。演員的心理節(jié)奏把握得恰到好處,將每個點都準(zhǔn)確送到觀眾面前。
其次,演員的形體展示也是值得稱贊的。尤其是三位主要演員的表現(xiàn):每一個轉(zhuǎn)身、每一步走動,甚至每一次抬手、眼神……都干凈純粹,毫無任何拖沓。開場時分有一段精彩的打斗場面,西哈諾一人抵擋來自不同方向的武士的進攻,每一次出手隨著刀刃的刺殺停滯瞬間,被刺武士均以一種慢化過程的形體表現(xiàn)被擊潰,同時伴有夸大的呻吟聲。這幾乎是一種純電影化的表現(xiàn)方式:慢鏡頭、多視角,動靜有序,亂中有章,配合燈光與音效的變化,舞臺沖擊力很強。之后出場的五個武士配合意大利歌劇展現(xiàn)了一段精湛的“刀舞”,很好地將形體與自身職業(yè)特征結(jié)合,雄壯有力,每一個動作都完成得干凈漂亮。為了劇情的需要,同時明確舞臺支點,更好地配合燈光服化效果,在武士的出場呈現(xiàn)結(jié)束后,五名女性演員(亦是切換道具的工作人員)隨著音樂上場,配合豐富多樣的形體動作將五個方形木制坐墊和方形桌分別切換至適合的演區(qū)。之后,五名武士成四方一點的格局(四名分別坐于舞臺四角,領(lǐng)袖克里斯堅坐于四人構(gòu)成的矩形中心)分別坐于其上品茶嘗點。這期間的動作也做了一種風(fēng)格化的處理,包括抬手、咀嚼等都以一種反生活常規(guī)的慢速進行。另一邊,西哈諾與克里斯堅交流過程中,四名武士不時做出簡單反應(yīng):或轉(zhuǎn)頭,或停頓,或表情。關(guān)于形體的相關(guān)細節(jié)還很多,在此不一一贅述了。
再者,道具切換的舞蹈化。以往關(guān)于將切換置于燈光下進行的處理方式并不罕見,但很少見到能像《西哈諾》這樣將其結(jié)構(gòu)于戲劇整體,在不破壞演出節(jié)奏的同時還能將其處理為一種舞蹈化的舞臺畫面予以呈現(xiàn)。之前已經(jīng)說過全場演出沒有暗場,所有道具切換都在演出中直接進行,需要切換的道具也只跟五名武士直接相關(guān),所以切換人員一共也是5人(均為女性)。每一次切換時刻,她們都以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上場:或舞蹈,或走動,甚至期間還穿插有中國戲曲步法表演程式中的“矮子步”,形式多樣,又很富有觀賞性。尤為可貴的是,所有切換動作和過程均自然地融合到規(guī)定情境中,成為整出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其他演員的表演沒有絲毫影響,反而豐富了舞臺畫面的整體性。將道具切換上升到整體舞臺呈現(xiàn)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單獨構(gòu)成一段精彩的表演,這應(yīng)該說是導(dǎo)演的又一高明之處。
以上五名女性在承擔(dān)“切換工作人員”工作的同時,也是穿插劇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演員。可以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一種近似于“歌隊”的作用,只不過,她們更多是以形體來充實全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至于為什么不用“舞隊”形容,因為我個人認(rèn)為這不能將其簡單定性為“舞蹈穿插”。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一些劇目很多存在期間融入舞蹈元素的例子,但普遍還是以一種單純的舞蹈形式出現(xiàn),罕見能把它很好地融入戲劇整體。并且,劇中這五名演員的每一次出場用“舞蹈化的形體動作”來形容可能更為恰當(dāng)。在整個大的戲劇環(huán)境下,她們的存在與舞臺其他人物普遍的剛硬形成的強烈對比,尤其是與五名武士時而于某種情境下產(chǎn)生某種呼應(yīng)和融合。比如,在表現(xiàn)愛情與欲望的一段戲里,五名女性身著和服手持陽傘,分別站立于各個武士右側(cè),五名武士用一種“心靈外化”的方式配合形體、燈光、音樂等圍繞身旁的異性“舞蹈”。如此剛?cè)岵⑦M,交織巧妙。不管怎樣,他們的這種時而舞蹈、時而走動、時而靜止、時而間離,不斷穿插劇中,對全劇的情節(jié)發(fā)展起到了推動、銜接和畫龍點睛的作用。
最后,程式化的情境轉(zhuǎn)換。舞臺背景由遠至近不過就是參天樹下的突出一扇日式拉門的平面房屋,屋前一片花叢,一棵枯樹,還有舞臺頂端的一扇方形窗戶。從頭至尾除了前臺一些簡單的日用道具的切換,完全沒有其他景片的變化。所有的場景變換全部通過演員的表演和觀眾的想象實現(xiàn)。這在中國戲曲里是常見的,在現(xiàn)實主義話劇中卻是相對罕見的。當(dāng)然,導(dǎo)演鈴木忠志對這出法國戲劇的詮釋本身就不是現(xiàn)實主義的。總之,全劇無論從布景、服、化、道、效還是演員的表演,導(dǎo)演的設(shè)計,構(gòu)架都非常嚴(yán)謹(jǐn)有序。
應(yīng)該說,這是導(dǎo)演帶領(lǐng)我們進行的一次完全風(fēng)格化的旅行,內(nèi)容并沒有擯棄現(xiàn)實,但卻以一種我們意料之外的方式使用現(xiàn)實,用語言、舞蹈、布景、燈光等重構(gòu)現(xiàn)實。劇場性超越了劇作本身,以致于觀眾直接或間接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看戲,而不是在看某個人的真實生活。至少從我個人的感受來看,全場下來我并沒有因為劇中人物的悲歡離合而產(chǎn)生自己情緒上的波動起伏,沒有激動,沒有不安,沒有與角色同悲喜共命運。但這九十分鐘的演出卻是嚴(yán)謹(jǐn)和耐人回味的。導(dǎo)演把過去我們只能在鏡頭下或者通過其他媒介才能展現(xiàn)的瞬間在舞臺上詮釋得淋漓盡致,讓我們寧愿相信這是發(fā)生在劇場里的一次關(guān)于戲劇的奇幻魔術(shù)。而除去舞美等劇場性的考慮,這一切卻又僅僅是通過一個個演員的語言與形體來表現(xiàn)的,簡潔、清晰、明確。包括最后的謝幕,依舊沒有任何多余的動作,與全劇的風(fēng)格一樣,干脆利落又不失嚴(yán)謹(jǐn)。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日本話劇《西哈諾》給我的感受,我想說,這是一次在平靜外觀下的心靈沖擊,似微風(fēng)吹過,流暢、自然、清新卻又深刻發(fā)人深省。這樣的處理方法和表現(xiàn)手段或許可以給我們的當(dāng)代戲劇以某種啟示,值得我們?nèi)パ芯亢徒梃b。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