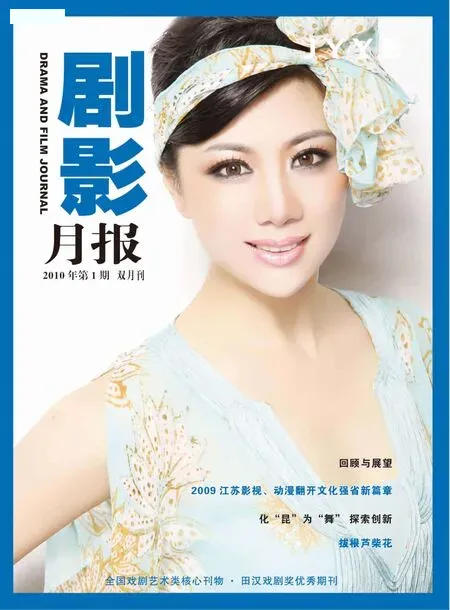對胡星亮教授關于戲劇“魂兮歸來”論述的一次辨證解讀
■濮波
胡星亮教授在《中國當代戲劇的“招魂”與“失魂”》的講座中給我們闡述了中國當代戲劇面臨的精神問題,從戲劇“靈魂”這樣的角度出發做了一次深入的探詢,也廓清了一些概念。首先,什么是戲劇之魂和人的戲劇?所謂戲劇之魂,即戲劇精神,也就是戲劇的現代性追求。新時期,中國戲劇走過了“招魂”、“鑄魂”、再次“失魂”的沉痛,因此,再次呼喚魂兮歸來,是一種當務之急。而要樹立這個概念,必須強調20世紀中國現代戲劇轉型的根本標志是現代性追求;強調中國戲劇生態格局已經從傳統的 “戲曲”一元結構發展到“話劇——戲曲”二元結構;強調20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追求,著重表現為精神內涵的現代意識。
一.在探詢中,當代戲劇發展的歷史呈現了清晰的脈絡和線條。
胡星亮教授秉承了南京大學在當代戲劇理論上堅持的一種獨立品格和人文立場,不僅具有一種用客觀的歷史視野看待問題的坦然,也在回顧歷史中做到了邏輯的清晰:戲劇魂魄之遮蔽和清晰的不斷演繹和交替,既看到了歷史,又用客觀的歷史觀出發對今天、未來的戲劇做了全方位的辨析。認為,目前戲劇形態呈現的三個形態雖然也貌似輝煌,實際上無法遮蔽其精神內涵枯竭的命運和桎梏,基本上切中了要害——主流戲劇(以楊利民的《地質師》等為代表)中現代現實主義的本質內涵和戲劇精神被忽略;實驗戲劇(以孟京輝的《思凡》、《我愛 XXX》、《戀愛的犀牛》,林兆華《哈姆雷特》等為代表),否定文學在戲劇中的重要地位,重表演而輕文本,戲劇敘事的表象化,有時則摻雜“新左派”的政治偏見,大多對傳統的解構尖銳犀利,自身的精神美學建構不足;商業戲劇(以《離婚了,就別來找我》等為代表)通過商業上的炒作包裝,逃避現實和排斥人文精神,意識形態掌控中的唯上,市場經濟沖擊下的唯利,令整個社會人心浮躁和精神萎縮,出現一度創作疲弱,二度創作紅火的畸變。包裝炒作的熱鬧與藝術品格的粗鄙,令現代化進程遭到嚴重扭曲。這里胡星亮教授對這種扭曲做了批評。在胡教授的觀念里,那些“忽略了人的價值、忽略了精神向度”的當代戲劇是十分有害的,它們流離于社會真實之外,還幻想對社會發言,它們擾亂真實的戲劇市場,拿假培育來混淆真市場……大致上講,胡星亮教授對于失魂的分析是真誠和精神可嘉的。在這些真誠的言辭里,一個堂吉訶德式的戲劇批評界教授形象已經栩栩如生,呈現出明確的批評立場。
然而,作為一個學子,我覺得事情并不能到此為止,而應該看到現象的復雜性,歸納在這樣邏輯線條背后出現的個性和特殊性。如:雖然“失魂”是當今話劇的主調,但是否存在例外,可能孕育出我們今后理想的形態的一種雛形,如《戀愛的犀牛》(既是商業化炒作,又有現代性),此其一;
事實上,主流、商業和實驗三者的彌合與疏離,界線的模糊和滲透是普遍現象,它們之間具有自我矯正、自我完善的功能。如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是90年代中國戲劇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征。1991年中宣部組織了 “五個一工程”獎,同一年,文化部設立了“文華獎”。這兩個獎項的實施,成為90年代國家組織精神產品生產的重要方式,造就了一大批被標簽為“優秀”的劇目,使主旋律戲劇崛起。這些劇目主要有《天邊有一簇圣火》、《虎踞鐘山》、《商鞅》、《生死場》等。這個龐大的群體里面,政府獎勵作為一種新型的戲劇投資方式為文藝團體和社會接受,至于政府倡導的戲劇到底有否觸動真正的戲劇消費,甚至有否破壞本來需要扶持的戲劇觀眾和消費群,這需要有數據才可以說明,但它們在事實上壓制了純商業戲劇的低俗泛濫,又不是一件壞事情。
所以,客觀的陳述應該是這個樣子的:當代的“戲劇失魂”既是一種客觀,又有可能是一種我們賴以審視的依據,所謂腐敗是鮮花的土壤,“黑夜給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樣的表述是否可以成立?樂觀主義是否可以在當代這樣一個戲劇疲弱的環境里成立,因為在樂觀主義者看來,所有弊端都可以轉化成一種優勢:在大家都喊失魂的時候,可能正是真正的靈魂可以大行其道、渾水摸魚的時機。這樣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大?需要我們學者和戲劇工作者的拭目以待。
或者,應該更加的模糊語言來概括更加科學——“非彼即此”的價值觀同樣值得審視,其抵達問題真實的可能性很可能被這種二元對立消解掉。
二.在探詢中,關于戲劇“招魂”期盼呼之欲出。
應該說,失魂是無奈的——招魂是必然的,著重點應該是重塑人的戲劇。這樣的論述至少是邏輯嚴密的。
招魂是人的價值的宏揚,失魂是人的價值的喪失,其間沒有妥協和中間地帶,在這兩個美學對立的概念中,價值一直是衡量我們戲劇的重要依據。我們失去的悲劇里既然蘊涵著曾經的確立和尋找,那么,現在去消滅“喪失”狀態的法寶就勢必是招魂無疑。這在字面上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我們應看到,人的價值要確立和宏揚,還必須看國民性,一個人的價值萎靡和委瑣的國度,是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戲劇的,這幾乎可以是定論。但是,一個人的價值被扭曲或者壓制的社會,不一定不會誕生優秀偉大的戲劇(如俄羅斯契訶夫時代的戲劇《海鷗》、《櫻桃園》),戲劇要招魂,首先要看清楚我們當下是精神萎靡還是活躍的自由精神被壓制的問題。
如果承認后一種情況,也就是承認中國當代藝術家思辯和藝術的能力,是歷史問題和美學問題,是一種需要時間空間來解決的問題。但是,一個反面例子是,那些移居海外的藝術家——當他們不再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否可以因為可以自由表達 “人”的問題而創造出一流的戲劇作品——事實上沒有——高行健寫《絕對信號》是在國內。這樣就似乎把問題復雜化了。
因此事實上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文革以后的精神反撥和思潮風涌導致了一個不平凡的時代。但是這個啟蒙和追求被看得那么崇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今的時代,翻天覆地的變化呈現出光怪陸離的外殼,我們對自身的認知也在不斷地更新——我們自身要探詢我們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人格需求:我們不可否認在在真正的需求背后隱藏了對虛偽的渴望,我們掩藏我們極端的欲望,掩藏我們的否定欲望和永遠的不滿足。
向日葵菌核病生物防治的初步研究…………………………………………………… 裴 丹,杭麗雪,于景苑,王曉潔,韓 冰(87)
這是一個精神極端的空虛的時代,又面臨體制和政治的干擾,許多方面的合力,讓我們失去了依靠和泊岸的錨……我們在精神上依然在大海上漂泊和流浪……從這個意義上講的招魂,既有對外界的苛求,又有自身的錘煉,兩者必須辨證統一考慮。
因此,戲劇招魂——任重而道遠。
戲劇,本質上是一種“場”,美國著名女哲學家蘇珊·朗格(符號論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情感與形式》中發現:“至于戲劇,它同樣創造了一種虛幻的經驗和歷史,因此戲劇實質上是一種詩的藝術。”戲劇的整體需要是我們對于詩歌的需求本質上是一樣的,在一個物質維度擴大而精神向度縮水的時代里,戲劇和詩歌面臨的困惑是類似的。我們需要維護戲劇作為一個藝術品類的尊嚴和價值,維護它的光輝,這就對藝術家和對體制提出了雙重的要求,也對能營造這個環境的外在世界提出了質疑和審視,“我們拯救自己的道具依然只能是自身”,因此考量它不應該是單一的。
附錄:
我對于一些相關問題的看法:
1.戲劇理論,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再到尼采……到馬丁·埃斯林的《荒誕派戲劇》,繼承、持續和超越、顛覆是兩根主線,在這個箱體之內,戲劇從一個墻面滲透到另一個面,而藝術家在里面摸索、掙扎的結果,很有可能把這個正方的箱體,弄成了一個類似不規則球形的物體(但它們是不規則的),于是,我們看到一個奇怪的沒有規律可循的形態——現代戲劇樣式很有可能是那樣的,在反叛中有回歸,在前瞻中有回顧……這符合人的定義和性質,人是求知和反思的結合體。
2.藝術家精神的墮落是分等級和呈現階梯狀分布的——如對戲劇本體“人”之理解和演繹——
有人從來不寫不關于真正的人的作品;
有人暫時不寫人本體的作品,而寫教條式的作品;
有人幾乎不寫人本體的作品,而寫有市場的作品;
有人從來不寫人本體的作品,而寫其他標準的作品,比如教育性的,他個人認為這種作品是對社會人類有利益的而更需要張揚;
有人知道寫出的東西是沒有觸及存在之本粉飾太平,甚至指鹿為馬,黑白顛倒,與“人本體”背離,但他還是樂此不疲,甘愿為利益集團服務并享受豐厚的物質回報……
其實,價值判斷時常左右藝術家的創作,一些被標簽為歌功頌德的類型或者為“五個一”創作的藝術家,在他們的人格坐標里面,未必不是從正義和對人的理解出發的,未必不在改造人類劣根性甚至丑陋國民性的光環之下尋求突破,只不過價值坐標高與事實判斷每個人偏向的程度不一樣。
3.分歧和誤讀于是接踵而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人的問題上的爭論本身是沒有定論的,于是價值混亂下我們如何獲得概念的明晰個戲劇理念的一些共鳴 (一致性幾乎是不可能的)是我們要注意的。如什么叫戲劇的本體?為什么戲劇的本體是人——難道不能是物質和空氣?(如荒誕派戲劇發展演繹的那樣,未來戲劇樣式可能壓根兒不一定需要有真人表演!)
4.多元既是一種我們要發揚的考慮問題的向度,又可能被地方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政治集團利用,成為腐敗的源泉。舉一個例子:你說地球是要節約的因為它只有一次消費,比如石油等等,我要提出多元的看法,地球是可以多次消費的,比如氧氣等等;
5.體制的干預是與接受體的思想狀態和精神向度有關的,一個具有超級彈性的民族,在這個晦澀里可以化疼痛為力量,而一個個性被抽離,人格貧弱到一定層次的民族,在這個晦澀下面,只有孤芳自賞和自我憐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