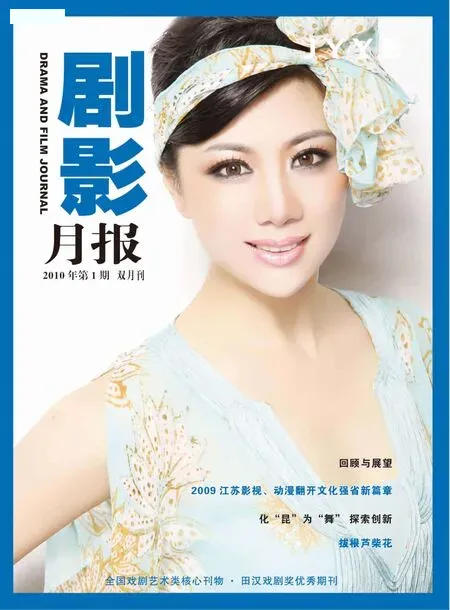談談淮劇的歷史淵源
■陳萬宏
說起淮劇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一部中國地方戲曲發(fā)展史的濃縮版,可它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淮劇,是由蘇北民歌、勞動號子、民間說唱及香火戲發(fā)展而來,可分為門嘆詞、香火戲、徽夾可、江淮戲、新淮戲、淮劇等發(fā)展階段。其中“徽夾可”階段即是淮劇發(fā)展史上,比較特有的歷史時期。
門嘆詞,即貧苦藝人為生活所迫,挨門逐戶地為乞討而演唱的一種說唱形式。以民歌小調演唱一些民間故事、歷史傳說等。
香火戲,即為敬神祭鬼、禱祀還愿的巫儺僮子在敬祭神鬼之余,為了娛悅民眾以獲更多的布施,而將巫書及宗教勸世文中的故事關目演唱出來的一種表演形式。
兩淮(淮陰、淮安)、鹽阜(鹽城、阜寧)地區(qū)自古巫風盛行,早在商周時期即有巫儺祭祀活動,而與古代儺舞一脈相傳的香火戲,直到現(xiàn)在的淮安金湖農(nóng)村中還有傳人。因為當年演唱香火戲的僮子,跳大神、演小戲、唱門嘆詞三樣都可以,所以民眾們又稱他們?yōu)槿勺樱伤麄冄莩龅南慊饝蛞簿退追Q為“三可戲”。
另還有一種說法是,香火戲主要流傳于古淮河的上河、里河、下河“三河”區(qū)域,所以被戲稱為“三河戲”;而當寫下來看時,“三”字和三點水偏旁往往被連在一起了,所以,“三河戲”又被稱為“三可戲”。
兩淮地區(qū)也有直接稱“唱淮調”的。
徽夾可,是淮劇發(fā)展史上所特有的階段,那它是怎樣形成的呢?明清時期,兩淮地區(qū)得河道、漕運、鹽運、榷關,以及府衙所在地等之大利,經(jīng)濟昌盛帶來了戲曲的繁榮。當時的清江浦(現(xiàn)淮安市區(qū)的運河兩岸“夾岸二十里”、“人口五十萬”),成為全國的治理河道的總指揮中心,全國漕運、鹽運的樞紐中心,全國造船、修船最為集中的地區(qū),與揚州、蘇州、杭州一起并稱為運河上的“四大都市”。在淮地發(fā)財?shù)幕丈虃儯约叭珖鞯貐R集到這里的大商巨賈們,引得諸多唱戲的徽班涌來。徽班與其他劇種在這里交流、競爭、繁榮的同時,對兩淮以及鹽阜地區(qū)的地方戲曲發(fā)展起到了催化和哺育的作用。
特別是到了清咸豐五年 (1855年),黃河又改道北移后,加之海運開通,致使兩淮的城市經(jīng)濟走向衰落,大批的徽劇藝人不得不流落到農(nóng)村。為求生計,徽劇藝人們常主動地聯(lián)絡“三可戲”藝人相互搭臺演出,有的還聯(lián)姻生子、結拜授徒,因此就帶動了還在戲曲初級階段徘徊的“三可戲”,幸運地進入了“徽夾可”的發(fā)展時期。由于得以向徽劇學習,大大地豐富了淮劇的演出劇目,角色行當也漸發(fā)展齊全,淮劇也就比臨近地區(qū)的其他地方劇種提早走向了成熟。最主要表現(xiàn)在劇目、基功和行當?shù)确矫妗?/p>
江淮戲,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因淮河、洪澤湖洪水泛濫,上、下河地區(qū)的藝人們隨著難民流落江南,直到上海等地去謀生。他們的演出被江南人稱為江北戲、江淮戲。
鹽阜地區(qū)的韓太和、時炳南、武旭東、何孔標、倪福康等,以及兩淮地區(qū)的楊子良、沈月紅、大友子(徐明芳)、沈玉波、石景琪等先后到達了上海,對江淮戲立足上海和江南,都做出過重要貢獻。
據(jù)《淮劇志》載:曹月紅約于1920年到上海,和時炳南、顧漢章、陸三龍等同臺演出。因他的唱腔清亮甜脆,被觀眾贊譽為“繃脆透的淮餅子”,他獨具一格的西口[淮調]在同行中頗有影響。孫玉波1921年到上海,他演唱的[淮調]清脆爽朗、吐字清楚,被稱為地道的“淮繃子”,業(yè)界曰:“由此,‘淮繃子’引進至上海。”
再后來,蘇北到上海謀生者越來越多,江淮戲也越來越紅火,因而吸引了原唱京劇的藝人也加入到江淮戲中來,這樣就又有了和京劇同臺演出的“皮夾可”時期,致使淮劇又有了新的發(fā)展。突出表現(xiàn)在,由小時唱過香火戲,后學京劇、徽劇,又改唱江淮戲的阜寧人謝長鈺,于1927年在蘇州創(chuàng)唱了一字多腔、演唱細膩的[拉調];由淮安籍的、靠自學過京、昆、徽、梆的筱文艷,于1939年創(chuàng)唱了更加調式自由、唱詞句式自由,更能讓豐富情感得以充分表現(xiàn)的[自由調]。
而在南方演出的藝人們再回到家鄉(xiāng)演出,又帶動了兩淮及鹽阜地區(qū)的唱戲水平的提高。
在兩淮地區(qū)的民間,以吳應成、劉玉琴、周茂貴等人的家班最具影響力。
吳應成,自幼愛好三可戲,愛唱民歌小調,年輕時因誤抓而被捕入獄。在獄中,他自編悲板[淮調]非常動情地演唱自己不幸的遭遇,博得了獄官同情而獲提前釋放。出獄后,他便情有獨鐘地以獄中自創(chuàng)的[淮調]與人合演小場戲,這樣一來,他的[淮調]與傳奇很快在兩淮地區(qū)流傳開來,向他學唱[淮調]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在兩淮有[淮調]鼻祖之稱。約于1915年自組“吳家班”,其長子吳守琴、次子吳守進后來都成為淮劇著名的藝人。
劉玉琴,自幼隨繼父學戲,擅唱[老淮調]、[淮繃子]。1933年組班。日本鬼子侵占江淮期間,劉玉琴以鍋灰抹臉,任刑加身,拒不為日本侵略者演唱。她是名副其實的淮劇宗師,眾多淮劇名角都是她的門生。(新中國建立后還受上海淮劇團特聘教授淮調)
周茂貴,自幼隨父學藝,他的[老淮調]又有自己的特色,被觀眾和同行們譽為西路淮劇的一絕。
據(jù)《淮劇志》記述:東路的香火戲原本沒有[淮調]。是于1930年,下河的楊金花父女倆先后到上河地區(qū)來演出,為打開局面而學唱西路[淮調]。后在保持高亢激越格調的基礎上,又融進了[下河調]的柔和抒情韻味,從而形成了東路的“軟淮崩子”。
為什么我把“江淮戲”繼“徽夾可”之后提出來作為淮劇的一大發(fā)展階段呢?這是因為在這一時期,淮劇又有了較大發(fā)展的主要地點,是把它稱之為“江淮戲”的江南。是由于受到江南文化,特別是大上海文化氛圍的影響,其中包括受到京劇的影響等,淮劇才又有了較大的提高和發(fā)展,最主要表現(xiàn)在唱腔和劇種音樂等方面。而此時的京劇在這一時期對諸多地方戲曲都有較大影響,所以,將“皮夾可”歸入“江淮戲”時期來表述。
到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三可戲在蘇北革命根據(jù)地,發(fā)揮著宣傳教育、團結民眾、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重要作用,被稱為淮戲、新淮戲。
1942年1月,淮安的新安旅行團由桂林回到了蘇北,開始組織和指導文藝宣傳活動,并由凡一、方徨、常虹、雪飛四人,專門組成了淮戲研究小組。
淮戲緊密配合時代發(fā)展編演了大量的現(xiàn)代戲,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最大特點,并在后來直至現(xiàn)在,形成了淮劇新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新中國建立后的1950年,從上海“麟童劇團”的戲單上,開始有了“淮劇”稱謂,淮劇的發(fā)展從此走上嶄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