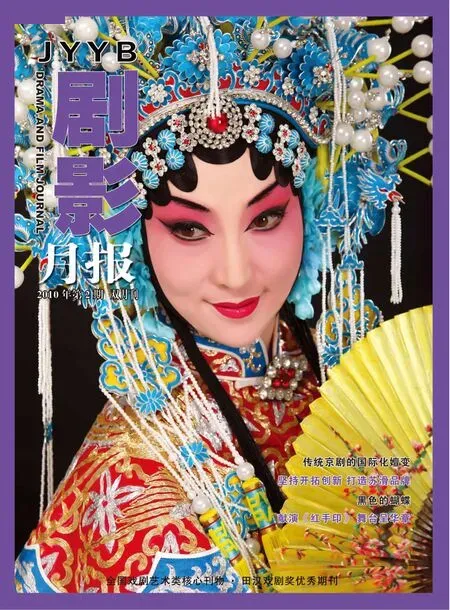柳琴戲的吐字
■胡玉俠
從藝三十年,自踏入訓練班學習第一段柳琴戲唱腔時,老師就告誡我們:“唱戲一定要做到吐字清晰。吐字不清,如鈍刀殺人。”兒時年幼,不懂其深刻含義,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藝術的逐漸成熟,才慢慢地心有所悟。
對于一名戲曲演員來說,戲曲的四功五法要精通熟練,所謂四功,即:唱、念、做、打,五法為:手、眼、身、法、步。我們地方戲尤其對唱的要求極高,要求演員要做到字正腔圓。唱戲首先要做到字正,只有把字唱正了,觀眾才能聽清楚你唱的是什么,才能靜下心跟隨你進入下面的劇情,只有把字音念準了,才有利于行腔的圓潤,正可謂“字正腔圓”。我們戲曲演員對唱腔的處理,必須逐字逐句的揣摩。先要弄清詞語的含義,再加以戲曲藝術的修飾,而后再展現在舞臺上。我們的先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總結出關于吐字的“五音”和“收聲”的規律,按五音的規則找準字的發聲位置,使其咬字和吐字的真確完美,如果我們在唱腔中咬字不正,則唱出的字義不明,讓觀眾聽來不知其所云,就如鈍刀殺人。由此可見,我們戲曲演員的咬字和吐字何其重要。我們柳琴戲是以演唱為主的地方劇種,咬字和吐字在演唱中極為重要,他的演唱技法立足于蘇北的民間音樂基礎之上,突出他的小調風格和“拉魂”特性,通過詞與曲的完美結合,讓人們聽后如癡如醉、欲罷不能。
清代戲曲理論家王季烈在他所著的《螾廬曲談》中寫到:“故人云:‘取來歌唱里,勝向笛中吹’,謂其能分析字面也。然使唱曲而不讀其正字,審正其音,則咿啞嗚囈,有音無字,聽著不知其所唱何字,靈妙之人口,等于無知之樂器,曷足貴歟!”另一位戲曲理論家徐達春也曾直接指出,那種不能表達人物思想情感,只能“尋腔依調”唱法,談不上是藝術,“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了,由此可見,歷代的戲曲表演藝術家們無不致力于講究歌唱吐字的真與美。所以,無論我們的唱腔和念白,都要力求把字咬準吐清,切忌尖團字不分、含糊其辭、囫圇吞棗。
要想分清尖團字,我們必須掌握好漢語拼音,學好了漢語拼音,才有助于我們演唱時吐字技巧的提高。我們把平時說話的發音方法加上藝術的夸張,使其加強和美化,這就如同我們在舞臺上所運用的程式動作一樣,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們在每一句唱腔中的吐字,不能單靠嘴皮子的力量,而是要使用丹田氣,使其更加充實飽滿、圓潤甜美。我們所說的咬字是經過唇、齒、牙、舌、喉等器官將字咬成不同的姿態。咬字要正,咬字不正就變成了另外一個字了。吐字是將唇、齒、牙、舌、喉咬成的字,正確清晰地吐出來,開、齊、攝、合是吐字的方法,是指字在口中的部位和字的著力點。在唱腔的運用中“四呼”、“五音”要清爽,整個口腔的動作不宜太大,力求聲音的圓潤和統一,在處理每個字的字頭、字腹、字尾時要準確得當,不能含含糊糊,于此同時還要注意字的生動和連接,將每個字咬得準、吐得清、收得凈、唱得美。只有做到了吐字清晰,行腔圓潤,才能使觀眾緊緊地跟隨著你,走進舞臺形象的內心世界,才能達到:你喜他樂、你悲他泣、你瘋他狂的境界。
由于柳琴戲的曲調大都來源于蘇北民間小調,所以唱腔中還保留一些虛字,它是用來襯托一些花腔用的,例如:哪哈呀哈、嗯啊哎嗨呦、我嘚嗯哎呦、嗯啊咿呀等結構的語氣助詞,這些我們統稱“輕聲”詞,他在唱腔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地方色彩的完美體現,演唱時,我們不能淡然處之不屑一顧,我們更不能一味的去追求多么圓潤,多么字正腔圓,一味的去夸大,而要唱得輕巧自如,反之,我們就不是畫龍點睛而是畫蛇添足了。
以上是本人對咬字和吐字的理解,如有不妥,還請專家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