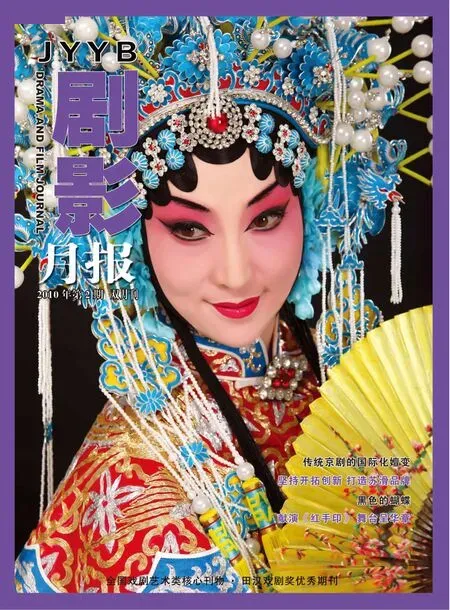我演《白兔記·出獵》中的咬臍郎
■王如丹
我演《白兔記·出獵》中的咬臍郎
■王如丹
2001年冬,江蘇省蘇州昆劇院傳統版本《白兔記》在臺灣新舞臺開演,我有幸擔任咬臍郎一角,和梅花獎得主王芳(飾李三娘)同臺聯袂獻演。此番臺灣演出的版本是明傳奇疊頭選折版本,為《養子,上路,送子,出獵,回獵》,整場演出由于古樸、原真,得到了崇尚傳統的臺灣觀眾熱烈好評。《白兔記》元無名氏作,南曲戲文,共三十三出,至明改編成傳奇演出本三十二出。元南戲有四大傳奇,列有《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劉智遠白兔記》描寫劉智遠,李三娘二人,自結合又分離,最后重圓的故事。其中《出獵》一出,則描寫劉智遠被逼投軍后,李三娘受哥嫂折磨,一日在磨房產下一子,用牙齒咬斷臍帶,取名咬臍郎。李三娘為避哥嫂害兒,托竇公送至劉智遠處,撫養長大。一日,咬臍郎帶著軍士出外打獵,為追趕一只中箭的白兔,來到沙陀村外,在井邊偶遇挑水的李三娘,經過詢問方知就是生母.回家后和劉智遠說知,接李三娘回家團圓。
咬臍郎昆曲中用作旦行當扮演(又稱娃娃生),昆曲中的少年兒童角色年少氣盛,伶俐可愛,但又要童聲細氣,所以往往由女角來扮演。因此產生作旦這一行當,因女角個子小,嗓音細而嫩,頗有童聲氣息,適合扮演這一類角色,如《寄子》中的伍子也是作旦扮演的,伍子這一人物也是我擅演的角色。
當咬臍郎在王旺和眾軍士簇擁下,持馬鞭上場九龍口亮相.隨著同念“穿地錦襠”作一大段騎馬馳騁的舞蹈動作,至見到井旁有一婦人,勒馬,下馬,叫王旺去問婦人是否看到白兔,直至婦人回答:有兔必有箭,有箭方有兔時,咬臍郎聽了不免詫異,隨后叫婦人過來問話。咬臍郎在旁邊石塊上坐下,戲進入了高潮,我在前面舞蹈動作時和后面這段問話的戲中盡量以裝出雖然年齡小,但像懂事的大人一樣的情感和形體動作來體現。
當李三娘唱到,所生之子名喚咬臍郎時,四軍士一聲吆喝,咬臍郎既驚詫又緊張,畢竟還是小孩子,得知婦人所說的劉智遠和咬臍郎完全同自己和父親名字一樣,不驚詫才怪呢。故我既用套翎子,大轉身的形體動作,配上一聲驚叫來表現咬臍郎的驚詫,但同時也忙喝住眾軍士的吆喝免得驚嚇苦命婦人的聲聲念白:不可生事,不可生事,來表現咬臍郎的善良和懂事,隨后送走了婦人,咬臍郎帶著疑問的心情,和出發前興致勃勃的打獵玩耍心情完全不一樣的情緒上馬回府。最后回府詢問父親劉智遠,促成父母相會,全家團聚。實際上《白兔記》全劇中從劉李被分離到團圓,起到關鍵相連作用的是咬臍郎和一只白兔。沒有咬臍郎打獵追趕白兔,也就不會碰到李三娘,也不會有后面的劇情發展.咬臍郎是起到了主線作用的。
我在多年飾演咬臍郎一角中深深體會到,作旦這一行當,包括演咬臍郎和伍子這一類角色,一定要有較為扎實的基本功,并要有一付好嗓子。舞臺上出現的男小孩表演中不能有太多的脂粉氣,既要演出男小孩的天真活潑,可愛伶俐,又要體現出年少懂事,知書達理的氣質,特別是像咬臍郎、伍子的這一類人物。但咬臍郎在騎馬打獵中又不能過多的堆積身段,而是應該根據人物,特定情景需要,合情合理地運用程式表演手段;同時對于已近不惑之年的女演員來講,更應該注意在形象塑造上更接近人物,更好地掌握情、理和唱、念、做、舞的結合,塑造出可信的舞臺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