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脈動的近距離解讀
○侯文宜 范秀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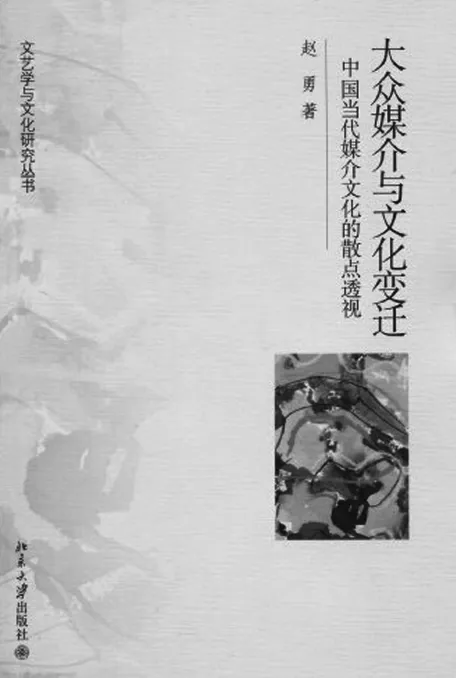
《大眾媒介與文化變遷——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的散點透視》,趙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43﹒00元
早在20世紀60年代,被譽為信息社會、電子時代“先知”的馬歇爾·麥克盧漢就曾預言:“‘媒介即是訊息’,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P34)20世紀以來,大眾媒介的迅速崛起正日益證實著這個理論,特別是電子媒介的出現,不僅改變了文化傳播的方式,改變了文化自身的形態,甚至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方式。媒介文化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化,它重新構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并潛移默化地轉換著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觀。
20世紀90年代之后,媒介文化研究逐漸成為顯學。當代文化不只是以大眾傳媒為傳播介質,許多文化形式更是大眾媒介所制造和特有的,基于大眾媒介所產生的各種文化現象紛繁錯雜,因而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媒介文化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話題。但令人遺憾的是,當前的媒介文化研究主要是對西方社會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的橫向移植,而缺乏對中國當下文化現實問題足夠而有效地關注,現實感、本土意識顯然不夠。趙勇先生《大眾媒介與文化變遷——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的散點透視》一書的出版宛若一縷透光,用智慧的語言和通徹的思想觀照當下本土經驗世界中發生的種種文化景觀,將學理和現象熔于一爐,直指當代文化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及本質所在,一定意義上填補了這一空白。
該著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文化史的研究角度。作者采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在解讀當代文化現象時,“把媒介文化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以大眾媒介為切入點,縱觀當代中國近三十年內隨著大眾媒介本身的發展變化所產生的文化演變,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媒介文化現象——電子書寫、博客寫作、文學閱讀、書信短信、紅色經典、百家講壇等熱點問題,經過層層分析和深入解讀,揭示出一條清晰的文化轉型的脈絡:大眾媒介影響下當代文化變遷的兩個基本維度——“從審美文化到消費文化、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全書邏輯嚴密、似斷實連,趙勇先生用他獨特的自我表征方式,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清晰明了的當代媒介文化圖景。
《大眾媒介與文化變遷——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的散點透視》一書共五個章節,通讀之可見出該著另一特點,即個性化的思維構架與獨到的考證、辨識、洞見。第一章重在辨析大眾媒介和媒介文化的涵義。作者由流行的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的解釋切入話題,但是從現實的角度看,西方正進入成熟的消費社會,中國則正經歷由傳統的生產性社會向富裕的消費性社會的轉向,因此正在轉型中的中國消費文化不同于凱爾納的界說而有其獨特的微妙處、復雜性和多樣性,趙勇敏銳地指出:“凱爾納的界定畢竟是立足于西方社會現實、理論視角等方面形成的一種的判斷,其中的一些說法并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作者對媒介文化做了更為精準的定位,認為媒介文化是“大眾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之后所出現的文化形式”,同時是“一種全面抹平的”、“雜交的”、“不斷生成的”文化。而在大眾媒介的引領下,本來應該作為精神文化守護者的知識分子,也在大眾媒介的迅速崛起中轉換角色,變成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媒介的介入重新塑造和形成了知識分子在媒介時代新的價值定位——“知道分子”,文化成為了一種商品待價而沽,審美意識形態日漸讓位于消費意識形態。之后的章節中,作者針對媒介時代出現的熱點問題一一展開討論,例如第二章對傳統寫讀模式與數碼時代寫讀模式的美學比較,第三章對“第五媒介”手機出現后所帶來的現代性體驗之利弊分析,最后的兩章則以意識形態批判的方法對當前“紅色經典”遭遇改編惡搞的文化現象和“百家講壇”的新式文化生產模式進行了犀利的解讀和批判。在面對種種具體的文化現象剖析時,作者不回避,不粉飾,不僅闡述出當今文化變遷的真實格局,而且深刻揭示了大眾媒介在當代文化變遷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具有怎樣的作用,以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符號經濟及現代傳媒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大眾消費文化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已愈來愈突出。然而,如何看待之卻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是,不管褒者貶者,都不能不處于大眾文化的環繞之中和影響之下,整個社會正在發生重大的文化變遷。那么,究竟如何客觀、準確地判斷其性質、是非、價值,又如何給予正確引導使其健康發展,就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在目前國內媒介文化研究尚不充分,特別是對當代文化變遷缺乏科學解釋的情況下,該著從學科理論的高度,透徹分析了沉淀于一般媒體信息表層之下的文化內涵、歷史邏輯、是非價值,無疑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啟發。尤其可貴的是,趙勇并不盲從于流行的媒介文化理論,深厚的學術涵養使他在借鑒比照中辨析著中國當代消費文化的形態特征并發出自己獨有的見解,加之文體風格上學術性與平易性的融合,從而深入淺出地展示出在媒介的參與下我們的文化正處于一個怎樣的狀態之中。該著的成功之處正在于其獨立的學術精神,結合具體現象的求實精神,對媒介文化的正負意義所作的批判性的、正確的估價,為我們理解當代紛繁錯雜的媒介文化及其影響提供了深刻獨到的視角與觀點。
當然,媒介文化作為新興的文化形態,對其批判既要著眼于它運行的顯在層面,又要洞察所存在的現實價值和意義,這種新興的文化形態既然生逢其時,也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媒介的迅猛崛起填平了地域文化之間的鴻溝,模糊了生活和藝術的邊界,也使得公共話語與私人話語的界限逐漸消失,但不可否認,這種“全面抹平”的媒介文化也豐富了民眾的精神生活,開辟了文化普及的新路徑,且帶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對于形成市民社會的公共空間和培養民眾的現代人格、現代觀念、現代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作者也不可能預知生生之易的文化在未來的發展空間中會有怎樣的變化,所以種種判斷和論證無疑又都帶有了階段性的特征,有待未來的檢驗。但令人觸動的是,趙勇在文中時時憂心于審美文化的黯然退場,提醒著我們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