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儀控技術應用中的基本問題
王遠隆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核反應堆系統設計技術重點實驗室,四川 成都610041)
隨著國家核電事業進入大發展時期,核電技術國產化也成為熱點話題。如何將引進的國外核電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礎上創新出自主化的新一代核電技術,也自然成為需要實時考慮的問題。
本文以核電儀控技術應用為例對實際工作中可能影響國產化的問題作一個概述性的討論。
1 核電儀控技術應用中的基本問題
1.1 理論基礎問題
(1)核反應堆模型剛性問題[1-2]
核反應堆(裂變堆)的物理模型是反應堆動力學系統的主要研究對象,數學表達復雜。當利用計算機進行數值仿真計算時,會發現對該物理模型作數學處理有很大難度。故有提法稱此現象為剛性(Stiffness)問題,或者直接稱反應堆數學模型為病態方程。圍繞這個剛性問題,有不少研究文章出現。
所謂剛性問題,實際上就是反應堆數學模型中的物理參數組合匹配問題。

式(1)代表反應堆物理模型經過一系列簡化處理后得到的點堆模型的指數函數數學表達式。當反應性擾動量為δk=0.023時,計算得到上式中的特征參數值(w0,w1,w2,w3,w4,w5,w6)分別依次為150.1399,-3.0612,-1.1931,-0.3460,-0.1176,-0.0323,-0.0125。這里看到,w0與w1~w6之間量值差異很大。
計算數學理論教科書認為,物理特征參數值彼此間的比大于10倍就算是數學上的剛性問題。在計算機做數值計算時,剛性問題反映出的結果是,由于參數過大與過小造成計算誤差積累最終導致計算失真。
但只要從尊重歷史的角度考察一下,就會知道這僅僅是由于當初計算機科學技術處于發展早期階段的暫時性誤解。所以,把它轉而作為數學和物理概念自然就不應該了。現在像RELAP5這樣的大型程序都可以微型計算機化,再提剛性問題顯然與技術發展事實不符。計算數學中“兩個特征參數比值大于10倍就是剛性問題”的結論也需要修正。
(2)模型處理本身的虛假問題[3]
反應堆物理模型是通過時間、空間分離才轉化為點堆模型的。故該模型僅在反應性變化不至引起堆內嚴重空間效應時才適用。如果再在點堆模型基礎上引入數學近似條件而不認真考慮物理上的合理性,則極可能導致簡化模型失真而引發工程設計中的失誤。
檢驗模型處理是否合理的辦法很簡單,用公認的模型做個仿真計算比較即可。
(3)虛假水位問題[4]
核電站常用的U形管蒸汽發生器水位測量與控制技術中常有虛假水位一說。
蒸汽發生器的虛假水位原理性的提法是:蒸汽流量變化造成蒸汽發生器內水裝量持續性處于兩相流狀態,從而引發汽水界面處汽泡持續性的漲縮變化,導致水位測量儀表測得的水位持續變化。這種因汽泡漲縮造成的水位變化習慣稱為虛假水位。
圖1、圖2是計算機仿真得到的虛假水位曲線。

圖1 蒸汽流量階躍下降10%額定值水位變化Fig.1 Level change when10% step-down of steam flow

圖2 蒸汽流量階躍上升10%額定值水位變化Fig.2 Level change when10% step-up of steam flow
事實上,所謂的虛假水位是真實的物理現象。這是蒸汽發生器內典型的兩相流特性。圖1所示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蒸汽發生器因水位持續上漲灌滿其蒸汽空間而喪失自己的產汽能力。圖2所示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蒸汽發生器因水位持續下降而被“燒干”。控制技術稱這樣的對象為自身不穩定對象或自身不平衡對象。
如果因為人的主觀認識能力所限就認定實際的物理現象是虛假的,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做一些先進控制技術研究試圖調節這種虛假水位,那必定是徒勞的。道理很簡單,研究是建立在主觀虛假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可能有真實結果。
就核電站而言,它本身與常規火電廠的鍋爐汽包在原理上有類似的地方。但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這就是常規火電廠沒有核電站反應堆那樣的自穩、自調特性。如果把蒸汽發生器及二回路連同核反應堆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這種自穩、自調特性就能有效幫助修正蒸汽發生器的非自穩缺陷。
(4)反應堆自穩、自調特性問題[5-7]
反應堆的自穩定性和自調節性(簡稱自穩、自調特性)是保障反應堆安全的重要基礎之一。但這種自穩、自調特性常常被與反應堆的固有安全性混淆在一起,甚至認為反應堆的自穩定性就是反應堆的固有安全性。
固有安全性是反應堆的特殊要求。這是由核裂變反應特殊的放射性問題引發的。固有安全性需要滿足三層防護原則和五級屏蔽原則。而反應堆的自穩、自調特性僅僅是反應堆自身的一種穩定調節機制(控制機制)。這種機制僅能在外部發生小的干擾時把反應堆自己調整回到原初狀態(反應性變化時)或到達新的穩定狀態(負荷要求變化時)。
從控制的角度看,這種自穩、自調能力在理論上可以應對很大的干擾。但實際工藝系統所用材料對熱應力有各自的適應范圍,控制自然就會受到相應的限制。
有一點要特別強調,控制機制不論是自身具有還是外部另設置一個控制系統,其功能實現都是建立在所有工藝系統的完好性和早先物理、熱工設計的準確性基礎上的。一旦這種條件失去,則控制機制就難于發揮作用了。比如失水事故發生,設計上就規定保護系統先于控制系統作用引發停堆;保護停堆是強制性的,也沒有考慮自穩、自調問題。當然,這樣是否合理可以研究。
1.2 技術應用問題
(1)核反應堆模型空間效應問題[7-8]
這個問題突出表現在反應性儀這種核技術應用儀表中。
核反應堆的反應性不可直接測量。反應性儀是利用可直接測量的反應堆功率(核功率)通過點堆數學模型推導出的倒時公式間接計算出反應性。其應用多在反應堆物理啟動期間。
反應性儀研究報告說使用的是“消除了空間效應的點堆模型推導出的倒時公式”。這種提法明顯不合適。正如前面分析堆模型時指出的那樣,反應堆點堆模型并沒有消除空間效應,僅僅是在有限制的物理合理性范圍內將時間、空間分離得到的結果。所以,由點堆模型推出的倒時公式也絕不可能消除空間效應,其使用也一樣要受到限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反應堆啟動期間,由于功率很小,核測量誤差很大,依據所測核功率來計算得到的反應性量值其可信程度會受這種誤差影響。
(2)反應堆保護系統問題[10]
反應堆保護系統是一種特殊的控制系統,屬于核安全三層防護的第二層。它的保護功能是依據核安全分析所給出的安全極限值設置的。核電站一旦出現這類極限值,保護系統就要強制觸發事故性停堆保護動作。這種動作時間上要求要快,則必然會導致反應堆熱工系統物理狀態急劇變化接近背離物理上的能量不能突跳原則。這顯然是以犧牲設備壽命為代價的,如同醫學中的放療結果。有必要對這樣的保護機制重新評價。
常規核反應堆控制系統是不可能出現能量突跳的。一旦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則必然是控制系統功能設計或控制系統方案設計有問題。圖3是典型能量突跳的兩個例子。圖4為能量平滑過渡的實例。
(3)數字化技術應用問題
我國核電數字化技術發展和應用遠不如常規電廠和其他領域,且還是在其他領域發展到成熟階段,并且到國外已經在核領域使用時才開始考慮使用。這背后的原因當然是常說的安全性問題所致。
其實,反應堆的安全性與技術的先進性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主觀上先入為主說先進的技術不成熟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試想,國外第一個使用數字化技術的反應堆系統其依據又是什么呢?效率與效益是直接刺激先進技術使用的重要動因。當初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商用核電站的業主事實上也是在冒風險的。由此所能考慮到的就是對風險的掌控能力問題。敢于搶先一步,會贏得相當大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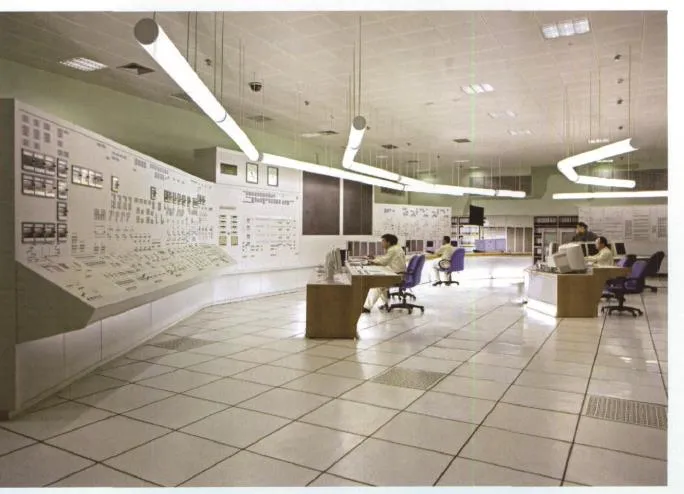

圖3 能量突跳問題Fig.3 Energy jump

圖4 能量不能突跳實例[11]Fig.4 Example of energy can not jump
(4)數字化技術中的并行性問題[9]
并行性是指為完成同一功能或任務的多個動作同時進行。它是模擬儀表的系統屬性。并行性的好處之一就是時間利用最大效率化。盡管從信號流動角度看似乎在元、器件一級有先后之分,但整個系統從一啟動開始各類元、器件之間在時間上就是完全并行的。
數字化儀控系統作為儀表系統也自然具有這種基于元、器件一級的并行性特征,而不能認為是數字化技術給系統帶來的好處或者說是數字化技術的特點。
數字化技術是以微型計算機和微處理器的使用為特征的。當前的計算機仍然遵循著美國科學家馮·諾依曼所確定的計算型機器的系統架構原理。這種機器的指令流是按照二進制串行結構設計的(字位一級是并行的)。這就好像人說話要一句一句依先后進行,計算機釋讀自己的語言仍然是要有先后順序的。可見,把并行性作為數字化技術的特點是有違科學原理和歷史事實的。
(5)數字化技術自身安全性問題[12-17]
數字化儀控系統自身的安全性是其功能能否順利實現的關鍵。在目前以引進為主及國內市場多為國外品牌的背景下,如何鑒別國外產品的安全性是檢驗自身消化吸收能力的重要尺度。
在標準方面,目前基本是對等翻譯調整國際標準為國內標準。標準是技術先進性和技術可達性的產物。國內目前是以引進或國內組裝作為應用支撐點。產品安全性檢驗標準帶有很強的依賴性。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通過消化吸收能建立自己的標準體系。
(6)引進與國產化問題
從當前的技術現狀看,儀控系統的引進是避免不了的。
技術引進實際是對引進方鑒別能力、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的綜合檢驗。特別是軟件程序,僅僅靠所謂標準題庫檢查仍然會有漏洞存在的可能。而標準題庫本身的檢驗又靠什么?顯然人的判別能力是重要前提。
引進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最好的技術買不來”。有種說法叫“不求最好,爭取能用”。而這恰恰會成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根源之一。引進、消化、吸收是目前的現狀。
數字化儀控系統的基礎是以計算機為特征的微電子技術和軟件技術。在這兩方面沒有大的突破之前,國產化多半是要靠在購買硬件和軟件前提下進行的,主要著眼點應是在系統集成上爭取突破。比如核電站所要用的DCS系統(數字化控制系統或分布式控制系統)。
(7)新的控制技術可實現性問題[18-19]
新的控制技術是否能應用到核反應堆控制中,主要取決于技術可實現性。
先進的原理性理論如模糊數學、神經網絡、遺傳算法等引入后,極大地推動了控制理論和技術應用的發展。但作為控制對象的核反應堆,由于其安全性所帶來的保守性導致其對新理論、新技術的使用持更為謹慎的態度。面對這種特殊性,新的反應堆控制技術可以先行在理論研究有充分依據的基礎上,再進行控制器的研究試制,借此為工程應用做好技術儲備。
2 技術問題反思
上述各類技術問題實際上反映出在核電領域中儀控系統應用方面基礎性研究工作的滯后。
從工程技術的角度看,問題源于重在實用、利用。技術是圍繞著這“兩用”的工具,結果造成長期缺乏對技術應用層面上的基礎性部分的關注,使得在面對換代更新上臺階時顯得步履維艱,力不從心。
基礎性研究是既費時又費力的。特別是關鍵性的基礎研發,只有長期堅持才有可能突破而形成規模化的帶動作用。當然,涉足多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則更是需要整個團隊足夠的耐心和真誠的合作。
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加強基礎研究才能支撐應用技術的持續開發,國產化也才會有可靠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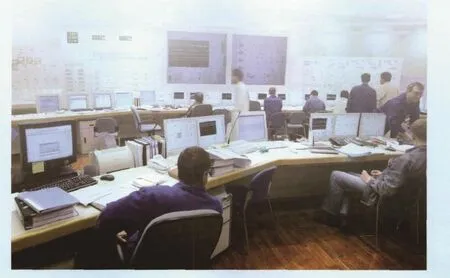
[1]王遠隆. 核反應堆動力學模型“剛性”提法否定. 北京:中國核學會核能動力分會學術會議論文集[C],2009,11.
[2]王遠隆. 核反應堆動力學模型“剛性”提法質疑. 合肥:第十二屆反應堆數值計算與中子輸運學術會議論文集[C],2008,4.
[3]王遠隆. 核反應堆動力學模型簡化問題. 昆明:中國核學會核能動力分會學術會議論文集[C],2007,4 .
[4]王遠隆. 蒸汽發生器水位控制問題. 武漢:中國核學會學術會議論文集[C],2007,10.
[5] [USA]Westing House. AP1000 Safety Analysis Report. April21,2003.
[6] [德]Wolfgang Rysy,等. 張祿慶,連培生,朱文煜,等譯. 核電廠[M].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5.
[7] [美]S.Glasstone & A.Sesonske. 呂應中,許漢銘,施建忠,譯. 核反應堆工程[M].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6.
[8] [美]Karl O. Ott,Robert J. Neuhold. 鄭福裕,侯鳳旺,譯. 核反應堆動力學導論[M].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2.
[9]王遠隆. 核電站數字化儀控系統結構分析. 四川:四川動力工程學會核動力專委會學術會議大會報告[D],2010,04.
[10]王遠隆. 核反應堆控制系統安全性保障措施. 上海:第十一屆工業儀表與自動化學術會議論文集[C],2010,6.
[11]阮良成,俞忠德,陳忠武,等. 秦山二期核電廠2號機組汽輪機誤快速降負荷瞬態分析[J]. 核動力工程,2007,28 (2):82-85.
[12]IEC. IEC61508-1-7.
[13]Jay Abshier. Ten steps to secure control system.PutmanMedia,2008.
[14]Jeffrey R.Harrow. Living control systems.PutmanMedia,2008.
[15]Bela Liptak. How to improve Nuclear Power Plant Security. PutmanMedia,2008.
[16]彭瑜. 工業控制軟件功能安全的實現方法和驗證. 上海:第十一屆工業儀表與自動化學術會議主題報告匯編[C],2010,6.
[17]傅家祥. 智能電網時代繼電保護技術發展趨勢[J]. 機械與電子.,2010,7 (1):1-4.
[18]王遠隆. 核反應堆模糊控制[J]. 四川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45(Suppl.2):1-4.
[19]王遠隆. BP神經網絡控制應用的基本問題[J]. 機械與電子.2010,7 (1):119-124.
[20] [英] Robin. Kerrod(主編). The Young Oxford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M]北京:外語研究與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