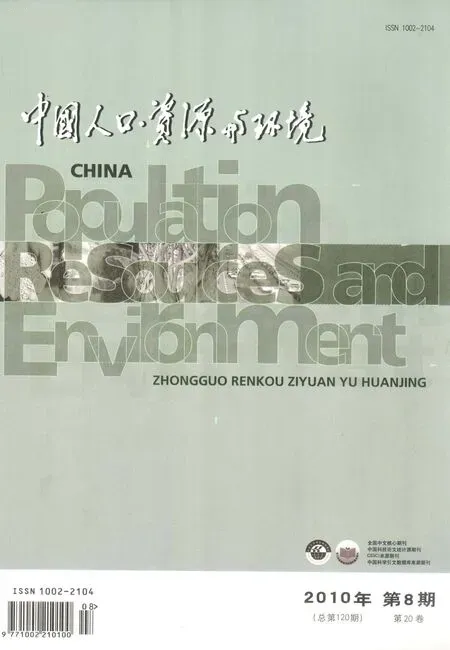資本投入、耕地保護、技術進步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程名望 阮青松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200092)
資本投入、耕地保護、技術進步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程名望 阮青松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200092)
工業化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騰飛的重要性,已經被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走過的道路所證實。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世界各國都曾經或必將面對的重要課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既是我國實現持續經濟增長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也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本文的動態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國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較多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和較少的土地資源稟賦是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始動力和內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使得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下降,農地荒蕪現象嚴重,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農業資本投入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影響顯著,增加農業資本投入,既能促進農業的發展,又能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技術進步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兩個效應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農業技術進步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影響并不顯著。本文的研究結論所蘊含的啟示是,中國在選擇經濟發展路徑時,應該考慮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特別是要充分利用本國富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
動態均衡;資本投入;耕地保護;技術進步;勞動力轉移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始于農村的改革給農村經濟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工農差距、城鄉差距并沒有縮小,中國的“三農”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特別是1990年以后,農民收入持續數年徘徊下降,糧食總產量也隨之出現連續下滑。至2003年已經降到1996年以來的最低點。面對該嚴峻形勢,2004-2010年,中央政府連續出臺了7個針對“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支農政策,開啟了新一輪的農村改革。而“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離不開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的順暢轉移。農村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非農產業、從鄉村向城鎮轉移,既是世界各國都曾經或必將面對的一種普遍現象,也是其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的必由之路[1-2]。農村勞動力轉移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必須轉移出去,但轉移出去必須要同時考慮農業經濟發展,特別是糧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現有脆弱的城市體系難以在短期內承受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如何避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大起大落”和盲目流動,以保證農村勞動力有序、平穩、持續地向城鎮轉移,是必須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的目的在于,在中央政府連續出臺“一號文件”的宏觀背景下,通過理論推導和實證分析,研究農業資本投入、農業技術進步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和影響,以及耕地保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該結論為國家制定勞動力轉移政策以及工業化的道路選擇提供了重要依據。
1 文獻回顧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作為一種派生性生產要素,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對農業勞動投入有著促進或替代作用,從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就國內已有研究來看,牛若峰、曾廣奎等學者認為農業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擠走了勞動力”,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3-4];汪小勤、占俊英等學者認為,農業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并不能解釋我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而應該從城鎮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5-6]。對于耕地保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李實、劉繼兵等學者認為勞動力轉移使得土地資源搭配更加合理和有效率,從而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限[7-8],也有部分學者持反對態度,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地荒蕪或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下降,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9-10]。國外學者也很重視對該領域的研究,Bose考慮了耕地效率對二元經濟的影響,并認為耕地效率對農業部門的影響會“傳導”給理性的農民,從而影響農民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意愿[11]。Baumol創新性地把經濟分為持續發展部門和停滯部門,并認為持續發展部門主要的投入是資本和技術,而停滯部門主要的投入是勞動力,隨著要素流動,停滯部門的產品生產成本和價格必然上升,從而會吸引更多的勞動,該理論被稱為“鮑莫爾病(Baumol’s Cost Disease)”[12]。Ngai等從研究結構轉變入手得出了勞動力配置機制,即技術進步促進了勞動邊際生產力的提高,從而改變了勞動力在社會各部門的配置比例,并認為勞動力轉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Outcome)而不是原因(Cause)[13]。Pianta&Vivarelli通過對意大利等5個國家農業部門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發現農業資本投入只是在短時期內引起農業就業量的減少,長期和總體上會引起農業技術進步而對農業就業具有正效應[14]。
2 模型的建立與推導
首先,我們做如下假設:①為了抽象出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的特征及其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按照Lewis二元經濟理論[15],把社會部門劃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本模型僅僅分析傳統農業部門;②農業生產使用土地、勞動和資本三種生產要素,分別用 Gt、Kt和Lt表示;③農村勞動力總量固定為L;④農業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⑤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勞動力是同質的;⑥At表示技術系數并假設其是外生變量;⑦時間序列t是離散的,即:t=0,1,2,3…。則農業總產出Yt可以表示為[16]:

(2)式表明,農業人均產出隨資本供給增加和農業技術水平提高而增長,隨農業勞動投入增加而遞減。由于土地和資本是固定不變的,人均產出的增長要求農業技術進步率必須高于農業勞動投入增長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勞動投入增長率是工資率的增函數,這里采用Hansen和Prescott所定義的函數形式[17]:

應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要素收入分配法定義(3)中的工資率wt,即令工資率 wt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出:

式(10)表明,應用新古典模式,從動態分析看,農業勞動力投入量和At、Gt、Kt三個變量存在正向關系。進一步,假設農村剩余的勞動力會全部轉移到非農業部門,那么就如式(11)所表明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和農村勞動力數量L呈正向變化關系,而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At、耕地面積Gt、農業資本投入Kt呈負向變化關系[18]。
3 實證檢驗與分析
3.1 分析方法與變量設置
本部分檢驗上文所建立的模型的結論是否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據式(11)的結論,我們把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把農村勞動力總量、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耕地面積和農業資本投入量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對于模型結構,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穩妥性,我們選取多元對數模型作為結構形式。對數模型的優點在于它反映了解釋變量的變動與被解釋變量變動的關系,所要估計的結構系數恰好是變量之間的彈性系數,而且它發映了被解釋變量增長與解釋變量的增長間的關系,適合長期的時間序列數據。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經濟轉軌中的中國農業資本投入、技術進步等因素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因此選擇多元對數模型是合適的。計量模型結構如下:

L: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
G:耕地面積
ATFP:農業全要素生產率①全要素生產率包括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由于數據的原因,本文不詳細區分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
AK:農業資本投入量
TL:農村勞動力總量
3.2 數據來源
數據采用中國1978-2008年的縱截面數據。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L)采用國家統計局農村經濟調查總隊公布的數據;農村勞動力總量(T L)數據來自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1978-2002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ATFP)的數據來自趙洪斌等[19],2003-2008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數值采用《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利用“索洛剩余”法計算得到。農業資本投入量(AK)的數據,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不同資料或學者提供的數據差別較大[20-21],這里筆者從農業投資的來源界定統計口徑,用財政、信貸、集體資金和農戶投入四部分加總計算農業資金投入量,按照該統計口徑,該數據采用《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到。而農業耕地(G)的數據,1986-1995年為國家統計局年報數據,1996-2008年數據根據國土資源部各年國土資源公報整理得到。3.3 回歸結果分析
用Eviews3.1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回歸結果如下:

分析回歸結果,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上,除變量LnATFP外,其余的3個解釋變量的系數的t統計值都是顯著的;從模型的整體顯著性看,F值很大,說明模型在整體上是顯著的;調整R2高達0.977 4說明模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很好;由于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可以認定逆方差性基本不存在,而D-W值為2.021 1說明序列相關是不存在的。從模型解釋力來看:①農業耕地面積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的關系顯著為負,前者每增加1%,后者減少0.702 9%。這說明農業耕地面積的貧乏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之一。②平穩性檢驗有多種方法,本文利用的是單位根檢驗法。農村勞動力數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2.215 5%。這表明過多的農村人口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推力。③Eviews提供了ADF and PP兩種單位根檢驗,本文應用了ADF檢驗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由于篇幅關系,ADF檢驗值和檢驗過程略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根據本文附錄中的數據進行檢驗或直接向筆者索取:walkercheng@163.com。農業資本投入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的系數顯著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236 5%。這說明農業資本投入的增加,例如大型農業機械設備的購置和應用、現代農業化肥和農藥的購買應用等,對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有促進作用。④農業TFP與農村勞動力轉移量之間的關系為負,但不顯著,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并不明顯。
3.4 協整關系檢驗(cointegration Test)
現實中的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極少屬于平穩序列,而平穩性在計量模型中具有重要地位。為了判斷以上估計結果在長期過程中是否具有平穩性,我們對模型做協整關系檢驗。其過程如下:首先對每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②,以判斷它們的單整階數,初步判斷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然后做詹森檢驗。通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在模型中,lnG、lnAK、lnATFP、lnCL四個變量都是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③,而lnL也是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也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進一步的詹森檢驗(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結果如表1。

表1 詹森檢驗結果Tab.1 Results of 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
詹森檢驗結果表明,在模型中,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所以這兩個模型在我們選擇的樣本期間內均是穩定的。
3.5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
OLS估計只是將農業資本投入、農業技術進步等變量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的關系給以量上的描述,并未說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為了排除偽相關,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建立了二元變量自回歸模型逐一檢驗了各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因果關系。取Lag Specification=2,檢驗結果如表2。從格蘭杰檢驗結果看,變量lnG和lnCL能完全拒絕原假設,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數量和農業耕地是被解釋變量(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原因。而變量lnAK、lnATFP都不能完全拒絕原假設,這說明農業資本投入量、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等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農業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可能僅僅是相關關系,而不是因果關系。

表2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Tab.2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4 結論與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農藝工歇業、失業和返鄉現象比較突出。而2010年初,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卻又出現嚴重的“民工荒”。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如此頻繁和大幅度的波動,無論是“民工潮”,還是“民工荒”,無論是“招工難”,還是“找工難”,都給經濟發展或社會穩定帶來了一定的沖擊,還會影響到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本文從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平穩、持續轉移的視角,研究了農業資本投入、農業技術進步、耕地保護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和影響。比較分析理論模型的結論和基于中國1978-2008年數據的計量結果,發現它們在變量的基本關系上雖然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謀合。這里進一步給出一些基于中國特例的解釋和評述。
本文的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都表明,較多的農村人口數量和較少的耕地資源稟賦是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動力。也就是說,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條件是我國1978年以來轟轟烈烈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始動力和內在根本原因。1978年以后,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度約束逐步被打破,城鄉勞動力市場逐步完善。隨著這些外在市場條件的成熟,由于人均資源稟賦稀少而貧困且被迫長期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必然理性的流向相對富余的城鎮。因此,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是作為市場經濟個體的農民的理性行為,是中國農民在特定資源稟賦條件下的必然反應,也是中國農村發展乃至中國工業化的內在必然規律。我國政府機構應該遵循該規律和歷史趨勢,認識到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制定相應的政策(例如:保障、提高進城農民工的收入,保障進城農民工的安全,在戶口、子女入學、就業機會等方面消除歧視,提供城鎮醫療、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建立完善的農民工勞動市場等)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順暢轉移。
耕地保護關系到糧食安全,是國計民生的大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也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由此可見,耕地保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都是我們無可回避的重要難題。而農業耕地面積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負向關系。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且以青壯年勞動力或農村“精英”為主[22],這一方面使得農村勞動力投入不足,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下降,農地荒蕪現象嚴重,這種農業空心化的現象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刺激了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鎮的快速膨脹,而工業發展和城鎮擴張都需要占用土地,其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大量耕地的非農化。如何協調耕地保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矛盾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農業資本投入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之間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業資本投入對農業勞動力有替代作用。增加農業資本投入,既能促進農業的發展,又能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我國農業資金的來源主要有財政、信貸、集體資金和農戶投入四部分,促進農業資本投入增加,要從這四個方面入手,多管齊下。政府機構要認識到農業的基礎地位,堅持不懈的增加財政投入,要規范和完善農村信貸市場和機構,保證農業信貸資金的充裕和充分利用;但最重要的是要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利用市場杠桿,發揮激勵機制,使得農村市場的主體——農村集體和農戶愿意增加農業投入,認為“種地劃算”或“搞農業劃算”,使得他們有增加農業投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農業投入的邊際遞減效應明顯,規模經濟是增加農業效益的必然選擇。目前,我國的農業耕地仍舊是土地承包,小塊耕作,規模不經濟現象極其嚴重。這使得增加農業投入的得益受到極大限制,必然阻礙農業投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而,改革土地制度,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是提高農業效益、保持農業持續投入增加和農業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仔細分析發現,農業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對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作用,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是現代經濟學難以解釋中國問題的特殊性,還是中國特例否定了現代經濟學?首先,這是因為理論模型是無限期動態模型,是反映了農業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長期影響趨勢,而基于1978-2008年中國數據的實證分析則是檢驗了三個變量之間的一種短期影響,因為相對于無窮大的時間來說,1978-2008年只能屬于短期。而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是有差異的。就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來看,一方面,技術進步可以節約或替代勞動力,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又可以派生出新的產業,推進農業技術升級,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短期中技術進步對就業主要表現為負效應,而長期主要表現為正效應。“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通過增加產出,導致資本總量增加,生產規模擴大,提高社會消費水平,尤其可以促進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征的服務業的發展,從而產生就業擴展效應。在農村,技術進步除了通過促進農業產業化等影響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點,就地吸收剩余勞動力外,在其推動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也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提供了條件”[10]。基于1978-2008年中國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農業技術進步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并不顯著,這表明技術進步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這兩個效應,交叉作用于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相互抵消,使得農業技術進步沒有成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動因。就資本投入與勞動力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來看,資本確實可以擠出或替代勞動力,但這僅僅是短期效應。長期看來,隨著資本的積累,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匹配關系,資本投入增加會要求勞動力需求的增加。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經濟走的是一條資本深化不斷加速的發展道路,這必然會降低生產過程中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率,使得較高的資本投資率并不能相應地導致較高的勞動力需求增長率,這不但影響了農業就業總量的增長趨勢,而且造成了社會勞動力就業結構轉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其次,這種情形的出現,反映了在我國的勞動力轉移問題上,經濟力量被其他因素大大扭曲了,由于政府的傾斜性政策特別是戶籍制度等,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自由轉移受到較大的制約。那么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也就很難完全解釋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動因和影響因素,還需要從更廣泛的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結論所蘊含的啟示是,中國在選擇經濟發展路徑時,應該考慮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特別是要充分利用本國富裕的勞動力資源。而僅僅追求總量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有效的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所以必須考慮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技術進步帶動的就業效應;同時要促進勞動力就業市場機制的完善,特別是解決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制度約束。繼續加強教育水平和積累人力資本,普及各層次的教育培訓機構,提高勞動力素質,以解決好結構性失業問題。
致謝:本文模型的建立運用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的分析框架。在此對朱曉冬教授給予的啟發和多次指點表示感謝。
References)
[1]Obstfeld M,Peri G.Asymmetric Shocks[J].Economic Policy,1998,(26):207-258.
[2]Daveri F,Faini R.Where Do Migrants G o[C].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595-622.
[3]牛若峰.發展模式、技術進步與勞動力轉移[J].農業技術經濟,1995,(5):6-11.[Niu Ruofeng.Mode of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bor Migration[J].Journal of Agritechnical Economics,1995,(5):6-11.]
[4]曾廣奎,徐貽軍.內生農業技術進步條件下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模型研究[J].湖南社會科學,2005,(5):86-88.[Zeng Guangkui,Xu Y ijun.Study on the Model of Rural Surplus Labor Model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J].Hunan Social Sciences,2005,(5):86-88.]
[5]汪小勤.農業技術進步與勞動力的利用和轉移[J].經濟縱橫,1998,(1):15-18.[Wang Xiaoqin.Study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Agriculture and Labor Utilization&Migration[J].Economic Review,1998,(1):15-18.]
[6]占俊英.技術進步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1):99-101.[Zhan Junying.Technical Progress and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SurplusLabor[J].Science&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2003,(1):99-101.]
[7]李實.中國經濟轉軌中勞動力流動模型[J].經濟研究,1997,(1):27-36.[Li Shi.Study on the Model of Labor Mobility with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997,(1):27-36.]
[8]劉繼兵.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收入與農村經濟增長[J].湖北社會科學,2005,(4):63-67.[Liu Jibing.Study on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Migration,The Income of Peasants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J].Hubei Social Sciences,2005,(4):63-67.]
[9]寧光杰.經濟增長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J].經濟問題探索,1995,(4):54-59.[Ning Guangjie.Stud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Migration[J].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1995,(4):54-59.]
[10]李俊鋒,王代敬,宋小軍.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系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5,(1):23-29.[Li Junfeng,Wang Daijing,Song Xiaojun.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J].China Soft Science,2005,(1):23-29.]
[11]Gautam Bose.Agrarian Efficiency Wages in a Dual Econom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9):371-386.
[12]Baumol W,S Blackman,E Wolff.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Asymptotic Stagnancy and Nnew Eevide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75):806-817.
[13]L Rachel Ngai,A Pissarides.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C].Working Paper,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04.
[14]M Pianta,M Vivarelli.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Innovation:Evidence and Policy[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 ork,2000.
[15]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M].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
[16]Ian K ing.A Simple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rogramming in Macroeconomic Models[C].New Zealand University,2002:24-27.
[17]Gary D Hansen,Edward C.Prescott.Malthus to Solow[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4):1205-1217.
[18]朱曉東.高級宏觀經濟學講義[C].上海交通大學,2006.[Zhu xiaodong.Advanced Macroecono mics lecture[C].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2006.]
[19]趙洪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率演進的研究[J].財經研究,2004,(12):91-100.[Zhao Hongbin.A Study on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 of Chinese Primary Industry since Reform in 1978[J].The Stud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4,(12):91-100.]
[20]鄭洪濤,李銳,張蕙杰.二十一世紀初我國農業資金供給形勢的分析和預測[J].農業經濟問題,2000,(9):16-20.[Zheng Hongtao,Li Rui,Zhang Huijie.Study on China’s Agricultural Capital Supply Situation Analysis and Forecas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2000,(9):16-20.]
[21]趙麗華,趙國杰,韓星煥.我國農業投資效應分析[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4,(3):22-24.[Zhao Lihua,Zhao Guojie,Han Xinghuan.Study 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China[J].Technoeconomics&Management Research,2004,(3):22-24.]
[22]程名望,史清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動因與障礙的一種解釋[J].經濟研究,2006,(4):68-79.[Cheng Mingwang,Shi Qinghua.An Explanation for the Motivation and Obstacles Affecting Rural-urban migration:the Case of China[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6,(4):68-79.]
[23]厲以寧.中國城鎮就業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1:50.[Li Y i-ning.Study on Urban Employment of China[M].Beijing:China Planming Press,2001:50.]
[24]李寧,趙偉.東北地區城市就業能力的地域結構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7(4):44-48.[Li Ning,Zhao Wei.Spatial Patlernof Urban Employment Capability in the North-east Area of China[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7,17(4):44-48.]
Capital Input,Infield Protection,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Farmer Labor Migration
CHENG Ming-wang RUAN Qing-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 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is not only the major issue that we are facing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essential way to solve“thre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in China.The dynamic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on data from 1978 to 2008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larger number of rural workforce and less land resources endowment is the basic cause that leads to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However,the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moving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or cities and towns reducesfarmers’enthusiasm to cultivate the land,degrades productivityof agricultural land,restric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nd even threatens china’s food security.Coefficient between the numbers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This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e in investment can not only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stimulate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Advancement i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The countera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effects make advancement i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lightly affect the migration.This paper draws conclusion that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we choose the approac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especially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China’s rich labor resources.
dynamic equilibrium;capital input;cultivated protection;technology advancement;labor migration
F323.6
A
1002-2104(2010)08-0027-06
10.3969/j.issn.1002-2104.2010.08.005
2010-03-20
程名望,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與社會政策分析。
*教育部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編號:200802471084)、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編號:EAA080254)、上海市社科規劃青年課題(編號:2008E JB007)、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課題(編號:10ZS30)資助。
(編輯:于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