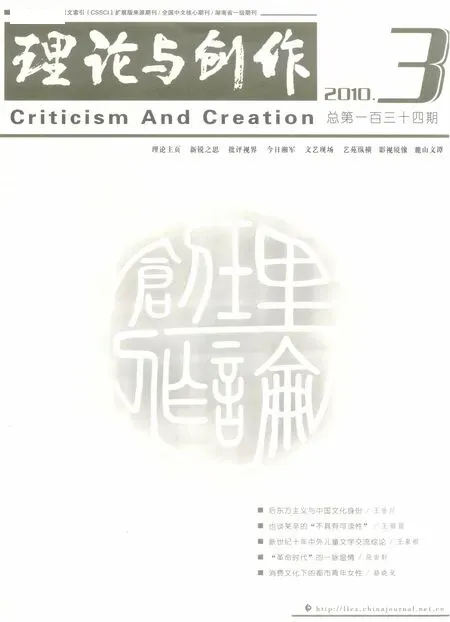你看那正在復活的詩歌
■ 左春和
當代詩歌在深陷于阿道爾諾的詩學命題之后,奧斯威辛和布拉格之春已成為檢驗詩歌生存能力的死穴。歷史想象力的斷裂造成了當下詩歌歷史命名能力的喪失,詩歌因此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羞辱。在詩歌已死的年代,其實除了極少數詩人堅守的歷史硬度之外,整個詩壇確實在滿天繁星之處竟然是星光依稀,熙攘喧囂之處則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詩壇繁榮中的貧困、喧鬧中的荒涼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判斷。
在詩歌新的美學格局的構建中,世俗美學的當下為王已經讓詩歌的自娛自樂走進“笑和遺忘”,歷史想象力的斷裂又使詩的存在徒具形式化的特征。在奧斯威辛事件中上帝是沉默的羔羊,任何關于上帝深不可測的公義并沒有能平息歷史留下的巨大空虛。作為一種獨立的美學話語,詩歌應該在這種歷史缺位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以便維持從廣場出走之后的精神生態。遺憾的是詩歌在進入隱蔽的世俗化之后愈來愈進入了不再指涉現實的專業化生存。在專業化生存中,正如薩義德所言:“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這種安適的、體面的專業化使詩歌表現為工具理性對歷史張力的壓抑,進而化約為消費性的大眾功利文化的泛濫。當這種詩歌的世俗喧嘩登峰造極之后,默茨的話才顯得擲地有聲:“沉默才不可理喻,有時甚至令人憤慨。”
畢竟歷史的道路不完全是保羅的道路。歷史的光芒依然照耀著漢語中的詩歌,詩歌生存的世俗真實并未能全面顛覆漢語生態。近日讀到沈浩波的《秋風頌》、《北京,我的幻影》及《亞細亞的憂傷》等詩篇才知道歷史并未全部失蹤,深切的歷史關懷依然散發著心性品質的溫暖。詩的自由一定在民間的深處。或許正如尼采所言:“真理就是讓我們忘了它是幻覺的幻覺”,激情和神話讓我們對歷史的正義關懷已忘卻多時。布拉格之春之后的天空是空虛的,所有的熱情在一哄而散之后我們才開始審視熱情的合法性,但理性又使得詩歌的判斷極易滑入道德清算。在精神氣候凝固多年之后,詩歌的歷史關懷也已經成年,它不再象當年擁抱高蹈正義的熱情那樣去寄希望于新的號召。邁克爾·奧克肖特強調:“實現正義的熱情,會讓我們忘記慈悲為懷;對公正的熱望,使許多人變成了鐵石心腸。”沈浩波只是發現廣場的熱情中:“高高的天幕/偶爾有幾顆星星/睜開那屬于已死老人的/渾濁、酸痛,充滿沉默威嚴的眼睛。”這種對廣場彌賽亞主義與現實關聯的拆除,意味著詩歌的判斷走進了大地的反思:在“天幕”之下我們具有屬靈的品質,還不甘于被各種烏托邦所統攝。我們所要求的公義和幸福并未在自然法則的因果之中產生,有時候只能重新打量預定性的塵世秩序。當詩歌洞穿了這一切又不具備自身的行為能力之時,只能“提醒我們強權的凜冽/和天空的無知”(《秋風頌》)。在一個后極權時代,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所以沈浩波告訴我們他看到的:“一群洗得干干凈凈的女人/像一把又白又甜的大蔥/帶著渴望被啃一口的喜悅與羞怯/在秋風中忙著出嫁……”這些天空之下的“女人”怎么了?她們為什么暗含著神圣的熱情,在一種神奇的自我改變中去“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托克維爾)?
布拉格之后,奧斯威辛命題成為壓抑著的死亡。詩歌也因此發生了自由的斷裂,自從失去了廣場的熱情之后也失去了仰望天空的興趣。為了壓抑死亡與廣場彌賽亞主義的關聯,犬儒主義普遍成為當下詩人的生存理性。于爾根·莫爾特曼說:“被壓抑的死亡是存在的,被壓抑的死者和哀悼者在我們中間。對死亡的壓抑使得現代人冷漠、麻木、不成熟。它造成了扭曲的享受態度和偏激的績效主義官能癥。它透過壓抑而抹殺了對整個生命的熱愛”。
在詩歌這種壓抑著的死亡埋葬多年之后,雖然“人們像水珠一樣消失/像鴿子一樣消失,像麻雀/一樣消失,像被吞吐進胃里/的梨一樣消失”,但是“我在深水中不肯安眠的倒影/不晃動,不破碎/睜著溺死者灰色的眼眸”。這種歷史想象力的復活不單是歷史話語的復活,而是詩歌永遠無法泯滅的那個噬心的歷史主題的復活。當所有的“天空不再給予希望”(貢斯多)之后,詩歌依然把最后的絕望留給自己,歷史的命名能力便是這最后絕望中的歷史復活。所有“壓抑著的死亡”并沒有消亡,而是用歷史的斷裂創造了自己的死亡。按照巴德爾的神學祈禱命題,死亡從本質上遠遠超過了談論死亡,死亡中“灰色的眼眸”并未象談論死亡的人們“鴿子一樣消失”,和“像麻雀一樣消失”。或許還可以按照大衛·弗格森所引述的工具論神學的觀點來慰藉自由中的詩歌:“一個存在著自然之惡的世界將因此而培育出堅韌、勇敢、獻身和慷慨精神,而用別的方式這些是不可能實現的。”其實這遠非詩歌在復活中的力量,它的力量來自于一個真正的歷史命名能力的自由情懷和人類倫理秩序的鼓舞。當一切崇高的道德命題同烏托邦一起隨風飄散之后,支撐著詩歌合法性生存和歷史命名能力的永遠是普世的人類倫理。人類倫理永遠高于政治理想。這也便是為什么別爾嘉耶夫不厭其煩地強調:“政治是控制人們的假象。”原因在于“自由高于存在”。任何道德命題和意志命題可能是對于自由的拒絕,也是以現存秩序之名對于人性倫理的拒絕。
沈浩波在這首不同凡響的《北京,我的幻影》中解禁了對于自由生長的拒絕,同時也解禁了對于歷史想象力的戒嚴。告訴我們“悲傷的事物至今仍然/停留在石頭的陰影中。玻璃/的反光,像是密探冰冷的眼/而記憶在不存在中閃光。”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的“人的不幸就起源于他的偉大;起源于他內心存在著無限,起源于他不可能最終把自己葬送于有限”。在這首詩中“麻雀在右眼飛翔”,它無法像“左眼”中“安靜”“啄食”的“鴿子”那樣“肥胖”,那樣“像浮腫的死孩子”一樣安逸。雖然“連視線都飛不出”,但“這可憐的/小石頭般灰不溜秋的東西/不幸擁有了渴望自由的意志。”是的,自由,自由,有多少精靈為你而亡。所以別爾嘉耶夫才說:“自由的反對者喜歡用真理來反對自由,強迫別人去確認這一真理。”目的在于剝奪天賦的脆弱而強勁的自由。這樣既存的自由與權力的沖突便進入了福柯的權力命題:權力話語在強化自身真理性的同時,也削弱了其存在的基礎,并暴露之,使它變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不是嗎?連一只飛不出視線的麻雀就使得“天空布滿鉛粒”,同樣也使得權力難以在伯克的權力批判中向人的內心范疇延伸,因為它“很少能行積極的善”。在此,沈浩波透過“夕陽像廢墟之神……”聽到了“烏鴉的大喉結吐出歡歌”,并認為“我們一定看到了什么,但我不能宣布”。在權力和犬儒共謀的美學格局中,這種詩歌的勝利也只是自由的勝利,而不是世俗的勝利。盡管這種詩歌的勝利穿過了語詞的象征性曲折,但天空覆蓋下的大地還是能聽到那種對于犬儒主義文化自媚的響亮耳光。這種詩歌的勝利沒有進入獨善其身的東方主義哲學和價值虛無主義,它的復活在奏響詩歌犬儒主義的歷史喪鐘。在那種自負的意志和結構之中,詩的自由使它的復活具有著使“專業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寫作”者無地自容的力量。
朋霍費爾說通向自由的道路,不僅有行動,而且有受難。但是作為曾經擁有上帝榮耀的詩歌,它永遠不會滿足于做那只“左眼”中“啄食”的“浮腫”的“鴿子”,它的生存只為證明自身的歷史命名能力和精神尊嚴。它的復活也是不甘于隨著整個文學主體的結構性死亡而消亡,而是在充滿了陰謀論、敵人意識和斗爭美學的精神祖國傾訴自己的信仰和愛。只是諾恩羅普·弗萊說:“詩歌僅按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形式提供啟示:它并不描述也不表達啟示的單獨內容。”這并不能歸責為復活中詩歌的自由策略,而是真正的詩的自由與戰斗號角的本質分野,是沉郁的力量對于昨天高亢的宣言的告別。
當復活中的詩歌再一次披著信仰而飛翔,我們似乎看到那“金色的/馬車、像馬蹄達達的聲音”。詩歌雖然走出了權力的征用,但在普遍被消費主義雇傭的時代里,詩的復活又面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犬儒主義和阿倫特所謂“平庸的邪惡”的多重圍剿。所以,詩的自由與復活仍然是一種理想,一種裹挾著走出阿道爾諾哲學命題的夢想。詩歌的“信仰不是理所當然的,它不可能帶著一定的目的性而產生”(雅斯貝爾斯),在新的復活中詩歌也只能在自己的詩歌內部對世界發言。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對這些復活的詩歌中那些堅硬的帶著金屬寒光的詩句沒能引用,也無法做精準意義上的文本細讀。這些詩歌的出現第一次告訴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史沒有斷裂,從這些精神記錄中我們仍然能夠聽到歷史的心跳。在另一首《亞細亞的悲傷》里,沈浩波更是把詩的關懷伸展到認同性意志結構的想象之中,去觸摸那種“瓦礫下埋葬著正義/悲傷是一封不準被傳遞的信”的“耶路撒冷的凌晨”。這種以血的代價鑄成的東方共同體想象為什么沒有應答個體生命對于和平的呼喚?恐怕是生命的福音并不能靠代祈而完成的權利命題。這些復活的詩歌追求帶我們從鉛一樣的天幕下逃脫出來時,我們才發現原來是一種多么軟弱的東西在籠罩著生命的奔放與自由。在死亡的極限處,奧斯威辛的確給了詩歌一次機會,當詩歌能夠在“秋風”、“幻影”和“悲傷”中傾聽、承負生命的不幸,生命便賦予它復活的偉大榮耀。
九十年代以來,詩歌中那種免于恐懼、免于奴役、免于傷害和實現自我價值的生命欲求隨同那熱情的人群一起逃之夭夭,在顯而易見的意義上詩的自由也停止了呼吸。今天當我再一次感到詩歌復活中那種歷史想象的內在張力,對于“幻影”的否定又并未使用否定的話語去完成否定。才使我真正看到了詩歌在新的時代的有效作為,它并不為你提供彌賽亞式的精神按摩,只是孤獨地去背負自由的實踐和心靈的風暴。也許詩歌的自由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它也沒有必要去解決一切問題,只象德爾圖良荒謬論神學那樣證明天空的荒謬就足夠了。正因為這個“幻影”的荒謬才使得世界如此真實。凸顯在這些詩歌中沒有任何道德話語的自我捧媚,只有來自曾經沸騰血液的刻骨銘心的省察,以此告訴你,詩人并不一定是一個道德人,但他的道德勇氣在這個犬儒化的時代里會使犬儒主義倒吸涼氣,讓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從此掙扎于“啄食”與“浮腫”的精神困境。